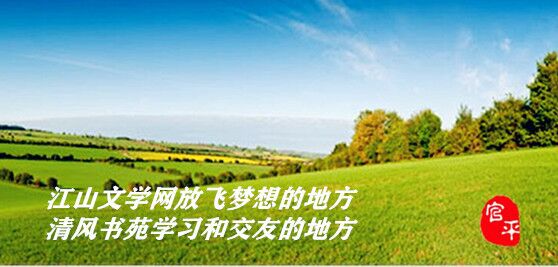【荷塘】秋来豆腐香(散文)
【荷塘】秋来豆腐香(散文)
![]() 那天双休日在家,我遵妻嘱去菜场买菜。走到一豆腐摊前,一股豆香扑鼻而来,那白白嫩嫩、水灵灵的豆腐,不禁勾起了我绵长的思绪……
那天双休日在家,我遵妻嘱去菜场买菜。走到一豆腐摊前,一股豆香扑鼻而来,那白白嫩嫩、水灵灵的豆腐,不禁勾起了我绵长的思绪……
小的时候物质较为贫乏,生活相当简朴,那时要是能够吃上一碗香喷喷的小煎豆腐,别提有多高兴了。
那时最盼的是过年了,因为过年前在农村会打豆腐、捣糍粑,我就在外婆家见过舅伯、舅妈在春节前忙着打豆腐的情景,只要他们家打豆腐,就会让表姐或表弟来叫我们去吃豆腐脑、喝豆浆。做豆腐工序较多,从泡黄豆开始,经人工打磨,即用石磨将泡好的豆子磨成豆浆,再经过滤之后,剔除豆渣,把豆浆倒入大铁锅里熬制成热豆浆,就可以喝豆浆了。烧好的豆浆再放上经配方的卤水,就成为嫩豆腐,又称之为豆腐脑,把它再用罩纱布包起来,放在豆腐专用的隔板里,用石块或其它重物压上,等到一定时间就压制成了我们可吃的豆腐。
据说,宋代苏东坡极喜食豆腐,他在湖北黄州为官时还经常亲自做豆腐,并精心烹制,用味醇色美的豆腐招待亲朋好友。友人吃了他做的豆腐更是赞不绝口,亲切地称之为“东坡豆腐”,直流传至今。东坡曾在蜜酒歌中写道:“煮豆作乳脂为酥,高烧酒烛酌蜜酒”,可见他对豆腐的喜爱。
在上学时邻家发小的父亲因信佛长年素食,豆腐就是他最好的素餐美食。每次放学回来从发小家穿过的时候,就见这位父亲大人独自在做自己吃的菜——煎豆腐。煎好的豆腐为焦黄色,然后放上青椒、红辣酱等调味品,稍煮后就可起锅食用。闻到弥漫的诱人的豆香,我忍不住会直咽口水。
我母亲在街道供销社饮食店工作,是一名厨师,又称红案师傅,做得一手好菜。等我懂事的时候,母亲就教我煎豆腐等系列菜的做法。当时家里只有柴火灶,烧的是草把子,经常烟熏火燎的,火大火小都很有讲究,豆腐块切好后,什么时候下锅,什么时候翻动,什么时候加调味品,经她做出来的豆腐,那真是色香味美。轮到我做时,虽然小心翼翼,有时也难免会将豆腐煎成“豆腐渣”或都煎糊了,但豆腐的醇香味还是满足了食欲。除了煎豆腐外,豆腐其实还有多种吃法,常见的如在夏天可做成凉拌豆腐,或皮蛋拌豆腐;日常会做麻婆豆腐、家常豆腐,还有豆腐汤、豆腐丸等等多种菜肴。豆腐丸的做法会复杂很多,平日里母亲是少有时间来做的,但每逢春节母亲准备过年菜肴时,必会做豆腐丸。具体做法是,往豆腐丸里放一些肉末,将肉末和豆腐捣烂后糅合在一起,加上香料和粘性粉一类,再捏成丸子,然后用蒸笼蒸熟,放些调料即可食用,也可用于下到汤锅里,闻起来香,吃起来鲜。那些年猪肉凭票供应,过年能吃上加了肉末的豆腐丸,就是最奢侈的事了。
七十年代末我到地区中专学校求学,对我来说当时学校食堂最诱人的菜就是豆腐或香干子炒肉了。豆腐加上少许肉丝和青椒、芹菜,两毛伍分钱一个,价廉物美,就是上好的菜了。
是豆腐滋养了我的身体,强健了我的大脑,陪伴了我的学生生活。
前不久几个爱好摄影的同事相约去了离我家乡不远的程集古镇,在老街上第一家青砖飞檐老房子就是一个豆腐作坊,屋檐下挂着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冉记豆腐”四个大字,可算是豆腐老店了。走进豆腐店,一对中年夫妇正在打制豆腐,女主人操着长把锅铲在灶前的大锅里搅动着豆浆,男主人见我们来了,边和我们打招呼边忙着自己的事,往灶台上倒粗壳,用铁钬钳扒着粗壳把火烧旺。听他介绍,这是一家豆腐老作坊,他已是第三代传人了。这几年尽管豆腐店的生产能力不如从前,但他们仍然在小镇坚持着、坚守着,用自己辛勤的劳动为人们奉送美味的豆腐。如今他们除了不再用驴拉磨磨豆浆外,仍然用传统工艺制作豆腐,保持了豆腐的原有风味,生产出的豆腐、千张等豆制品,味道纯正,豆品飘香,很受顾客的欢迎。看到夫妇俩刚刚打出来的豆腐白嫩,千张皮薄有劲道,我和同事每人买了几斤,才离开程集古镇。
秋风里闻豆香而思豆腐,怀恋儿时吃豆腐的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