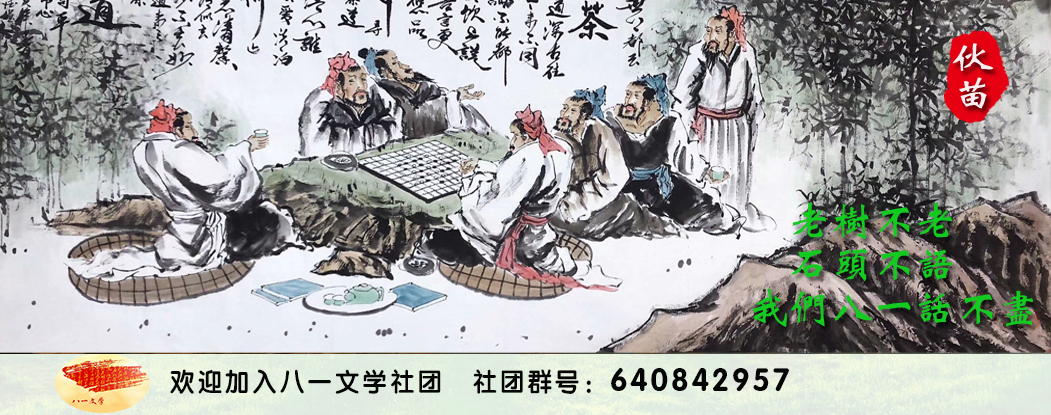【八一】快活非凡的珍大大(小说·家园)
【八一】快活非凡的珍大大(小说·家园)
![]() 一
一
夜色像巨鸟的翅膀,悄然掠过田野,把大地变得一片模糊。渠水在静谧中潺潺流过,怡然自得。纺织娘和蛐蛐干劲十足地开始奏乐,迎接黑暗的来临。月亮懒洋洋地滑出云层,使大地更显得扑朔迷离。
侯家村口,道路和长渠交叉处的土桥上,烟火一闪一闪。远瞧好似个老汉,走近了才显露出一个农妇的身影,又高又胖。她狠狠拔了几口烟,朝桥头站定,突然放开细尖清亮的嗓子嚷道:“看电影的快点!再迟就不等啦!”
音波在坦荡的大平原上急速地扩展,从门缝、窗口涌进各家各户的堂屋、厨房,撩得那些女性电影迷们心焦火辣、手忙脚乱。姑娘媳妇们或是端着饭碗,或是拧着毛巾,或是怀揣着吃奶的伢儿,慌不迭跑到篱笆边应道:“珍大大,千万别走!就来就来罗!”
古板的家长们在一旁气得鼓腮瞪眼,却不便阻拦。因为珍大大排行大,辈份高,几乎半个侯家都是她的侄辈、侄孙辈;加上珍大大火气足,口舌厉害,几句话不对碴儿她就会劈头盖脑攻了上来:“咋啦?把女娃们当牛马使?想发财不是这么个发法!早先没电影你也不过秸秫杆儿扎墙草当瓦;如今我天天看电影也没穷得去当裤子。自个儿土拔鼠似的,还不准孩子们乐乐!都不去,人家放电影的吃不吃饭?你说呀!你安的什么心?!”直嚎得对方连连后退,诺诺应声,把暗暗得意的娃娃们打发出门完事。
珍大大瞧瞧队伍到齐,把三尺长的烟竿儿一挥,威风凛凛地前面开路。看电影的妇女大军叽叽喳喳、欢天喜地地出发了。行列中最小的妞妞才八个月,趴在妈妈的背篓里东张西望,好不精神!他妈妈秀秀在娘家就是有名的影迷,至今本性难改。公婆无奈,只能拿出这一手来钳掣:“屋里屋外事儿堆成山,要去你带上妞妞!”最大的成员要数司令官珍大大本人,今年足足四十八岁。她十来岁到男家做童养媳,为偷偷听戏不知挨了多少打骂,后来成家立业作了主人,才光明正大地把看戏当作家规之一。什么京戏、楚戏、汉剧、皮影剧,来啥看啥,从不挑剔。但文化革命中那些“叉腰跺脚”戏她不爱看,嫌踢起的灰尘呛人。近年来戏班子渐渐绝了迹,她又爱上了电影。什么惊险片、科教片、“男扮女”、“女扮男”,她一视同仁,样样喜欢。她永世难忘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公社电影队竟在她家门口放了一场电影。虽说煨茶烧掉半捆棉柴,顽皮的娃儿们践踏坏一垅茄子秧儿,散场后三把椅子失踪,五把椅子断了腿,珍大大却乐得整夜睡不着觉,认为这是她生命史上最值得自豪的一件大事。
朦胧夜色中,哪个“嗳呀!”一声,咕咚跌进了土坑。不要紧,这一带是长江旧道,掘地数丈仍是细沙,摔下去不疼也不脏,只是虚惊一场。同伴探身用力一拽,嘻嘻哈哈就上来了。
路途中,真正的危险是那些歪心眼的小伙子们。他们乘着黑暗钻进女人们的队伍,推推攘攘,动手动脚,企图占点便宜。只要求援声传进珍大大的耳朵,她立刻止步转身,举起长烟竿,猛喝一声“谁?”单单这一个字儿,足以使不规矩的家伙胆颤心惊,仓皇逃遁。——被珍大大训斥过的人,还能指望顺顺当当找个好对象吗?
这一带是荆、楚故地,风俗古淳。女婚男嫁,习以为常,姑、叔、姨、舅,统称“大大”。大大虽多,谁也没有珍大大深孚众望。她豪爽,她大度,更主要的是她快活。她能把沉闷变为活跃,活跃变为热闹,热闹变得锣鼓喧天!她简直就是一台戏:人称“快活非凡的珍大大”。
到了。空旷的原野上传来激动人心的音乐;漆黑的天边出现雪亮诱人的灯光。队伍骚乱起来,人们纷纷加快脚步。珍大大晃动着烟竿儿匆匆交代道:“散了场还在那棵树下聚堆,谁犯了自由,往后别再想和我一块儿出门!”这种警告威胁力量很大,没有了珍大大,就没有了保护神。心怀不满的家长会马上加以利用:“啊?你不是和珍大大一道?!好大的胆子!快给我挑水浇园子。敢迈出门槛一步,看我不敲断你的狗腿!”所以,珍大大的部下,个个都是“一心一意跟她走,千难万险不回头”的。
就像渠水漫过田垅,渗进土地一样,到达放映场地的小股队伍眨眼汇入了黑压压的人群、各自寻找着合适的位置。四周树杈上、麦垛上全是光脑壳的男孩子;银幕背后,蹲着一排排文静的女孩子,她们早就晓得:除了幕上的字儿,反看正看,其实都是一个样。一个大队包电影,东南西北四个大队都要来,再宽阔的稻场也容不下呀!勇敢些的姑娘们在人海里拚命朝前挤,知道大多数男人都乐意为她们挪出一个空档来;害羞的姑娘们只能站在后面,从前排人肩头、耳根间的空隙瞅着,可怜巴巴地欣赏着银幕上的半边脸庞或一团莫名其妙的色彩。脚尖踮酸了,一落下来,眼前只剩下陌生人充满汗气的后脊梁;还没缓过气儿,听着音乐叮里咣当怪吓人,不知银幕上有啥大变动,鼓鼓劲儿又使劲把脚尖儿踮起来。怎么?脚后跟触到一个坚硬的东西!把体重移了上去,全身顿时轻松多了!回头一瞧,原来珍大大不知从哪个旮旯摸来了一块垫脚砖头,就这几寸厚的废砖块,使姑娘崛起于黑暗,沐浴在光明之中。
二
至于珍大大,不用操心。她个头高、力气大,针插不进的人堆里她也能拱出个位置,还可以捎带捞上背孩子的秀秀。珍大大那红火闪亮的烟锅头犹如开路先锋就钢铁汉子也得退避三舍。珍大大的烟叶厚墩墩、黄澄澄,是她亲手栽培,收、晒,又用米浆熬制过的。她抽得津津有味,旁人闻着也余香扑鼻。若有哪个楞头青不识深浅说她:“看电影吸烟,罚款伍角”,她不一烟筒扣过来才怪!
也有些倒霉透顶的同伴,影片里主人公都快结婚了,他们还没找着个正经位置,在人缝间汗漉漉地窜来窜去。听那乐曲悠扬婉转,急得她们心焦如焚,无奈何只得高声求救于珍大大,好比羊羔呼唤着母羊。珍大大二话不说,高高擎起烟竿,招呼他们过去,自己侧身让了出来,再雄心勃勃地去开辟新天地。过后如果有谁道谢,珍大大瞪起双眼:“咋?我带你们去是叫你们看人家后颈项的?你们一个个垂头丧气灰溜溜的,我能安心安意看?快乐本是大家伙儿的事!”
有时放映地点太远,队伍气喘吁吁刚刚赶到,银幕上便映出斗大的“再见”二字。人们只好怏怏转身,稀里糊涂朝回撤。娇嫩一点的开始抱怨,背孩子的秀秀发誓有人用轿子来接她也不再看电影了。可是第二天晚间珍大大宏亮的声音一响,她们照旧迫不及待地跟了出来。好像双腿不是长在自己身上,到是在珍大大嘴上。
为了什么呢?仅仅是为了瞧瞧那淡寡如水的、放了十遍甚至二十遍的电影吗?还是为了听听沿途的流水潺潺、道旁的虫叫蛙鸣?还是为了想看看白天劳动过的田野在晚上变成啥模样?或者,竟只是为了去感受那万人聚会的宏大热烈的气氛?去见见某张深藏内心的难以忘怀的脸蛋?
谁也说不清楚。反正那些姑娘们、媳妇们、半大的孩子们爱跟着珍大大走,爱在平坦柔软的沙质路上絮絮细语,爱在辽阔的夜空下奔跑追逐。大自然为了报答人们辛勤的耕耘,利用地球的阴影和月球的反射,把自己装扮得比白昼更加妖娆,让人们去尽情欢乐享受。
就在开卷描写的那个夜晚,电影结束回家的路上,侯家的女人们听到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珍大大要离开农村进城啦!她的有出息的女儿,中专毕业后留在省城,如今已成家有了孩子,要把母亲接去料理家务。
背着小妞妞的秀秀气咻咻地追上来:“珍大大,当真吗?”
“又是电报又是信。”珍大大得意洋洋。
“那,咱们往后看电影……”秀秀眼眶涌出了泪花花,想像着婆母幸灾乐祸的笑容。
“我说清楚了:好,住半年;不好,打个盹儿就回来。”
“您还愿回来呀?人家城里三步一个剧场,五步一个电影院,您……唉!还能回来呀?”秀秀激烈地反驳说。
旁边有人插嘴:“看你个傻秀秀,是人家闺女亲,还是你亲?”
这话有理,谁也不好再开口挽留。
从珍大大离开的那天起。侯家的土桥失去了魅力和权威。往昔浩荡的看电影大军如今成了散兵游勇,各自为战,家长们把憋着的气舒舒服服嘘了出来,心满意足:“死妮子们,可得老老实实给我呆在家里。”
珍大大一走,仿佛把自由、欢乐、电影一古脑儿全带走了。
女儿柳柳偕同丈夫一起到车站迎接母亲。女婿戴着眼镜,说话轻言慢语,是个文弱书生模样。只是喊“妈”的时候,舌头像是短了半截,声音刚冒出来就吞回去了。珍大大并不在乎,朗声应了个“唉!”反把年轻人唬了一跳。
女儿家住六楼,楼梯狭窄,珍大大身胖体宽,勉强通过。后来只要她一走动,整个单元都得开放红灯,暂禁通行。珍大大好不纳闷:“这班泥瓦匠们八成是些比搓衣板还干瘪的人。”
吃过丰盛的接风晚餐,珍大大兴致勃勃,问起小外孙,说还在奶奶那边,明天接回来。珍大大便掏出塑料包儿,抖开几片肥大的烟叶,细心卷成筒儿,然后“嚓”地点燃,小小的房间里马上飘荡起几缕清烟。女婿伸出食指朝上推推眼镜,不觉皱了皱眉。女儿笑着问:“妈,您还抽烟?”
“混时辰呗!”珍大大说着喷了口浓雾。女婿忙屏息让雾散去——他知道这叫“强制抽烟”。
“报上说,抽烟得……病呢!”女儿仍笑着。
“胡说!”珍大大伸出树干一般的胳膊,“我抽了一辈子烟,来,比比看!”
女婿实在忍不住了:“我们小娜娜才三个月,恐怕受不住这呛?”
“越呛越壮,清嗓镇凉。”珍大大朝女儿一指:“我柳柳小时候从不兴害病,我那时就抽烟哩!”她朝女婿瞟了一眼,意思是:不然的话,你哪来这么个好媳妇!
女儿女婿相视一个苦笑,只得暂且作罢。
三
晚上,珍大大在窄溜溜的床上刚刚躺下,忽听得远远传来阵阵音乐声,便向内室高声问道:“柳柳,哪儿在放广播?”
“隔壁剧院。”柳柳干巴巴回答。母亲不受“开导”,她有些沮丧,又担心丈夫瞧不起。
珍大大却极端兴奋起来:多近的戏院哪,简直跟那次在我家大门口放电影一样,可人家这是朝朝每日如此呀!今儿来不及了赶明天,无论如何要过去瞧一瞧。可是第二天亲家母送孙女儿来,聒聒噪噪忙了一整天,插不进这个话题。到了第三日,吃午饭的时候,小俩口正议论给娜娜买件啥式样的连衣裙,珍大大打断他们的话:“柳柳,这两天唱的啥戏?给我弄一张票。”
女婿惊愕地张开嘴巴,眼镜差点从鼻尖上滑下来,好像岳母说的是“太阳掉到咱房顶上啦!”一样。柳柳瞅一眼丈夫,脸蓦地红了,忙说:“妈,这戏……有啥看头?”
“没看头人家咋会演?”珍大大理直气壮。
女婿急忙参战:“这是下面县城小剧团的,没什么水平,包您一进去就打瞌睡。”
柳柳顺势道:“妈,过几天天津歌舞团要来演出,我们一定给你买张票。”
小娜娜无意中和父母结成了同盟,她猛然在外祖母怀中大哭起来,四肢乱蹬。于是这场谈话便不了了之。
过了些日子,有天吃过晚饭,女儿女婿说有要事出门。珍大大见他俩打扮得漂漂亮亮,说话又吞吞吐吐,心生疑团;掐指一算,那个什么天津的大剧团也该来了,莫非……珍大大心生一计,抱着小娜娜站在阳台上,死死盯住通过剧院的通道。果然不多会儿,便见女儿女婿勾肩搭背,亲亲热热走过去了。珍大大顿时怒从心头起,没良心的东西们!只顾你们快乐。来了这么多天,没说请我看回戏。不过几步路,到像隔着高山大河一般!还设法儿哄骗我!
珍大大可不是好惹的,她把小外孙女哄睡,在摇篮里放好,三下五除二拾缀了衣裳卷儿,然后搬把椅子,横眉竖眼坐在客厅中央,严阵以待。好便罢,不好当夜就走!
小俩口谈笑风生上得楼来,把门一开,便晓得事情不妙。柳柳抢上一步:“妈!”
“妈死了。这里只有老佣人丫头片子!”
柳柳知道母亲的脾气,怕闹出难堪,忙赔笑说:“妈,您别这样!哪晓得票这么难搞!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弄了两张。都是独唱独奏的,以为您不爱看——”
“我没长眼睛没长耳朵,听不到看不见!”
柳柳噎住了,悄悄捅捅丈夫。小伙子先伸出食指正正镜架,清清嗓子,然后小心翼翼喊了一声“妈!”——
只这一个字眼,便把珍大大心中的怒火浇熄了一半,因为女婿自打车站上吐了含糊不清的半个“妈”字外,再没用过这个称呼。
“您们年纪大的人,喜欢的是古装戏曲片。后天上映‘三上轿’保证给你买个好座位。”
珍大大是个鞭炮脾气,炸得响也退得快。见女儿女婿窘成这样,早就暗暗心疼,何况又有“三上轿”的指望,便回嗔转喜道:“看不看事小,何必瞒着我?当娘的在侯家也是一呼百应的人物哩!”
摇篮里突然哭声大作,于是事件圆满解决。
到了那天,小俩口再不敢怠慢,早早便买了张五排五号送来。珍大大眉开眼笑,做晚饭时尽量施展手艺,煎的豆腐黄中透亮,炒的菠菜根甜叶香;汤炖得不咸不淡,饭蒸得松软清爽。
一家三口正欢欢喜喜吃着,突然大门“笃笃”作响,来了两位气度不凡的客人。文质彬彬的女婿一反常态,毛手慌脚地找瓶子打酒;女儿也春风满面地筛茶装烟。珍大大在厨房扯住女儿一问,才知道是两位了不起的贵宾,据说女婿的提薪晋级定职称,关键全在他俩身上。这是件大事,珍大大只好把“三上轿”搁在一边,重新掏炉升火,赶烩佳肴,为女婿的前程加盐添油。
感谢老师赐稿八一社团,感谢支持八一社团,期待老师更多佳作,问好老师。遥祝冬祺,并祝创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