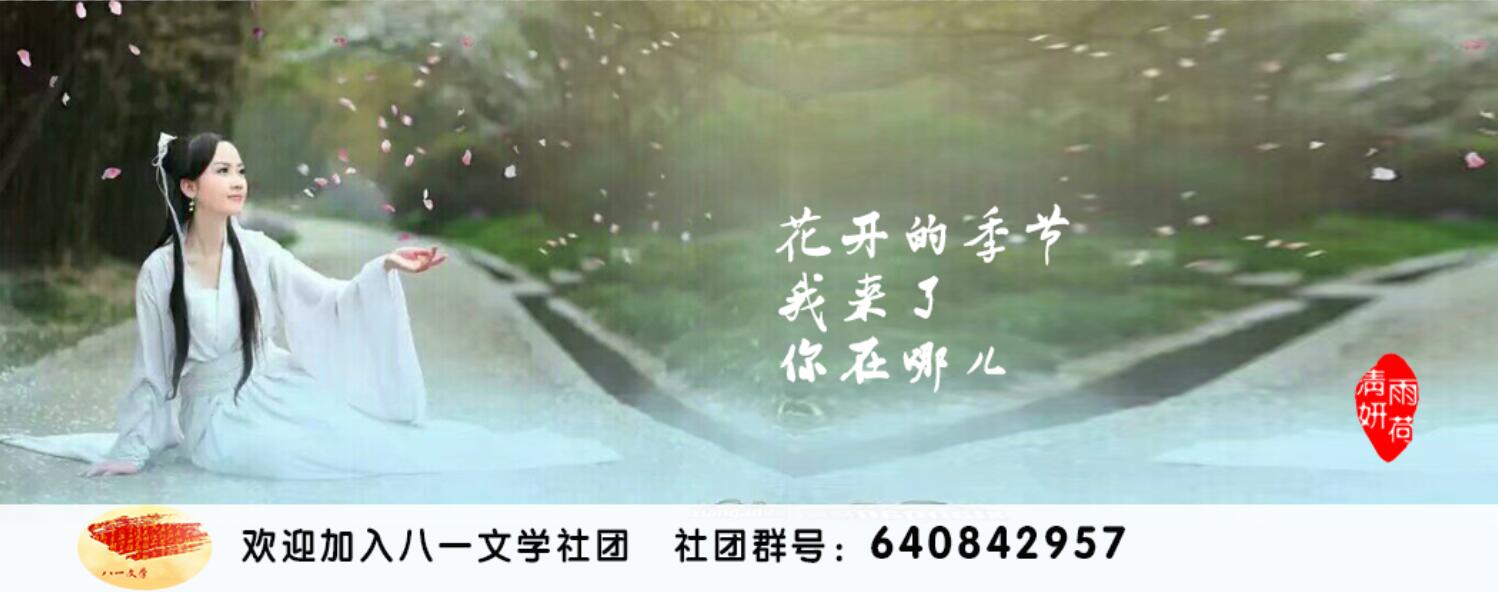【八一】又忆母亲(散文)
【八一】又忆母亲(散文)
![]() 是谁在春风中呼唤?是谁又勾起了我的思念!
是谁在春风中呼唤?是谁又勾起了我的思念!
吃过了早饭,原本昨天我们电话联系,一起乘车回家,但考虑到今年的疫情,要尽可能减少群居和扎堆,我只能先行一步了!
在前些年,关于清明节,曾有人提出了网上祭奠,这样既环保又可减少道路拥堵。虽然响应的年轻人很多,但由于受世俗观念的影响,新风俗落实起来大有点任重道远。
故乡的山水我是熟悉的,故乡的人情我是熟知的,故乡的一切往事似乎在今天又好像在昨天。今天的天气不错,太阳虽还没有完全升起,身上就已感到有夏天般的温暖。山坡上的杏花刚谢,桃花、杜梨花已开始争奇斗艳。
通往母亲故地路边的草丛里,每年春天都会开出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小黄花。自母亲去世后,每当我望见这草地上的小黄花,我就会想到母亲墓地上的花环,一种触目伤怀油然而生。
站在大路边,远眺这大田里翻滚的麦浪、我想起了母亲在世时,她常对我说:“宝丰麦好吃,每年都要给你们留种一些。”尽管她那时已有八十一岁了……她走后的这些年,我一直留种着宝丰麦,尽管有人说这长时间不换麦种,该品种会退化,但从我种植这几年看,它长势依然良好,难道是冥冥之中母亲给予了指导和保护!
在大田外的水库坝上,杨柳吐绿、枝条飘逸。小时候,在正月开学前,母亲总会挎上竹篮,拿上棒槌和木桶,到水库边给我洗衣服,我们儿童则在岸边的柳树下折柳条,做柳笛。
每当我们吹响了柳笛,小河边的柳笛声就如农村谁家娶媳妇的场面一样热闹,但这场景早已不复返,只留下“故人西辞黄鹤楼”般的回忆。
上学的那些年,每逢我出远门,母亲总会把我送过我们东边的水库坝,但每次都不忍心让她远送。她常说:“把你送到这儿还能采些野菜回去。”其实,我离家的时候,野菜早已遍地都是,根本用不着跑这么远的路来采,应该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吧!
从我记事起,每年春天,家里粮食都会遭遇“青黄不接”。每当这时候,妈妈就会不断挎上篮子到野外去找野菜。尽管我们的主食仍以黄面馍为主,但我们可以不断吃到吃美味的白蒿、小蒜、柳芽,榆钱、枸杞芽,蒲公英叶子,直到四五月份洋槐花开时,我们又能吃上好多树上的产品,如香椿、构树穗、洋槐花等。现在这种农村的东西早已成为城里人眼中的珍品。
令我最难忘的依然是麦收季节,父亲为农活忙得不可开交,家里又要吃面粉,这时候母亲就会一个人去推大石磨,给我们磨面,一想到她佝偻着腰奋力推磨的情景,我都不忍心再想下去。待我们会推磨后才明白这“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意。
又是一年春好处,此时此刻我突然有些不忍踩上这些悄悄钻出地面的花草。“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今天,上苍用春色把大地装扮的如迎客般的漂亮,真令人浮想联翩。
来到这熟悉再不能熟悉的田埂,这里有一片是母亲去世前,让我们栽种的一片速生杨。想当年,母亲坐在这地堰上拾掇着野菜。父亲和我,还有我的几位姐夫等五个人,一起挖坑,栽植,浇水、封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现在这片杨树林中,有的树长得已有我腰粗……如果岁月倒流,我也许会看到母亲在大田里劳作的身影。
当我们给母亲上过坟,又祭奠过我的其他祖先,我又来到母亲在世时,她给我们亲手种植的一片核桃林前,这些核桃有的在去年已挂果,大多数树干已有小碗口粗……
时光如匆匆的流水,挥之不去的依然是我浓浓的记忆。母亲生于兵荒马乱的1932年11月27日,没有上过小学……但她用她的勤劳和智慧养育了我们兄妹八个。
在前些年的春天,每当山坡上桃花盛开,我就会回来看桃花。但在母亲去世的那年春天,母亲让我把她点种的桃树苗嫁接成了新品种,有五月鲜,日本黄桃和冬桃。嫁接完后母亲很高兴地说:“你们爱吃桃,光去买怎么能行,不安全,还得花不少钱,自己种点你们以后采食随意”。然而就在我嫁接的桃树苗落叶时(2014年10月13日),母亲就匆匆地离开我们,去了她一生都挚爱的那片土地。
然,不知怎的,自母亲去世后的这几年里,我怎么也不想在这春天回家乡看桃花了,我也曾努力地写了一个关于桃花的故事,却迟迟不能完稿。每当我又提笔的时候,我已开始泪奔。母爱如山,但我没留住母爱。
在离开故乡的路上,当看到我车上的我家老二的奶瓶。我又想起刚才待我如子的三婶对我说起的事:“你母亲四十三岁生下你时,奶水少,你又偏偏食量大,吃不饱就哭声不断……你爹不断到村口的电线杆上张贴:天荒荒,地荒荒,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的小布告……你吃你妈的奶一直吃到五六岁!”我……
停不下匆匆的脚步,止不住滴滴的眼泪。很想再回到那令人心醉的母爱中,那其乐融融的亲情,那分享丰收时的欢笑、那在大坝上送我上学的场景……但这一切都被这无情的岁月中所吞噬,只留下这藏在心底深处的思念。此刻再想起她,又忍住回望故乡,山还在,我的眼泪却在飞!
(河南/曹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