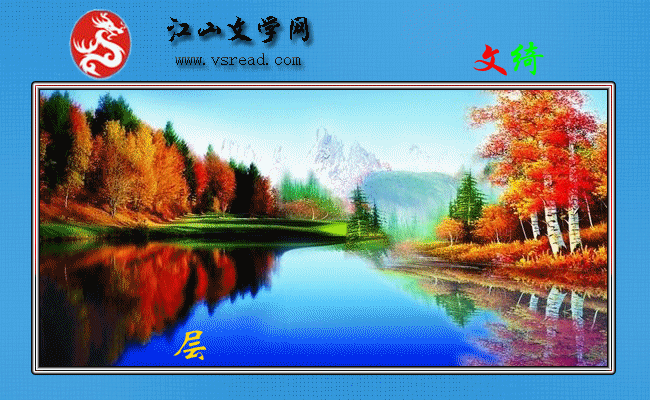【风恋】一只崖鹰的飞走(散文)
【风恋】一只崖鹰的飞走(散文)
大山给予人们的,是永远无法丈量的高度。喀斯特独有的地形地貌像无数把尖刀,耸立在西南山区的一些地方,割据着山中悠长而繁琐的日子。无声的叹息,久久回荡在远去的时光和岁月中。
随着最后一支猎枪被上缴,那只崖鹰更加肆无忌惮,似乎每只小鸡都是它固有的食物。
山里人已经和崖鹰斗了多年,那怕三叔的枪声响彻山谷,依然无法吓倒那只在天空中诡异般飞翔的幽灵。崖鹰是小鸡的恶梦,也是山里人的恶梦。身矫、麻黑、机灵、凶残,山里人给个子不大的崖鹰起了个邪恶名字,叫“麻妖子”。虽说人类是智慧的,却无法生出一双会飞的翅膀,以至于那只崖鹰来去自如。
鸡陪着山里人走过了很多年,是农家人解决燃眉之急的一次次割舍。父亲卖掉家中惟一的一只大公鸡,换回种地的种子和农药;母鸡孵出一大群小鸡,会让三叔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瘟疫中,看着家中的鸡一只接着一只死去,奶奶会老泪纵横。
那只在从半空中俯冲下来的崖鹰,残忍地叼小鸡,飞过黄皮树,飞过芭蕉林。小鸡发出“叽叽”的救命呼唤,却无法得到任何帮助。
山里的人们在咀咒着那只崖鹰。
巴掌大的土地,脚掌大的石缝。喀斯特地貌给予山里人更多的是石头,而非土地。世代居住的人们,捧起一捧泥土,艰难地走过春夏和秋冬。
一条小路从村庄通往山巅,被人们踩过无数次,以至于那些带着尖角的石块,早已被磨得圆滑可辨,并发出哀哀的嚎叫声。蜿蜒的小路上,走着土生土长的山中汉子,也走着远嫁而来的姑娘们。
有限的土地无法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大山一片接着一片被垦荒,从山谷一直垦至山腰,垦至山顶。草木下的石头露出狰狞猖獗的微笑。松鼠、蛤蚧、小鸟……山中的一切动物,被狰狞的石头一次次赶上山巅。它们的最后栖息地,是山巅上的几丛獠竹林。
偶尔,小鸟会飞到农舍边,一顿唧唧喳喳,似乎在控诉着什么。
人们不允许垦荒的土地上再长出任何野草。偷生的杂草,在秋天的玉米收获后,被割下来,收集成一堆,再点上一把冬火。光秃寒冷的大山,被剥去了最后的衣裳,像个袒露的流浪汉。半山腰那只崖鹰,在空旷的冬天里,更能清晰地辨别山下的每一只小鸡,它那罪恶的爪子时刻准备着。山下的小鸡们恐惧地躲进妈妈的怀抱里,母鸡则十分警觉地注视着天空中诡异飞翔的崖鹰。
母鸡飞了起来,但又如何能追上半空中的崖鹰?母鸡用刨食的老爪挡过了崖鹰的攻击和猎狩,护住了一只小鸡,却没护住另一只小鸡。残忍的崖鹰叼小鸡,飞过黄皮树,飞过芭蕉林……母鸡追赶着、哀鸣着,悲痛的泪水流淌着。
在崖鹰的利爪面前,母鸡丝毫没有示弱,只不过,母鸡始终没能飞起来。如同山里的人们一样,无论如何也无法搬走门前那座大山。
没有人愿意背着碳黑的农家肥爬上高高的山巅,再从山巅上背下几筐瘦弱的玉米棒子。尽管贫瘠的石缝中只适合生长母猪腾,但也被无助的人们开采出来种植了红米、火麻、南瓜……山风夹杂着细雨,吹在冰冷的石头上,大山在流泪。
无数杂草倔强地从石缝中探出,却始终没能逃脱人类的镰刀和锄头。
山里人和野草的较量,可以追踪到刀耕火种时代。
对于山里人来说,最痛恨的莫过于那些疯狂生长的杂草。它们总是贪婪地截取着庄稼有限的营养,以至于它们生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庄稼生长速度。几株几近枯萎的玉米,在杂草丛生中显得疲惫不堪。于是,人类的镰刀割向杂草,在太阳的高温炙烤下,被割除的杂草从失去生机再到干枯,最后在一把野火的燃烧下,化成一堆灰烬。
阳光雨露永远是公平的,当玉米的种子开始发芽,深藏地下的野草也在春天的雷声中猛然醒起。一场人草较量周而复始地进行着。杂草坚定大山属于它生长的地方,人类却果断地清除它们的存在。因为,那些毫无价值的杂草只会给人们带烦忧,让荒凉的玉米地一片惊恐。于是,杂草会用它们极强的生命力与人类对抗到底。一片杂草被斩除,一片杂草又在重生,疯狂的杂草会让人们精疲力竭,甚至投降。其实,人们是极不情愿与杂草斗争的。只是,为了生存,人们是不得不扛起锄头和握紧镰刀。
这一切,似乎与崖上那只崖鹰毫无关系。
疯狂的杂草丛是人类的公敌,却是飞鸟和走兽的天堂。杂草丛可提供温暖的栖息地和丰富的食物源。食物的匮乏让山中动物无法生存,松鼠会在夜里剥开刚成熟的玉米棒子,就连那只长年独居的深山老猴也鼓足勇气跑进菜园里偷走了两只南瓜,而那只来去自如的崖鹰已习惯趁人不备时俯冲向小鸡。有时,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真的显很渺小。无法在夜里一直守候着玉米地,无法知晓那只老猴子是何时溜进菜园的,更无法追赶上那只会飞的鹰。
因为人类可以改造自然。所以,在一切动物之中,人类永远是最聪明的,也是最可怕的。就像那只目空一切的崖鹰,哪怕有锋利爪子,也不敢和人类近距离交战。
于是,人们挂起一件破旧衣物,再在衣领上放置一顶破草帽。一根长竹竿挂着“假人”树立在家门口,山风吹起,破衣物破草帽像如人形晃动,一时间吓唬了崖鹰。只不过,饿极了的崖鹰还是会俯冲到地面。以至最后,那舞动的破衣物和破草帽失去威慑作用,像一只没有任何力量的孤魂,扭动着慵懒身子,根本无法吓走那只已然看穿的鹰。
山里人商量着,一定要除掉那只崖鹰。装机关、敲盆吓、用枪打。可是,那只诡异的崖鹰依然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着,像一只永不消失幽灵。一杆老旧的火铳就像放了一个大鞭炮,喷出一团永远无法到达半空的火焰。山里人甚至把刚孵出的小鸡染成红色、绿色,以此蒙蔽崖鹰,可好景不长,狡猾的崖鹰再次识出人类的诡计。
再也想不出任何办法对付那只凶残的崖鹰,只能咀咒着它早些老死或病死。
土地是山里人的命根子。其实,人们是极不情愿去耕种那石头成堆的巴掌土地和脚掌石缝的。只是,无能为力的大山无法提供任何一方沃土。
石头主宰着大山,每到一处,都可看到成片的石头,大的、小的、高的、矮的、长的、短的……每座山上都是奇形怪状石头,土地似乎只是大山夹缝中附着物。
坚硬的石头死死地压住大山,也压住山村无法喘息的日子。
苍莽的大山,让人看不到任何希望,尽管土地已垦至最高处,仍然无法满足一日三餐的需求,几筐瘦弱的玉米棒子,坚硬地刻着“贫穷”二字。贫瘠的土地,让山里的人们一声又一声地叹息着!
人们斗不过疯狂生长的杂草,也赶走那只会飞的崖鹰,心情像极那方四角天空的愁云,绝望的情绪在巴掌大的土地上和脚掌大的石缝中蔓延着。杂草决定向人类发起总攻,它们疯狂地霸占着大山的每个角落,顽强的根须牢牢地缠住每一块石头,让镰刀和锄头瑟瑟发抖。
那片远在山巅的石窝地,长满的芒草,无数根针芒像一把把锋利刺刀,好像在警示着山里的人们,此处不准踏入半步。去往山巅的小路上,各种藤曼交织着,再也无法行走。
一番辛勤耕作,却只种上几株长不大的玉米。山里的人们不再将全部精力集中在那几片贫瘠的土地上,纷纷走出大山,走向工地、走进工厂,勤劳和汗水正在努力谱写山村的变迁史。
国家退耕还林政策像一阙旋律高亢的歌声,在莽莽大山深处回旋着。人们纷纷把土地还给大山,把杂草灌木还给山中动物。大山重新披上绿装,狰狞猖獗的石头被重新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植被。
世代耕种的土地,再也分不出棱角,荒乱的杂草疯狂地生长着。大山变回原来的模样,飞回一群群多年不见的小鸟。虽然巴掌大的土地和脚掌大的石缝让山里人吃尽苦头,但些贫瘠的土地也曾经养活着一代又一人的人们。只是,生存的压迫超越了对山村的依恋,纵有百般不舍,山里的人们还是挥手告别大山。随着国家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实施,山里人纷纷响应号召,搬出大山,告别古老的土地,也告别爬山涉水的日子。
人去楼空,大山显得更加宁静,山中小鸟自由地飞进农舍,又是一顿唧唧喳喳。
父亲依然居住在山里,他说他喜欢清静。对于父亲的决定和选择,我十分尊重。因为,山里有我童年爬过的每一座高山,有我童年走过的每一条小路,有我童年我举起镰刀割向杂草的日子。虽然工作忙碌,但我依然会抽出时间回山村看望父亲,是义务也是责任。父亲养了很多鸡,生了一箩箩的鸡蛋。一群小鸡仍然在母鸡的带领下,走向杂草丛。
我问父亲:“‘麻妖子’还来吗?”
父亲说:“山上已经有它足够的食物,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