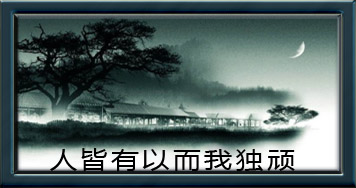【江山·恒】【流年】永远年轻的歌(散文)
【江山·恒】【流年】永远年轻的歌(散文)
![]() 夏日的午后,三点半多,小区大门外东北边的树荫下,常常围坐着七八个鹤发鸡皮的老人,每天下午到这儿报到,是她们必修的功课。
夏日的午后,三点半多,小区大门外东北边的树荫下,常常围坐着七八个鹤发鸡皮的老人,每天下午到这儿报到,是她们必修的功课。
年逾八旬的老妈,是其中的一员。她们分不清谁姓何名啥,见了面笑呵呵地喊着“嫂子”“大妹”,热情打着招呼,有着相同时代经历的她们,在一起,永远有说不完的话题。
那天傍晚回家,老妈很是兴奋地对我说起,今天两个九十多岁的老人一起唱歌了,歌名是《十二月里》。开始时是那个九十四岁的弯弯腰的老人在唱,这个老人,儿子的房屋是城中村,被拆迁,现在住在一个地下室——实际是楼的最下一层,门口就是小区外,只是家里没有窗户罢了。老人年轻时不知怎样落下病根,不敢独自一个人待在屋里。年近七旬的儿子每天要出去找生活,她就一个人呆在屋外,尽管已是夏季,她还穿着棉袄,因为儿子早上走时是四五点钟,空气还很凉冷。晚上有时我们出去散步,即使是冬天,也会看到老人坐在门口的沙发上打盹——沙发是儿子从垃圾堆捡来的。看见人了她就热情招呼,过来坐坐。夏季的白天,相对来说老人还不太寂寞,街上人来人往,半上午或者半下午,她提着马扎,蹒跚挪移到她家门口不远处的雪松树下,和周围一大帮年龄相近的人闲坐一起,或静默,或讲述她们经历的过往。
那个刘老师的婆婆也唱歌了。老妈绘声绘色比量着老人唱歌时的情形——她说,我要站起来唱。一边唱,还一边挥着手给自己打拍子,她七十多岁的媳妇坐在那儿,也给她打着节拍,还时不时为她鼓掌。老妈慨叹,人家93岁了,记忆力真好,歌词那么长,都记得清楚着呢。
老妈说的这个老人,我知道,是我婆婆村的,我喊她大妈。老人家满头白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微微佝偻的腰身,记录着岁月烟尘的沉重与威压。她皮肤白皙,穿着整洁,举止优雅,时常戴一副红框眼镜,更增添了她身上知性的气质。打眼看去,尽管满脸皱纹,但面色红润,猜不出她已经有九十多岁,也不像是在农村苦巴苦业生活了几十载的农民。上了年纪的她,经常被孝顺的大媳妇搬到城里来住,但是老人还是牵挂着农村的儿子,农忙时,就回了老家,为农村的儿子媳妇尽力帮点忙。这不,大樱桃采摘时,她又回老家住了四十多天。她的大儿媳,心疼她在农村生活苦累,樱桃季刚过,连忙接她回城,再次开启陪伴她的日子。坐累了,陪她走走;冷了,给她添加衣服。老人一说要回家,立马提着凳子陪她走。
每天,头发花白个子小巧年逾七旬的儿媳,跟在头发雪白身材高大的婆婆身旁,提着凳子,拿着外套,带她一起出去,或走,或坐,这,成了小区的一道风景。
老妈每天回到家,时常告诉我关于老人的新消息:她脑子真好使,问我多少岁,我一说84了,她立马就说,我比你大9岁,我93岁。她还认识字呢,今天走到商店门口,非得喊我过去坐坐,在那儿坐着,她看到门口摞着的纸箱上的字,就读出了声。
一天喝喜酒回来,见老妈没在家,我出去找。在住地下室的大姨家的门口,看到了她们。那时,她们在唱歌。先是家住那儿的大姨唱。听母亲说,老人也是老党员,十九岁入党,但是党员证丢了。老人腰佝偻着坐在那,声音轻细,曲调婉转,咬字清晰,十二段歌词,居然不打艮一直唱到底,全然不是一个人昏昏沉沉打盹时的模样。我忍不住拿出手机录了起来,心里钦佩,九十四岁的老人,记忆力真的不错。唱完,刘老师笑着说她婆婆,该你唱了。老人果真利落地站起来,大声唱起来,那声音,那气势,不亚于年轻人,她一边唱一边有力地挥动着手臂,仿佛在指挥着千军万马。唱着唱着,偶尔停顿一下,她的媳妇就说,该唱八月了,老人洪亮的声音就再次响起。此时此刻,老人白皙的脸庞洋溢着激情,她精神矍铄,眼睛亮晶晶的,仿佛回到了她歌声中的岁月。
我把拿着的喜糖分给周围的老人,给唱歌的二位又单独加了一颗,开着玩笑,说,这是你俩唱得好的奖品。老人开心地笑着,谦虚着,唱得不好。
回到家,我百度《十二月里》,找不到和她们唱的一样的歌词。根据脑子中记着的几句歌词,觉得和送郎参军有关。
再次在小区东的树荫下看到婆媳俩,说起大妈唱的歌,老人又情不自禁唱起来。交谈中,刘老师说,政府派人到老家去采访婆婆,她是老党员,还做过青年妇救会主任。我很惊讶,目光投向歌唱着的老人,这时忽然发现,站着唱歌的她,胸前别着枚红彤彤的党徽呢。歌曲唱罢,我随意问了几句:“大妈,您哪一年入的党?”“四七年。”老人家张口就来,接着补充,“那年我十九岁。”“您为什么要入党啊?”“人家村里干部叫俺入就入了。刚开始找俺,俺害怕,不敢入,吓得直哭,后来在俺姐夫家看到那个小本本——”(“是党章。她姐夫也是党员。”刘老师解释。)老人继续自己的话题,“俺姐夫说,是积极分子才让我看那本本的,我就入了。党员的活动要上避父母下避妻,干部要我们开会,都是偷偷找个场,不能让人知道的。”“哦,那你们党员都干些什么事啊?”“上面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俺这个人忠诚老实,上面布置的事从来不会打艮。”老人回答很干脆,但也太笼统。她有一搭没一搭说着,我认得字,也会算数,土改时,上面安排我参加了地主财产清算工作。区里开大会传达上面指示,我识字儿,每次我都要记下来,回村开会时好帮着村主任传达。白天干活,晚上开会,或者教村里的老百姓识字,那时候年轻啊,也不觉得累,浑身老是有使不完的劲儿……呵呵。老人瘦瘪下去的嘴咧开,笑得很爽朗,眯缝着的眼里流露出满满的自豪。还有……老人好像一时想不起来了,刘老师启发道:“你忘了你和我说过你们抬轿到黄庄?”“哦,那是送村里的小年轻去参军。”我想象着那个场景,年轻的大妈和村里的青年妇女四个人一组,抬着胸前别着大红花参军的男青年走在山村的小路上,她们依依不舍地把子弟兵送往部队,送上前线。之后她们在家耕种土地,照顾父母孩子,为前线备粮,备衣,心里牵念着抗战的郎君,于是,凄婉的曲调在心里响起:“正月里来是灯节,抗日郎君把家撇。一场风来一场雪啊,不知郎君冷和热。”心中的牵挂尽在不绝如缕的歌声中。
大约唱歌让大妈来了兴致,她开始滔滔不绝地说着她们那个时代的事:“我们在家搞生产,种地,纺棉花,开会,拉形式(就是以前说的拉活报),踩高跷,教老百姓识字……”刘老师补充问:“你抱着一岁的学英到那个黄庄去干什么?”“去培训五六天,回来给村里人当老师,教着识字啊。哎呀,孩子小,得吃住那里,我说不能去,可村干部说就我行,我只得去。”老人说到村干部说她行时,言语中透着骄傲。我想多问点这位老党员为革命做的事,老人一直的说辞是,上面叫俺干啥就干啥。也许,老人讲不出什么豪言壮语,但是,可以想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妇救会主任,她一定是克服了重重困难,冒着危险,带领村里青年妇女积极完成上级领导交给的任务的,为年轻的人民共和国诞生洒下了自己的汗水。
我正思绪万千,老人停下话题,兴奋地告诉我,俺今天上午去开会了,人家政府的人讲话,发给了这个——她骄傲地指给我看她胸前佩戴的党徽,还照了相,一人发了一个大蛋糕。“您自己戴上的还是政府的人给您戴的?”“她给我戴的。”她伸手指了指儿媳。七十四岁的儿媳也是党员,她性格开朗,贤惠孝顺,和婆婆关系亲如母女,听了婆婆的话,她开着玩笑:“嗯,我是你的免费保镖。”大妈听了,伸手去打儿媳,开满菊花的脸庞斟满笑容,那娇嗔的神态,宛如小姑娘。
“十二月里来一整年啊,抗日郎君把家还。进门先问爹妈好啊,再问哥来后问嫂。掀开门帘问贤妻好啊,你好我好大家好。”歌声再次飞扬。
使劲挥舞着手臂,重重强调一句“你好我好大家好”,老人缓缓坐在了小凳子上。但情绪依然沉浸在年轻时代的歌声中。
我翻阅着老人儿子冯老师为采访老人者整理下的歌词,心潮澎湃。歌词中展现了抗战时期后方妇女做出的巨大牺牲,她们的丈夫在前线浴血奋战,年轻柔弱的她们在后方忍受寂寞,忍受苦难,生产劳作,支援前线。正是这些无私无畏的中华好儿女的奋勇抗战,勇于牺牲,才迎来了崭新的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今天,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的日子里,飘过七十多年岁月的抗战家属闺中吟,使我再次感受到先烈打下的江山来之不易。让我们珍惜美好的新时代,牢记先烈的光辉业绩,用实际行动来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我们伟大的党光辉精神万年流传,鲜艳党旗高高飘扬。
附十二月里歌
(抗日家属闺中吟)
正月里来是灯节,
抗日郎君把家撇。
一场风来一场雪啊,
不知郎君冷和热。
二月里来青草发,
抗日郎君不挂家,
家中撇下四瓣菊啊
外面恋下牡丹花。
三月里来三月三,
桃花杏花开满园,
蜜蜂采蜜扬长去啊,
撇下花心受孤单
四月里来四月八,
娘娘庙上把香插,
人家插香求儿女啊,
奴家插香救丈夫。
五月里来午端阳,
大麦上场小麦黄,
人家有人晒麦场啊,
奴家无人翻麦秧。
六月里来热难当,
奴在绣房热得慌。
有心找个风凉场啊,
婶子大妈说张狂。
七月里来七月七
天上牛郎配织女,
你在东来我在西啊,
不知郎君在哪里。
八月里来月儿圆,
西瓜月饼敬老天。
人家敬天有人敬啊,
奴家敬天真可怜。
九月里来九重阳,
糯米造酒菊花香。
人家造酒有人喝啊,
奴家造酒无人尝。
十月里来十月一
从南来了个当兵的。
银钱捎来十八两啊,
捎给小奴做衣裳。
十一月里来十一月冬,
房檐滴水冻成冰。
伸腿冷来蜷腿空啊
千层被褥不压风。
十二月里来一整年啊,
抗日郎君把家还。
进门先问爹妈好啊
再问哥来后问嫂。
掀开门帘问贤妻好啊
你好我好大家好。

谢谢您读拙文并真诚留评。
祝愿您福寿安康!
《十二月里》,永远年轻的歌,唱歌的人,也有一颗永远年轻的心!

灵魂对晤、以心悟心,逝水的时光变得更丰盈和饱满。
善待别人的文字,用心品读,认真品评,是品格和品位的彰显!
我们用真诚和温暖编织起快乐舒心、优雅美丽的流年!
恭喜,您的美文由逝水流年文学社团精华典藏!
感谢赐稿流年,期待再次来稿,顺祝创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