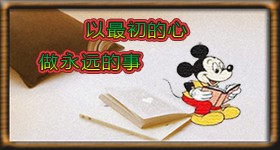【流年】红方(小说)
【流年】红方(小说)
![]() 江水平缓,暗中涌流,浪花相互追逐。水湾处,水平如镜。一只水鸟从岸边深草里游出,一条鱼突地跃起,又落水里。水鸟折回,隐入草丛中。歇在草上的蝴蝶,受到惊吓,铺展双翅,飞掠而起,从江边女子头顶上飞过,往对岸去。
江水平缓,暗中涌流,浪花相互追逐。水湾处,水平如镜。一只水鸟从岸边深草里游出,一条鱼突地跃起,又落水里。水鸟折回,隐入草丛中。歇在草上的蝴蝶,受到惊吓,铺展双翅,飞掠而起,从江边女子头顶上飞过,往对岸去。
女子叫阿娥,正在码头青石板上洗衣服。她羡慕这只蝴蝶,要是她能变成蝴蝶,一定满世界去寻找他。即使寻不到人,尸骨也要找回来。他一走两年多,没有一丝音信。妈妈说,兵荒马乱的,也许已不在人世。阿娥不信,他不会死,不会丢下她,他那么喜欢她。
阿娥其实才二十二岁,可很少见到她的笑容。她怕人多的场合,人们打情骂俏,笑个不停。她笑不出来,她总是愁的,脸是垮着的。她知道有人背后对她指指点点,说她是哭丧脸。这又会怎样,哭丧脸咋啦,为她装在心里的男人哭丧有什么呢?
阿娥心里装的男人叫阿山。她与阿山在这儿第一次见面,也是在这儿送走了阿山。从此,她天天来这儿洗衣服,眼睛时不时飞到对岸,搜寻那个熟悉的身影。码头围栏外的蔷薇花开了,谢了,又开了,又谢了。这个古老的渡口,从她记事起就叫哭丧码头,凡有心事,丧亲心痛的女人,都会来到这儿对着江水嚎啕大哭,或无声痛哭,成了这个地方的习俗,也就有了哭丧码头的称呼。阿山走后,阿娥思念他,想得心疼,她就来这儿哭。哭了,不疼了。心又疼,她又来哭。
泪眼模糊中,她似乎看到了阿山。
她与阿山第一次相遇让她觉得仿佛在梦里。那天是4月27号吧,码头沐浴在通红的朝阳里,像一位刚从甜梦中醒来的美俏新娘,粉面烟霞。四月的晨,清风顺南盘江而来,落在人身上。盘江两岸,盛开的蔷薇花迎风绽笑。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蚕豆、香椿芳香,是从过江的小船上飘来的。赶早的人,要去赶珠街,好将蚕豆、香椿卖个好价钱,再买回需要的货物。心细的男人,也会给自己的女人买点女人用的东西。一轮红彤彤的太阳,从老东山翻出。道道金光像一支支利箭插入南盘江中。顿时,江水与天空之间,像拉起数不清的彩色天梯,幻得炫目,让阿娥觉得身处仙间。
阿娥还未缓过神来,有人大喊:围巾冲走了。
喊话的人是一个不认识的小伙子。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河面,阿娥最喜欢的红色围巾顺水流出一大截。阿娥急了,哎呀叫了起来,咋个办?
好办,看我的。小伙子笑着说。他一纵跳到一只小船边,取过船头的一节长竹竿,紧跑几步,伸出竹竿,将水里的红色围巾挑了起来。听他口音,这不是曲靖县人,有些像平彝县人。小伙子,穿蓝色衣裳,黑色裤子,布鞋,戴着一顶破旧的篾帽。中等的个子,普通的模样,但有一双明亮清澈的眼睛。
阿娥说,谢谢。小伙子已来到身边,红红的脸,笑眯眯的,捧着红围巾,像捧着一团火。她接过,有些不自在。小伙子嘿嘿笑了起来,轻轻道,我从平彝营上那边过来,想向你打听一下,珠街这边卖盐的商家,往哪走近?
你问对人了。过了江,出了码头,走右边的路,然后是一片稻田,穿过稻田中间那条路,便是盐村了。做盐生意的人家不少呢。阿娥自己都惊讶,面对一个陌生人,怎么说了这么多。她突然有些不好意思,双手不自然地伸进衣袋里,触摸到那个煮熟的鸡蛋。今天是她的生日,妈妈煮了两个鸡蛋给她,路上她吃了一个。阿娥灵机一动,拿出鸡蛋朝小伙子递过去,说,谢谢你帮我,这个鸡蛋你吃。
小伙子也不客气,接过,笑着说了一句谢谢,转身,走出码头,很快不见了。阿娥蹲下身,收好围巾,接着揉起衣服。她自己也不清楚,小伙子的形象怎么也揉不掉,她由不得地脸热了起来,赶紧四处瞟了一眼,没人注意她,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
阿娥来码头洗衣服更勤了,妈妈说她衣服不是穿烂的,是洗烂的。连续几个月没有在码头见到小伙子,阿娥心里空落落的。也许,他早回了营上,也许去了更远的地方。
阿娥再次见到小伙子,是半年后深秋的一个雨天早晨。珠街坝子一片枯黄,捆好的稻草码成草垛,堆放在田里,割口整齐的水稻根一撮一撮排列,与草垛对望,仿佛恋恋不舍。
阿娥的心也如此,她揉着衣服,眼睛时不时瞧一眼码头对面。一个小时过去了,衣服洗完了,她呆呆坐着。不会出现她脑中的场景,她红红的心像稻草一样枯黄了起来。直到冰凉的东西不断打到脸上,她才发觉,下雨了。竟然没有带伞,这几天丢三落四的,她在田埂路上慌慌跑着,端着盆。天灰蒙蒙的,东山上空黑茫茫的,雨还会更大。远远过来一个人,走得很慢。好奇怪的人,似乎不怕雨。田埂上很滑,雨沙沙的,雨滴落在田里,打在草垛上,发出不同的声音。一声闷响,阿娥吓了一跳。那人摔倒了,躺在田里。摔倒了起来啊,怎么还躺着?阿娥紧跑了几步。来到跟前,阿娥一声惊叫,端着的盆“嘭”一声掉了下去。这不是那个小伙子吗?身上有血,混着雨水,流进田里,把田都染红了。怎么办?他一定伤得重,痛晕了,不然这么大的雨,躺在田里却不知。阿娥四处看看,哪有什么人影子?雨更大了,昏暗的田野里,两个黑乎乎的影子合在一起,雾茫茫中,朝远处缓缓移动。
阿娥背了个人回来,水滴水淌的,可把阿娥父母吓坏了。他是哪个?声音有些慌。
爸妈,我也不知,他昏倒在路边,我不能见死不救吧。以前我见过他一次。阿娥不想隐瞒父母,还是说了出来。
阿娥父母不再说话,说什么呢?人都背回来了,女儿大了,自有她的心思。阿娥父亲替小伙子换完衣服出来说,伤得不轻,赶紧找大夫。说完也不等回答快步走了出去。
忙腾到半夜,送走大夫,阿娥催促父母赶紧去睡,说她背回来的人她照顾。阿娥父母没有再说,由着女儿吧,只是不能让外人知道收留了一个不明来历受枪伤的人,兵荒马乱的,就说是姑妈家儿子,阿娥的表哥来珠街做生意病了。阿娥的姑妈嫁得远,平彝后所梨树坪那个方向,挨着贵州,有谁会去打听真相呢。
这事让阿娥的姐姐知道了,她叫上自己的男人急忙赶来盐村,小伙子躺在床上还未醒来。
不是表哥啊,姐夫说。
是他,就是他。姐姐吃惊地大喊。望着姐姐和姐夫一惊一乍的表情,阿娥糊涂了。姐姐说,你姐夫以为是表哥,现在看了不是,可能后悔跑这一趟,家里有许多活要做。这个小伙子,他救了我和儿子。谢天谢地,妹妹救了他。
全家人睁大眼睛望着姐姐,满屋子的迷惑。姐夫反应过来,沉沉地说,你姐在山脚那块地里忙活,得贵在地埂边玩,突然来了两个男人,凶巴巴的样子,把你姐拖进沟里,得贵吓得大哭。别喊,你不顺从杀死你儿子,其中一个男人粗暴地打了你姐一嘴巴。老天长眼,就是这个小伙子,这个时候提着手枪跑了过来。你姐吓得头也不敢抬,抱着得贵躲在地埂下。后来响起来枪声,那两人往山里跑了。小伙子叫你姐领着得贵赶紧回家,防止那两人返回,说,他们是土匪。你姐领着得贵慌忙离开,连声谢谢都吓得忘了给人家说。没想到他为救你姐与得贵中枪了啊,阴差阳错,这是恩人啊。姐夫说到这儿突然压低声音,他有枪,可能是搞革命的。
啊?阿娥父母听了,慌忙出去看了看,除了一条看门狗在睡觉,四下没人,赶紧关上院门。
小伙子是两天后才醒来的。阿娥正靠在床边打着瞌睡,俏长的脸型白里透红,双眼合着长长的眼睫毛,粗粗的两根黑辫子搭在胸前,一身花布衣裳,每个扣子处绣有一个展翅的红蝴蝶,好像要飞。阿娥两只手叠着平放在面前的红围巾上。小伙子想起来了,脸上露出笑容,他双手杵着床坐起来。床咯吱一声,阿娥醒了,忙说,别动,你伤没好,再休息几天会好的。
不行,我得马上走。小伙子说着,移动身子,要下床。
阿娥起身阻止,她想起姐夫说的话,理解他,说,那也要等你能走啊,说着低下头,两朵红云落在脸上。这里很安全,我对人说你是我表哥,后所梨树坪姑妈家儿子。你别担心你的包裹,我收在外面一个人找不到的地方,你伤好后,我领你去拿。
小伙子望了望眼前的女孩,那双大大的眼睛忽闪忽闪的,眸子里有自己的影子。他心里一阵热,来了精神,仿佛伤已好了。我叫阿山,平彝人。他笑了,不再拘束,仿佛在自己家里一样。
阿娥给他扯了扯被子,说,我叫阿娥。你睡了两天啦,我给你煮个红糖鸡蛋,补一补。说完起身走了出去。阿山的眼睛跟着,也出去了。
床沿放着阿娥的红围巾,阿山觉得满屋子都红了起来,他拿过来,柔柔软软的,那天在码头的一幕,仿佛从红围巾里绽放了出来。要不是那天有事情,很想与她多聊几句。事情就那么奇巧,受伤后没有多想,朝这儿逃来,昏倒在路上。偏偏被她遇到了呢?冥冥之中仿佛有种期待。她叫阿娥,多好听的名字呀。阿山高兴得忘了自己是伤号,疼痛让他回到现实。不行,必须尽早离开这儿,在昆明办事掩护同志,被国民党特务认出,逃回的路上遇上两个土匪要对一个女人非礼时不得不出手,虽说救了那个女人和孩子,还伤了土匪,但自己也受了伤。如果被国民党特务知道这事,定会反应过来,追到这里,那就危险了,更会牵扯到阿娥一家,给他们带来灾难。
阿娥哪里知道阿山这些心思呢?她煮好红糖鸡蛋端来,说,你吃,我还要给你换药。大夫已经交代我如何换了,换完药,还要倒药汤给你喝。大夫说,好在没有伤到要害处,养一段时间就好。你不要多想,好好养伤,反正是在家里。阿娥突然觉得最后一句话有些那个了,顿时脸发烫,红得像床上的红围巾一样,忙低下头取药,不敢看阿山。
阿山心里咯噔一下,眼前这个女孩子对他来说有一种说不清的喜欢,他也没有多想,轻轻说道,好。他还告诉阿娥,他没有婚配,今年二十四岁。低着头的阿娥,脸红到耳根,心怦怦乱跳,仿佛有一只小兔子在里面,她也轻轻应了一声,好。除了心跳声,屋子里再无声音,只有满屋子的羞涩。
阿娥的母亲颠着身子,两只裹得蓝莹莹的小脚落地不出声,小跑到屋外耳房。耳房前,阿娥的父亲正在铡牛草。一捆一捆的苞谷杆碎成小节小节的,拴在柱子上的老黄牛嚼着,时而拱拱,时而卷卷舌头。
他爹,好,好,都说好。你没发现阿娥这几天手脚都是欢的。阿娥母亲扯着阿娥的父亲衣服,说完嘴也合不拢。
什么好啊?还不好,还要再铡才够牛吃。阿娥的父亲说完又塞一捆在铡刀下。
我说他们好上了,阿娥与那个小伙子。阿娥的母亲脸上开成一朵花,像墙角的山菊花。
阿娥的父亲望着山菊花,咧开了嘴。
从此,阿娥的父母每晚早早歇了,天亮就出门,直到天黑才回来。按阿娥的母亲的话说,让他们两人多待会,阿山不会在这儿养伤太久,如果阿娥姐夫说的是真的,那他的心一定大,天地更宽。也许是年长的人经历事情多,还说准了。阿山只待了五天,任阿娥挽留都要走,说再待下去会出大事的,为了阿娥一家人的安危,必须尽早离开。阿娥哭成泪人,阿山没有告诉她真相,自己的真实身份,怕吓着她。当然,出来执行任务时上级也交代,身份保密是确保生命的前提,活着才能完成任务。伤未痊愈,但必须得走。
天阴沉沉的,深秋的晨,冷风如刀。阿娥把自己的红围巾送给阿山,她轻轻给阿山系在脖子上。阿山把她揽过来,紧紧抱住,说,我会来看你的。说完转身离去。这回,他没有走码头,身影消失在珠街东山的方向。
阿娥没有想到,阿山这一走,就是两年多。
阿娥父母知道女儿相思的苦,自己的女儿他们最认得。阿娥呀,你还是看开些,这个年头,乱世,今天不知明天的事。妈妈的声音很细,很慢,但阿娥不敢相信。她只听得爹爹背着她常常叹气。一次无意听到爹妈在房里小声议论,阿山是共产党,阿娥姐夫在昆明看到通缉的照片,认出是阿山。她明白了,难怪妈妈会说兵荒马乱的,也许不在人世了。
阿娥话少了,人们常常看到她垮着个脸,仿佛脸上蒙了一层灰云,端着衣物去码头洗,边洗边哭。她下了决心,如果阿山不在世上了,她就不嫁了,守爹妈一辈子。
四月的珠街坝子,一块一块的稻田青汪汪的。到处是布谷鸟的叫声,叫一声绿一片,叫一声又绿一片。阿娥端着洗好的衣服,站在田埂上,呆呆望着阿山受伤跌倒的地方,仿佛多望几眼阿山就会跑出来。
妈,我回来了。阿娥进门看到妈妈在院子里切猪草,喊了一声,便放下盆,把洗好的衣服晾在竹竿上。阿娥,爹来了。看爹给你带什么来了?阿娥一回头,爹捧着大朵大朵红通通的马樱花。啊,马樱花,真美,我最喜欢的。阿娥终于露出笑容,从爹手里接过,使劲闻了起来,寡白的脸颊有了红色。爹知道你从小就喜欢马樱花,老辈人说,马樱花能给人带来好运。爹顺道就给你摘来了。阿娥的父亲没有对女儿说真话,他是看到女儿闷闷不乐,生怕闷出病来,故意上山摘来的。
阿娥躺在床上,这张床是阿山睡过的。她把花放在耳朵边,仿佛聆听花语,探出阿山在哪里。枕着花香,她渐渐入睡了。
是一阵敲门声搅碎了阿娥与阿山在梦境里的相会。这样的梦境数也数不清到底做了多少回,几百回吧。
这是我参加我们当地建党一百周年的征文,有幸获得二等奖,特发在流年,以便得到江山文友指教。
你评的正是我的主旨,不能忘记初心。初心是我们永远的红色方向。
灵魂对晤、以心悟心,逝水的时光变得更丰盈和饱满。
善待别人的文字,用心品读,认真品评,是品格和品位的彰显!
我们用真诚和温暖编织起快乐舒心、优雅美丽的流年!
恭喜,您的美文由逝水流年文学社团精华典藏!
感谢赐稿流年,期待再次来稿,顺祝创作愉快!
山哥真棒!

主题正是你说的。谢谢。也是我对党的百岁生日的献礼之作。
红方,寓意恰如、情意绵长,紧扣双重题旨,加之笔触洗练、遣词生动、情怀挚热,一篇爱国爱党爱民之文艺作品自然华彩倍出。已然佳作难得,却忍不住奢望:如若在人物、事件的背景与细节上更多一些以人性为元素的谋篇布局,《红方》定然不负情感错综、境遇扣人心弦而又引人入旨之厚重之作。拜读佳作,致敬作者。
慧眼,您的意见弥足珍贵,应该在这方面下功夫。
我会仔细品味您的建议。

向二哥学习!
这篇小说,我还是喜欢的。
终于获得二等奖。同乐!
在小说里,如鱼得水,哈哈。
不过还是有差距,写得不如意,还得继续努力。
与子青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