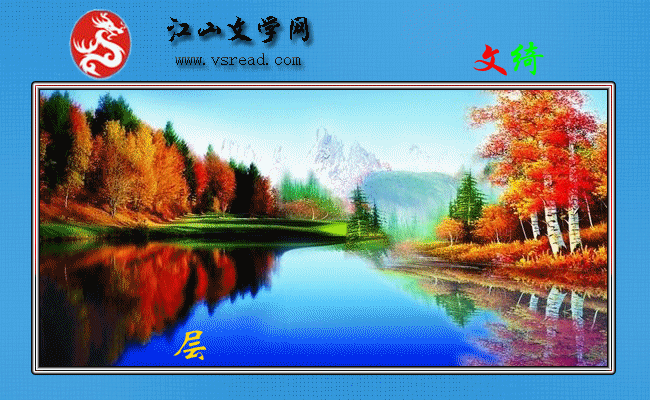【风恋】春叶,大山的轮回(散文)
【风恋】春叶,大山的轮回(散文)
桂西大山的春天来得慢,本是立春时令,但山间依然不依不饶地飘着一团寒雾。草木依旧没有发芽的意思。偶尔,一场让人分不清是冬雨还是春雨的雨,似冷非冷,淅淅沥沥,模糊了山中的季节。
本想抽点时间回趟山村,邂逅大山的春天,感受春回大地那漫山遍野的生机。然而,因为新冠疫情防控原因,再加上工作繁忙,一扫赏春心情。于是,我只能用记忆去沉浸大山的春天,感受一年一度季节的召唤。
山里的春天,最大的变化是各种树木都会发出新叶,这种新叶除了给人希望,更多的是一份轮回的到来。
春天又回来了,她不以大山的贫瘠而远去,也不以山村的落魄而逃离。她总会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季节,春风拂面、满树新芽。
深山的气象,春天不一定都是如花的季节。比如,梨花总会开放在寒冷的冬风里,而山茶花早早就绽放在霜降前后。所以,我对春天的印象,更多是停留在春风里,停留在老树新芽的喜悦中。
到过很多地方,走过一季又一季的春天。只是,城市的树木似乎感受不到春风的惊喜,那些四季常青路树没有发出多少新叶。
我不会责怪城市的树没有张开热情的怀抱去迎接春天,因为,城市的树有着它们的使命,那就是常绿,它们忘记了春天是个开花和长叶的季节,它们只能用永不褪去的绿,换取在城市中站立的机会。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对城市的树是同情的,就像冬天,树应该毫无牵挂丢弃每一片落叶,而城市的树却要竭尽全力地去维护每一片树叶的完好。偶尔,城市的一棵落叶树也会发出春天的新芽,但绝对不是乡间那棵千年古枫。
对于山村的春天,漫山的种种新芽给人的感受是一个季节轮回的亘古。
唐代诗人李白的“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生动地诠释了“亘古”的概念。我想,山村的四季也一样,今天的人们看不到古时的春天,但今天的春天一定也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古人们。于是,我对季节便有了敬畏,一种亘古的敬畏。这种敬畏让我释怀、宁静、回归。
曾几何时,大山是快乐的。比如,湿润的森林里长满蘑菇,经流不息的山沟里藏着螃蟹,还有那些深不可测的喀斯特溶洞里流传着一个个古老而神秘的故事。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有限的土地无法满足人们生存需要。于是,一片片森林在山火的作用下变成了可种植的土地,还有,那四季常流的溪水变成自来水引进农舍。蘑菇越来越少,小鱼几近绝迹,那些充满着古老故事的溶洞越来越可怕。
为了生存,人类没有错。只是,我无法找出让春天叹息的理由。比如,那一树树的新芽被满地青草所代替。尽管青草也是春天的一个元素,但过于单调的一地青草并非春天该有的全部。事实上,满树的新芽更能表达春天的喜悦,原因是,山里的人们总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除掉土地上的杂草,这种人与草的斗争在山村上演了千年。
本来对乡间小路上的杂草有着几分怜悯。比如,它们在冬天的冰霜里黯然死去,干枯着没有生命的身子,等待春天,等待春天再次赋予它们生命。
一片草叶在春寒料峭中的生存需要坚强和勇气。只是,山里人不会在意一片草叶的生长过程,他们更在乎的是土地上生长着庄稼而非杂草。于是,人类和杂草的较量在可耕种的土地上一直进行着。这种较量是一种生命的生存和另一种生命死亡的较量。
人们会将土地上生长的杂草毫不犹豫地去除,而那些本可拥有春天的各种野草会在长叶季节失去生命。这种生命的失去对人类而言,是可喜的。因为,人类希望土地上永远生长着最绿油的庄稼。
树没了,草也被一遍又一遍的去除。我对春天概念变得模糊且单一。
春天本来是个百花齐放、草长莺飞的季节。然而,因生存需要,大山的春天变成了树不断被砍伐,草不断被去除的斗争。这种斗争让春天变得繁忙而沉重。还好,村头那棵千年古枫没有被砍倒。这缘自大山的一种信奉,那棵千年古枫被敬为神树。神树有着不可侵犯的威风。我本想用“威严”去描写山里人对神树的信奉,但我觉得这是一种愚昧。
山里人对神的敬畏来自害怕而非尊敬。在我看来,神权并非主流,神权对人类的禁锢总有一天会被解除。只不过,我只是一个来自大山的孩子,也是一个被神权禁锢的受害者。在我的内心里,自小便种下对神权敬畏的阴影,这种阴影也一直笼罩着我。
父亲曾说,“世上没有鬼”。只不过,我还是怕鬼。虽然神从一定程度上说比鬼慈悲,只是,一些恶神比鬼更可怕。这种可怕表现在:人可以与鬼斗,但不能与神斗,只能永远诚服于神。所以,山里人对神存在着“畏”的心理特征。
村头那棵千年古枫被赋予神树的地位后,没有人敢去碰它的一枝一叶,就连靠近都需要一定勇气。因为,对神树的不敬会带来灾难、疾病、死亡。于是,一种表面敬重却又心中惧怕的心理是山里人千年摘之不去的枷锁。也好,一种神权的禁锢或许能保留一棵千年不变的大树。就像村头那棵古枫,因为赋予神的地位,没有敢去碰它的一枝一叶。于是,古枫每年都会发芽、长叶、枫红满树。
对于古枫,曾是山里孩子的童年梦魇。因为,大人们对神树的敬畏早已在孩子们的心中洒下了胆怯的阴影。比如,大人们时常教育孩子,“那是社神,会拿走人的魂魄。”
常年开荒、砍伐,大山变得越来越光秃。春天的到来,只是让乡间小路的杂草勉强地睁开睡眼迷离的双眼,然而,却又经不起老牛的一大口。
古枫有高大的树干,高至半山,直耸入云。成片的油茶林四季常青,山里人无法断定哪一片是春天的叶子。每年,古枫都会严格按照时令发出春天的第一张叶子。于是,山里人们对季节的判断,往往以古枫的叶子为标准。“看,枫树发芽了,该泡谷种了。”
曾经,我相信大人们的神说,不敢多向古枫看一眼,担心会摄走魂魄。当不小心看向古枫却发现魂魄仍然存在时,我便大胆起来,看向古枫的次数也就多了起来,以至我渐渐喜欢古枫那满树新叶,那是春天和大山的悄悄对话。
一直认为,山里的人们应该会踏着那条弯曲的山路,一代又一代地生存下去,守着四季的更迭,孩子长大,老人老去。何曾想到,大山的变迁,改变了山里人的固有思维。
山高路远,肩挑手拿。有限的生存资源无法满足山里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艰难的生活条件让人们仰天长叹。
山里的人们渴望走出大山,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随着国家易地搬迁政策的实施,山里的人们等到了百年一遇的机会,纷纷响应号召,举家搬出大山。世代走过的山路变得越来越陌生,疯狂生长的杂草不断地蔓延,掩住了曾经的足迹。那些熟悉的山头依然存在,只不过变得越来越荒芜。山间的稻田再也无人耕种,巨株的芒草从稻田的角边往中央生长,两山之间变成了一条再也看不见稻田的大沟。
熟悉的记忆在不断地游走、远逝,山村显得原始、落寞。
搬迁的人们生活在热闹的集市旁,生活在通畅的大道边,住进了舒适的楼房里。山里人勤劳朴素、坚强勇敢的基因还在,他们通过外出务工、科学种养,用双手编制着幸福的生活,再也不会因无米下锅而烦忧,再也不会因山高水长的叹息。
汽车爬行在弯弯曲曲的山间公路上,车窗外飘进缕缕大山的气息,这种熟悉的气息令人回味、安然。春风轻盈、温和,带着泥土的芬芳;阳光穿透一冬的阴云,爽朗地照在大山上;路边的杂草长出了最新叶子,干涸许久的沟渠又有了流水的声音。每一棵树,每一株草都徜徉在春光里。
或许是离开已久,曾经的寻常让我猛然醒悟。原来,最美的风景是曾经走过的路、淌过的水,只是,我们曾一度地忽略。
再也不惧怕那棵被山里人奉为神的古枫,因为我全然知晓,世上根本没有神鬼。当然,我不会去破坏古枫的一枝一叶。因为:我深深地理解,如果古枫没有被奉以神的地位,它应该早已被人类砍伐了。所以,我认为古人对树奉以神的地位,更是一种智慧,也正因为这种智慧,后人才能一睹那些千年生长的古树,见证历史的久远。
每次回到山村,我都会看向古枫,这已成为我对山中季节的断定。如:古枫新叶是春天,古枫茂盛是夏天,古枫叶红是秋天,古枫落叶是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