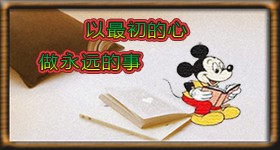【流年·巢】窗外那蓝蓝的天空(征文·散文)
【流年·巢】窗外那蓝蓝的天空(征文·散文)
我斜靠在病床上,窗外几只鸽子在嬉戏,有只胆大的鸽子竟然站在窗台上,点着头注视着我,仿佛咕咕地在说,你怎么不出来呢?
我一起身,它们哗地飞走了,带着哨音,盘旋着飞过高耸的楼房,一直向上飞去。我顺着鸽子飞的方向,看到了蓝色的天空。
碧空如洗,白云悠悠,似有微风吹拂,我却丝毫感觉不到,我被囚禁于此已经三天。不是囚禁,完全是一场意外。如果那天,我不到医院给妹妹送饭,如果放下饭盒转身就离开,如果那个小阳人,晚点或早点出现,也许,我就能避免这场意外。可是,哪有那么多的如果和也许呢?
那天我从病房出来,准备回家去,在住院部门口被保安拦住说,接到上级命令,因突发疫情,所有人不能出入。我无奈地回到病房,坐在板凳上,刷着手机等消息。等到夕阳落入山谷,天空拉上黑幕,等来了医院被封控的消息,封几天还不知道。就这样,我这个无病的人,像病人一样住进了医院,享受着病人的待遇。不对,我不输液,也不吃药,只是住在病房里。
与病人不同的是,我是无备而来的,没有带洗漱用品,没有带换洗衣物,羊毛衫上套着羽绒背心,外穿一件长风衣,一条秋裤,一条外裤,还有一个手机,就这么来了。
晚上八点,病人洗漱准备就寝,我也去擦把脸,漱了口。病人都躺在了床上,我却望着墙角那张又窄又矮的床发愣,七八十公分宽,一条白被横在上边,连铺带盖都有了。我140斤的块头,能躺进去吗?即使能躺进去,估计也无法翻身。家里一米八的大床空着,在这里活受罪,真想回家去。可窗口有护栏,门口有人把守,就是插翅也难逃。气愤,憋屈,无奈,一时占满了我的心房。我猛地拉开房门,走了出去。走廊里有许多人围在一起,叽叽喳喳像是吵架。
一个女人说,我家里还有孩子,不让回家怎么办?一个男人说,我家里还有老人,不让回家怎么办?又听一个年轻人说,我明天还要上班,怎么办,怎么办啊?穿白大褂的值班护士说,大家别急,急也没有用,我知道,我能理解,我的孩子也在家,还在等着我回去喂奶呢。听她如此说,走廊顿时安静下来。我心一颤,走了过去。她三十多岁,头上冒着汗,胸前湿了一片,是奶水浸湿的。
比起他们,我的洗漱换衣,我的睡觉,又算什么呢?大家都默不作声地向病房走去。我也转过身,默默地走进病房,关上房门,脱掉风衣,脱掉羽绒背心,然后躺在床上,打开手机,浏览朋友圈。
“啪”房间里的灯关掉了,屋里漆黑一片,只有手机亮着刺眼的光,朋友圈还没刷完,就关灯了?
妹妹说,姐姐,睡觉吧!
才八点半,就要睡觉啊?也太早了吧?这个时间,有时候在家里才吃晚饭。
“嗯,我们都患眼疾,害怕亮光,要闭眼多休息,才有利于尽快恢复。”
我无奈地关掉手机,静静躺在小床上,闭上眼睛,等待着入眠。也不知过了多久,感觉刚进入梦乡,“啪”的一声,灯又亮了,病人大姐上卫生间。她视力模糊,站立不稳,走路一颠一颠的,陪伴她的老公被隔在外面。我中午来还见过她老公,说回家给她拿日用品,就进不来了。
大姐关灯后,我睡着没多久,“啪”的一声,屋里亮如白昼,我从梦中惊醒。大姐起来喝水,上卫生间。我摇摇头,坐了起来,揉着眼睛发愣。一会儿,实在困得不行了,我又躺下,再次入眠,就这样不停反复。清晨五点半,我睡得正香,灯“啪”的一声,又亮了,护士端着盘子,拿着血压计给病人量血压。我只好起床了。
我头昏脑胀地去洗脸、漱口,然后等着吃饭。七点半,护士们送来了早饭,一盒牛奶,一个鸡蛋,两个肉包子,我吃得饱饱的。饭来张口,像个寄生虫,我内心感到不安。
病人输液时,我在走廊里溜达。溜达一圈又一圈,与对面病房的大姐聊天。大姐与我一样,来给老公送医保卡,就留在了这里。同病相怜,倍感亲切,话自然就多了起来。说到被封,大姐摊开双手激动地说,你看,我穿着羊毛衫来的,什么都没有。
我也什么都没有,现在最需要牙刷和毛巾了。大姐说昨晚许多人到小卖部买了牙刷、毛巾和脸盆,她也买了。
我停下脚步问大姐,昨晚能买东西?我怎么不知道。不等大姐回答,我一溜烟跑到护士站,对护士长说,我要去买牙刷和毛巾。昨晚到今早都没刷牙,嘴里黏黏的,难受极了,感觉都有味儿了,幸亏戴着口罩。
护士长拿出钥匙,打开大门说,要快去快回,不要走远啊。
我答应着出了门,一口气跑到小卖部,却被老板告知,牙刷毛巾昨晚就卖完了,确切地说,是抢完了。啊!什么时候来货?老板说不知道。我顿时泄了气,一边往回走,一边埋怨自己,昨晚摆出一副格格不入的架势,坐在病房里傻等,难道别人会送牙刷来吗?难道清高就能当牙刷用吗?可埋怨有什么用?还不如去想办法。我想起酒店的一次性牙具,用一次就扔掉,多可惜啊,现在有把一次性牙刷也是好的。家里也有一次性牙刷,是给坐火车准备的,可远水也解不了近渴。
妹妹输完液体,往旁边挪挪身子,让我也上床躺着。我按着酸痛的腰,斜靠在她脚头的病床上。透过玻璃窗,我向外望去。窗外是一排病房,病房后面有座高楼也是病房。越过高楼,一直向上,就能看到蓝蓝的天空了。
天空湛蓝,白云悠悠,我亦如躺在蓝天下,躺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风轻轻地吹着,花儿慢慢地开,远处传来了嘚,嘚,嘚的马蹄声,如梦似幻,那一刻我陶醉了。
等我醒来,已到了中午,护士长和护士们把午饭送到门口,接过盒饭,寄生虫三个字又冒了出来,不能这样等着吃饭,不能做寄生虫,既来之,则安之,该做点什么了。
吃完午饭,我坐在床上,打开江山文学网站读文章,写评论。不知不觉三个小时过去了,晚饭之后,在走廊走够两千步,再打开印象笔记写文章。
到了晚上,病人入睡时,我也躺在床上,让身体充分放松。清晨醒来,她们还在梦中时,我悄悄地把方凳搬到房门口,借着走廊的灯光写文章,读文章,写评论。
吃完午饭,我斜靠在妹妹的病床上,去仰望蓝天,遥想着驰骋在广袤的大草原上,抑或奔跑在鲜花盛开的原野。有的时候,望着望着就睡着了,就像小蜜蜂一样,飞出窗口,飞到广阔的田野上,肆无忌惮地奔跑。那一刻,我忘记了所有,只感到无比的幸福。白日做梦,也是香甜的。
三天过去了,已买到了牙刷,解决了刷牙的问题,头皮发痒却让我难以忍受,几天没有洗头,头发结成了一绺一绺的,怎么梳都贴在头皮上,没有了形状。发型凌乱,臃肿着眼泡,再加上一脸的倦容,让形象大打折扣,这副尊容,都让我难以示人。
我想起了多年前年去延安时,住在豪华的大酒店里,水龙头流出却是涓涓的细流,连毛巾都润不湿,就那么撩起水抹一把脸,顶着凌乱的发丝,也在延安城逛了两天。
吃罢晚饭,我用梳子沾上水,把头发梳了一遍,就挺起胸走出了病房,到走廊里去遛弯。对门大姐也出来遛弯,我们两个走着聊着,我夸大姐每天坚持锻炼。大姐叹口气说,不锻炼怎么办?你看我老公,几年前就劝他,管住嘴,迈开腿,可他听不进去,整天我行我素,胡吃海喝,吃完倒头就睡,不到六十岁就患上了糖尿病。医生让他注意饮食,多加锻炼,可他还是不听,依然我行我素,现在还不到七十岁,视力模糊,心脑血管疾病接踵而来,不得已,才到医院做手术,这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我也才知道,眼科多数病人都是糖尿病患者。妹妹同病房大姐,今年六十五岁,年轻时做生意,生活毫无规律,饮食毫无节制,还抽烟喝酒,二十年前就患上了糖尿病,现已发展到了后期,要注射胰岛素降血糖,还导致了脑梗、视力模糊等并发症。即使这样,住院期间,她还躲在卫生间里偷偷地抽烟。
可见,自律多么重要,能避免许多疾病,运动增强体质,增加抵抗力。头发脏就脏吧,形象不好就不好吧,忍受一下就过去了,锻炼却要坚持,还要坚持书写与阅读,让精神世界丰盈,让心态平和,保持乐观的情绪,这才是最重要的。
第七天,当我斜靠在妹妹的病床上,又去仰望蓝天时,忽然飞来几只鸽子,它们在窗外一闪而过,带着哨音,径直向天空飞去,在空中翱翔一圈,然后飞向了远方。
恰在此时,护士长进来说,大家收拾一下,两点以后就可以回家了。幸福来得太突然,我愣了一下,然后从床上跳下来,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儿,赶紧收拾东西去了。
七天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我却经历了许多的第一,从最初的无耐与郁闷,到最终的忍耐与接受,这个过程应该是人生的一次历练吧!无论怎样,我终究还是走了过来。
下午三点,我终于走出病房,走进了日思夜想的蓝天下。

因为疫情突然被封闭医院,作者并没有表现出过度的紧张与焦虑:读文章、写评论、记录生活,散步锻炼……诚如作者所说,坚持书写与阅读,让精神世界充盈。有时候忍耐的确是一种煎熬和痛苦,但是经历过才会觉得更美好。
文章里提到医院八点半就安排熄灯就寝了,那种感觉我真的感同身受:在医院、在火车上。世界上速度最快的是时间,最慢的也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