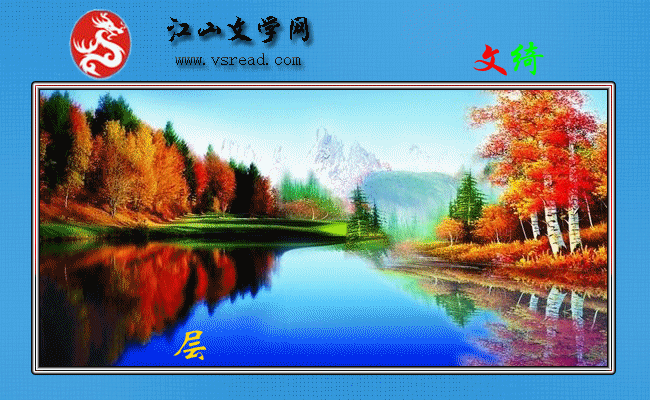【风恋】过年,大山的深深记忆(散文)
【风恋】过年,大山的深深记忆(散文)
一段古老而缠绵的记忆,像一首老歌,唱出渐行渐远的旋律;亦如一壶老酒,喝出经年的味道。
过年,一定是大山最值得期待的日子。
山高林密,独特的喀斯特地形地貌形成的座座高山,割据着山中那漫长而悠远的日子。山路弯弯曲曲、忽上忽下,似乎永远没有尽头;山泉汩汩流淌,流经那些艰难而沧桑的岁月。只是,不管生活如何如何艰苦,过年一定是个兴奋时刻,这个兴奋的时刻始于宰年猪的那天。
桂西山区传承着宰猪过年的古老习俗。我想,这个习俗有着大山的生存智慧。原因是,桂西群山座座,每一次出行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勇气,贫瘠的土地没有多余的一份钱购买集市上的猪肉;还有,没有必要,谁也不愿意花上一天时间翻山越岭去赶集。于是,年前宰上一两头年猪,再腌制成腊肉,改善来年生活便成了大山的生存技艺。
父亲说,“不杀年猪不像过年。”于是,我家每年都会保持宰年猪的习俗,而这个习俗也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并一直伴随着我走南闯北。
小时候,总是不明白我家的年猪为什么那么小、那么瘦,梦想同别人家一样,能宰上一头甚至两三头大肥猪,然后,让父母的脸上会挂满着灿烂的笑容。还好,山里并不是每户人家都能宰上一两头肥猪,有的人家甚至连猪都宰不起,这让我的心理尚存一丝平衡的安放。
宰年猪总是一个值得和期待的日子。父亲非常节俭,但,宰年猪那天一定煮上吃不完的大块精瘦肉。天还没亮,父亲便早早起床了。屋外的临时灶炉里传来旺火燃烧的呼呼声,爷爷、二叔、堂叔也起床了。爷爷是宰猪好手,他有一把磨得寒光闪闪的尖刀;二叔和堂叔都是老兵,抓猪不在话下。每年宰年猪,都是爷爷、父亲、二叔、堂叔共同完成的,似乎这是他们一年之中固有的一项默契。爷爷操刀、二叔堂叔抓猪,父亲烧水。尽管我家的猪不大,但堂叔总不免夸上几句,“比去年的肥多了。”堂叔的话总是让人感到欣慰。大山的人们四季劳作,需要大量的体力,吃几块大肥肉更能补充能量。
二叔力大无穷,他一手抓住猪耳朵,一手抓住猪后腿,用力一甩,再大的猪,二叔也能扛在肩上。猪会发出嗷嗷的尖叫声,这种声音对于大山来说,不是哀嚎,而是一种幸福。对于没有猪嗷嗷尖叫声的人家来说,年是缺憾的。
大山的冬天十分寒冷,旺火上的大铁锅里,热水翻滚,再用木梯架在铁锅上。二叔把宰好的年猪扛到木梯上,几把刮刀迅速褪去猪毛。几个来回下来,汗流侠背,早已忘了冬天的寒冷。
年猪的每一点肉都十分珍贵,那是山里人经过一年的饲养,翻遍每一座山打猪草养大的。
年猪宴烹饪成三道大菜,大锅肉、猪肝炒粉肠、猪血菜,每道菜的分量十足。
大山贫穷的一个现象是不敢生病,小病扛着,大病就看命了,能活就好运,不能活就认命了。
二叔身强力壮,生性乐观,谁也无法想象,军人出身的他会生病。二叔患的是骨癌,诊断书说只能活半年。但二叔觉得身体一直很好,不应该患有这种晴天霹雳的病。再说,换骨髓至少有几十万,几十万对贫困的山村来说,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于是,二叔否定了诊断书。只是,二叔的身体越来越差,高大挺拔的身躯越来越弯了。尽管他总是刻意地挺直身子,用一名老兵的步伐抗拒着病痛。没有药,不敢进医院。为了抗拒病痛,二叔把脚伸进滚烫的开水里。他的脚从红肿到腐烂,他脸色蜡黄。无法行走,二叔便骑马干活,直至他再也无法跨上马背。二叔的病痛是无法想象的,他的大腿一直流着脓血,不断地腐烂,从一侧可以看通另一侧。二叔已经意识模糊,不识人。但当我回家时,他想了好久,还是能叫出我的名字。
当我在青岛出差时,电话那头传来一片哭泣声。二叔去世了。没能见到二叔的最后一面是我今生的遗憾。我用随身携带的餐巾纸做成一朵白色的贴在胸口。高速行驶的大巴车上,耳边吹着悲痛的风。二叔才50多岁,正值壮年,这不是他该离开的年龄。再也听不到二叔洪亮的歌声,再也听不到二叔爽朗的笑声……二叔自诊断为骨癌,他用5年时间与病痛抗争,最终还是没能逃脱病魔魔爪。
三个月后的一天,爷爷把我和弟弟们叫到跟前,给每人发了一块银元和四十元现金。爷爷说他担心哪天他去世了,我们找不着。三天后,爷爷在坐凳子时坐空昏迷。当我从县城赶到老家时,爷爷躺在床上,并不断地说他的脖子很僵硬。我想,上天会保佑爷爷的,因为爷爷是那样的慈祥。
不幸的时,我还没回到县城,就接到弟弟电话,“公过了。”
一年中,两位亲人离世。
斯人已逝,活着的人必须振作,大山不允许一蹶不振。
又到宰年猪的时间了,怎么办?以前爷爷操刀、二叔堂叔抓猪、父亲烧水。虽然弟弟们有力气,但没抓过猪,害怕呀!堂叔虽然会抓猪,但他一个人也抓不住呀!兔子逼急了还会咬人,何况猪有一张大嘴巴。还有,谁来操关键的一刀。
父亲已经把大锅里的水烧得翻滚,爷爷留下来的那把尖刀也早已被父亲磨得锃亮。
我是家中的老大,这个时候,我必须站出来。我一把抓住猪耳朵,二弟、三弟、堂弟飞扑向猪,四人把年猪压得严严实实。堂叔找来那条用了很多年的绳子,把猪的那张大嘴捆住,顿时,猪大嘴的嗷嗷声变成了从猪鼻发出的嘤嘤声。
猪终于被我们制服了。谁来操关键一刀?说实话,我敢抓猪,但我还是不敢把刀刺向猪的槽口。父亲也说杀猪太残忍,他不敢,堂叔说他敢杀猪,但技术不好,杀不死。“我来。”堂弟是二叔的儿子,他也像二叔一样,胆子大。堂弟接过寒光闪闪的尖刀,像爷爷一样,敲了一下猪的前脚,然后一刀刺向猪的槽口。一股殷红的猪血汩汩涌出,当年猪停止挣扎,全身变软时,我们舒了一口大气。终于,第一次合作成功,大家脸上都绽放着无比欣慰的笑容。以后不再担心找不着人宰猪了。
贫瘠的土地始终无法改变大山的面貌,穷则思变,山里的人们必须另寻途径。山里人秉承大山的厚重,不断地走进工厂,走向工地,再也不把全部精力投向那巴掌大的土地和脚掌大的石缝,他们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不怕吃亏,他们用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创造着奇迹,不用种地也有粮食,不用养猪也有肉吃。
大家都觉得养猪是亏本生意,用养猪的时间去打工更划算。人们情愿买一头年猪,也不愿养一头年猪。二弟、三弟也认为养猪不划算,母亲也说养猪太辛苦。
大山的男孩和女孩有着分工的约定,男孩放牛,女孩打猪草。如果生了一个儿子,山里人会说生了个“看牛的”;如果生了个女儿,山里人会说生了个“打猪菜”的。母亲一直想生给我们生个妹妹,但生来生去,最后还是生了三个儿子。
我非常感受打猪草的辛苦。每天放学,我必须背着背篓翻到山的那一边,近处的猪草早已被摘得一干二净,打猪草的人们会越走越远。我家没有女儿,我必须像女姟子一样,认识山中各种各样的猪草,有水麻叶、构叶、何首乌叶……凡是山中猪能食的猪草,我都像女孩一样,一眼识别。每天打猪草回到家,往往星星都出来了。除了食猪草,猪还要吃糠麸、粮食,这是山里人的一种痛,人都不够吃还要给猪吃。尽管打猪草很辛苦,但父母依然每年都会养上两头猪,父亲说,养猪最好养两头,抢食,猪长得快。由于读书,父亲每年都会变卖一头猪为我积攒学费。母一直有个愿望,有一天我家能宰上两头猪,腌制八只腊猪腿。
因为家境实在窘况,二弟、三弟相继辍学了,他们不得不跟随着村里的人们外出打工。这是父亲的痛,也是我的痛。父亲的痛是没能让二弟、三弟完成学业,而我的痛在于为什么我没有一个有钱的父亲。多年后,我才恍然醒悟,是我错怪了父亲,因为,很多家庭早早就让儿女辍学回家务农了。贫困的是大山,而不是生存在大山里的人们。
大山里的人们一直在期待着改变,期待着告别肩挑手拿、跋山涉水的日子。只是,莽莽的大山犹如层层铁网,牢牢地囚禁着山里那些年年相似的日子,那怕是外出务工挣了钱,最终还是要回到铁笼当中。
随着国家扶贫易地搬迁政策的实施,山里人等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纷纷响应国家号召,搬离那些巴掌大的土地和脚掌大的石缝,告别了那囚禁多年的铁笼。山下有便利的交通、热闹的集市和温暖的房屋。
只是,山下没有养猪的猪圈。
父亲依然住在山里,父亲说,他喜欢清静,还可以养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