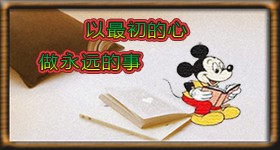【流年】大地的耳朵(散文)
【流年】大地的耳朵(散文)
猪在后院圈里嗷嗷直叫。我知道该拔猪草了,提起房檐台上的襻笼出了门。
一场骤雨刚刚歇住,阳光刺破云缝,将村庄照耀得一片鲜亮。街巷里,泥泞的路面上还摊着一洼洼积水,但街道两边已被人踏出了两道“路”。说是路,其实只是荷叶大的一个个脚窝,时断时续,刚刚放得下一只脚板;人走上去,就像池塘里蹦跳在荷叶上的青蛙。我提着襻笼,就是沿着家门口那条“路”,蹦跳着出了村庄,走到庄外的土壕岸上。
壕岸上的麦茬地里,玉米苗已抽出三四片淡青色的叶子。在一行行玉米苗间,割麦子时掉落的麦颗早发芽了,麦青绿茸茸,似乎比玉米苗长得还旺盛,在麦青、玉米苗间,长着一簇簇刺芥和打碗花。麦青、刺芥、打碗花,都是猪最爱吃的草。父亲平时用糠来喂猪,舀四五碗糠、少半碗麦麸,再倒入面汤、泔水,搅匀后就是一顿猪食。糠用麦草、玉米秸秆粉碎而成;打糠机就在村庄磨面机房外,一推闸刀,呜呜呜不到半小时就能打四五袋糠。麦草、玉米秸秆村子里遍地都是,可打糠得用电,用电当然要收钱。因此,拔猪草就成了我放学回家后的固定功课。猪草拔回家,用清水淘洗干净,再用菜刀切碎,盛在喂猪的铁盆里,倒些面汤、泔水,端进猪圈,老远就能听见猪头埋在铁盆中,酣畅淋漓的咀嚼吞咽声。
现在,天刚放晴,玉米地里湿漉漉满是露水,显然不是进地拔猪草的时候。我沿着壕岸上玉米地边那条莎草覆盖的土路,往地上头走。我发现,壕边上长着刺芥和打碗花。我蹲下身,刚拔了一把打碗花,再睁眼向前一望,兴奋得差点叫出了声——壕边的干塄上,在艾草、蒿草间,密密压压满是地软!地软一堆又一堆,软软的,黑沉沉的,在头顶太阳光的照晒下,似乎散发着墨绿色的光,一团团在微微翕动。那天下午,我捡了半襻笼地软。进了村庄,我还没走到家门口,整个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了壕岸上有地软,一窝蜂向壕岸上拥去。
那天夜晚,母亲将地软淘洗干净,切丝后,加上油、盐、辣子、调料,烙成地软饼。刚出锅的地软饼香喷喷,咬一口,满嘴油香。那一晚,我一口气吃了五片地软饼,肚子胀鼓鼓的,就连嘴里呵出的气都是香的。
除了庄外壕岸上,村庄南原的土坡上也有地软。因此,雨过天晴后,在南原坡坎上,时常可以看见提着襻笼拾地软的孩子身影。其实,村庄里地软最多的地方,是村里的苜蓿地。苜蓿,是喂牛喂马必不可少的青料。村庄里的苜蓿地,从春天到初冬一直绿葱葱,至少有七八亩。刚发芽的嫩苜蓿,是人们觊觎的一道下锅菜,因此苜蓿地常年有人看守着。
村子里看苜蓿的,是我叫“八爷”的老人。八爷黑瘦黑瘦,头发几乎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木匠的凿刀刻出来一样亮清。八爷爱说笑。嘿嘿一笑时,脸上的一道道皱纹里好像都盛满了笑意。八爷爱讲鬼故事。盛夏的夜晚,在麦场上乘凉,八爷一讲起唐王游地狱之类的鬼故事,身边总围满孩子大人。有一晚,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后来人散后,八爷将我搂在怀里,一声不吱睡在麦场上。母亲在村庄里找寻了大半夜,快要急哭了,八爷才嘿嘿笑着说:“娃在我这睡着呢。”但是,一看起苜蓿来,八爷像是变了个人,黑着脸,提着条鞭杆,站在苜蓿地边,威风凛凛像尊门神。八爷从不许村里的女人们进苜蓿地拾地软。用八爷的话说,“婆娘们身上长着八只手,贼着呢。”但八爷允许村里的娃娃们去苜蓿地拾地软。我们踩着雨后苜蓿地的露水,在刚刚割过的苜蓿茬间找寻着地软。地头上,传来八爷哼唱秦腔声;半晌工夫,我们会拾大半襻笼地软。
地软如果吃不完,母亲会将地软拣干净,晒在院子里;晒干后,母亲会将它们收拾起来。如果家里来客或者过节做臊子面,地软便成为必不可少的佐菜。故乡的岐山臊子面,讲究煎、稀、汪、酸、辣、香,还讲究红、黄、黑佐菜颜色亮丽,红是胡萝卜,黄是黄花菜、鸡蛋饼,黑是黑木耳。只是,母亲平时舍不得买木耳,只有过年待客吃臊子面时才用木耳,平时用地软。她将干地软用开水泡开,切丝和胡萝卜丁炒熟后,下到汤锅里,地软黑沉沉漂在汤碗上,咬一口,脆香脆香。
地软是从哪来的?小时候,每逢拾地软,为着地软的来历,我们总会叽叽喳喳争论不休。后来,我知道了,地软属于一种天然生成的藻类植物,春、夏、秋多雨时节,它们便在雨水中快速生长;雨后天晴,被阳光一照晒,便迅速变干,不见了踪影。
只是,知道这些时,我已离开了故乡,再也没有在壕岸边、坡坎上、苜蓿地里拾过一回地软。
我曾多次梦见在故乡拾地软的情景。一场新雨之后,大地湿漉漉,清新而洁净,草叶上滚动着一颗颗珍珠似的露珠。在草丛中,静静卧着一团团黑黑的地软,软软的,嫩嫩的,像大地长出的一只只柔嫩的耳朵,正静静地谛听着我从远方走近的脚步声。
同时欣赏这样的语言,灵动素朴,有质感。
我阅读时,儿童时光的记忆不时泛起。

包括喂猪,我们小时候印象里的喂猪,就是剩菜剩饭、泔水,好一点再拌入一些麦皮麦糠搅匀。当然这些只是我们一些散养的农户随意些,那些专门的养殖大户,还是饲养的会更精细一些,有专门的猪饲料;构树的果子,我们这里叫做“红疙瘩”,那是小时候我们极有限的几样美味之一。大概在春夏之交,那些小果子便逐渐变红变膨胀,就像一个个小红灯笼,颜色鲜艳明亮,让人垂涎欲滴。不过,那个东西经常凌空长在高处,采摘不方便有一定的危险,而且食用的多了会感觉舌头都是麻的……至于坐着索索的“地软”,我特地查了百度才知道:地软又叫地木耳、地皮菜,可以炒食还可以凉拌,我猜味道应该很不错。
这篇文章清新自然,很有画面感很有烟火气息,欣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