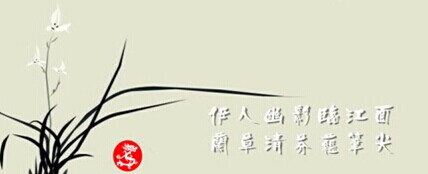【晓荷·旧时光】母亲的纳底针(散文)
【晓荷·旧时光】母亲的纳底针(散文)
![]() 一
一
今年回了一趟老家,在翻找一些老物件时,一枚沾满灰尘的纳底针赫然映入眼帘。它静静地躺在一个小木盒里,仰望着我,仿佛帮我寻回了许多儿时的记忆碎片。木盒里还有几卷针线和一些杂七杂八的小东西,如顶针、小剪刀等,都是日常手工活需要用到的物件。纳鞋底的工具叫鞋锥子,但在我们那里的地方方言就叫纳底针。
孩童时期,母亲经常给我们纳鞋底。母亲纳的鞋底既漂亮又实用,穿在小脚上暖洋洋的。农村都比较穷,买不起厚实的棉鞋,只能自己做。记得家里的钱都是压在一个老衣柜上边的小木箱子底下,有一分几角,最大面额不会超过十元面值。为了省着点用,母亲都舍不得花。只有我一次又一次地踮起脚尖在柜子门边去顶起那小木箱的一角,偷看着底下的钱数是否发生变化;或者偷拿一角几分去买几颗糖果,享受一番被细竹条抽打的深刻记忆。买布料还是需要用到箱子底下压着的钱,但母亲都会精打细算,不会冤枉多花一分钱。买来布料后,母亲就用熬制的米浆糊鞋底做鞋面鞋垫,把基本形状做好晾干,再用一个模具拟好尺寸拿大剪刀裁剪,一堆布鞋的零配件就成了。母亲做的布鞋要比买的棉鞋暖和多了,全是实打实的好布料。
每到冬天的时候,我们最期盼的就是能有一身新衣服,有一双崭新耐磨的小布鞋。我们那里冬天都比较冷,最冷的时候零下三四摄氏度。这个时候,村里人都很少出门,呆在家里烤火,取暖;一天也就出个一两趟,维持生活的最基本刚需;没事就拉拉家常,听听柴火堆里燃烧时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撸着脚下的土狗,看着袅袅炊烟。每次出门回来,大人们的脚都会被冻得通红。那种被冰浸的感觉,就像刚落进冰湖里一样,全身找不着一块暖和的地方。
母亲怕我们小脚被冻着,每年都会给我们纳鞋底,做布鞋。而做布鞋就需要用到纳底针,需要它穿插在厚厚的千层底上,纳出各种各样的纹路。母亲的手工很好,尤其做鞋垫的时候,能纳出许多种花样:有梅花,有四叶草,有星光,只要母亲叫得出名的她都会纳。
二
如果说有一种工具传承了几千年经久不衰,那么纳底针必然是其中一种。纳底针延续了历朝历代,直至科技时代的今天依然为我们使用和认可。在农村集市,你仍然能看到许多用纳底针手工制作出来售卖的老布鞋。一双双地摆在街边地摊上,旁边坐着一个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
我国最早的纳底针制作布鞋始于周代,这是从侯马出土的东周武士跪像而获得的结论。古时候,纳底针制作粗糙,针尖全靠人工打磨,不像如今的纳底针那样花样百出,有不同的各种形状。随着时代的变迁,手工技术越来越成熟,这项技术也在民间坊市慢慢传扬开来。有了纳底针后,古时候的人们就有了一双可以抵御风寒的布鞋穿,再也不用被冬天所折磨。
纳底针延续着历史的文明,一代传一代,传到了现在。母亲手里的纳底针是太奶奶时传下来的,太奶奶传给了奶奶,奶奶又传给了母亲。到最后,纳底针永远地躺在了小木盒子里,没有再继续传下去。
纳底针是用通孔木柄和圆铁针组合而成,尾部有一个圆形像算盘珠一样的顶手柄。为了固定木头不松散,通木上会加上几个箍圈,箍圈上有许多图案,很是漂亮。纳鞋底的时候,要注意细节,左手需带个顶针,不然锋利的钩针会伤到手指。
母亲的纳底针因为岁月的洗礼,箍圈已磨得光亮光亮,许多纹路都被磨平了。母亲纳鞋底的手艺不是跟奶奶学的,奶奶改嫁得早。母亲嫁过来的时候,奶奶已经改嫁到了其它地方,成了另一家人的母亲。母亲的手艺是跟外婆学的。外婆在我记事时起,就已经很老了,那腰被汗水弯成了九十度,拄着一根拐杖,蹒跚而行,很不利索。
三
母亲说,外婆纳鞋底和纳鞋垫的针法好,会纳出很多种图案,而且纳出的千层底和鞋垫好穿耐磨。母亲年轻的时候就跟着外婆一起学纳鞋底纳鞋垫,一针一线地学。外婆说,要想纳出的图案饱满,就要多绕几圈线,根据图案的层次感决定绕线的圈数。外婆还说,有层次感的鞋垫还能起到按摩的效果,穿起来更舒适。鞋底纳起来就简单多了,不用太花哨的图案,只要将千层底均匀固定就好。不过纳鞋底需要费很大力气,常常看到母亲手肘部高高抬起,就知道母亲很不容易。
母亲说,刚开始用纳底针学习纳技的时候,没少被针头扎破手指,痛得她哇哇大哭。那时候,在厨房忙活的外婆听到母亲的哭声,就跑出来。仔细一看,原来是母亲坐在堂屋门口学着纳鞋底,不小心被纳底针扎到了手指。当时,母亲纳的鞋底已经掉落在了地上,针头还插穿在鞋底上,带着一丝血迹,警示着使用它的主人。手指被扎到,母亲捏着自己的小手指,不停地哭。细小的血丝正在不停地从她伤口处冒出,染红了母亲的双手。她泪眼婆娑,可怜兮兮地望着刚赶过来的外婆,越哭越起劲。那时母亲才十来岁,还是个孩子。
外婆连忙安慰母亲,将她的手指放在自己的嘴巴里不停吸允。在那个时候,没有医疗条件,这种吸允伤口的方法是最好的消毒方式。外婆一问,原来是母亲没有带顶针,才扎到手指的。于是外婆对母亲说,用纳底针的时候一定要带枚顶针,不然很容易扎到手指。外婆还捡起地上的鞋底,一针一针地示范给母亲看,让她了解顶针该戴在什么地方,怎么纳鞋底,纳底针怎么使用,都耐心地给母亲讲解。
在外婆的悉心教导下,母亲也学会了怎么使用纳底针,并且跟着外婆学习了很多种花样。随着母亲出嫁后,母亲的手工艺活就越来越炉火纯青,会纳出许多种精美的图案。
四
一次母亲的纳底针丢失了,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她问父亲,父亲也没说拿。母亲翻了又找,找了又翻,就是没找着。
“奇了怪了,我明明放在小木盒子里,怎么会不见了呢?”
当母亲走出堂屋,一眼看见我正用着他的纳底针在院子里玩“金木水火土”游戏。金木水火土游戏是农村小孩子都会玩的一种简单游戏,就是在泥地上画两个连着的大框框,然后俩人用削铅笔的小刀对着自己的地盘凌空往下插四下,口中念出对应的金木水火四声,最后一声土是扎在对方的地盘上,如果小刀不倒,就可以将对方的地盘一部分划归自己所有,直到对方地盘下不去刀子定输赢。母亲看我玩得正起劲,气不打一处来,跑过来提起我的屁股就一顿打。边打还边训斥我说,纳底针玩坏了,以后还怎么给你们三姐弟纳鞋底?
纳底针可不是用来玩“金木水火土”游戏的,它是用来给我们三姐弟纳鞋底用的。没有纳底针,就没有我们的新鞋子穿。被母亲打了几屁股的我,委屈得哇哇大哭。父亲听到哭声,又跑出来安慰我,并跟我说,下次可不能拿母亲的纳底针玩了,不然过年的时候就没有新鞋子穿了。听了父亲的话,我就再也不敢拿母亲的纳底针玩了。
但有一次母亲的纳底针,真丢了。问我是不是又拿她的纳底针去玩了,我说没有。这次纳底针的丢失,真不是我拿的。自从被母亲打过一顿后,我就再也没碰过她的纳底针。
没有了纳底针,父亲又给母亲买了一个。不过母亲说,新纳底针没有老纳底针好用,嫌针尖的锋利度不够,手柄处还握着不顺手。父亲说,将就着用吧!等有钱了再买个好一点的。母亲也听父亲的,用这个新的纳底针给我们一年又一年地做着布鞋。
就这样,新的纳底针母亲又用了许多年。而这几年里,母亲也没提,父亲也没再买过纳底针。我们姐弟三的新布鞋还是一样,每年母亲都会给我们每人做一双。
穿着母亲纳的新鞋子,别提有多高兴。那种幸福的感觉,就像吃了密一样,美极了。不像隔壁领居家的孩子,由于母亲走得早,那双布鞋早已破洞连连,冷得他直打哆嗦。母亲可怜他,也会拿我们穿过的旧布鞋送给他,让他能抵御那寒冷的冬天。
五
然而在后来搬家的时候,母亲的老纳底针又回来了。原来老纳底针掉到了柜子的夹缝里,难怪母亲怎么找都没有找到。
搬家去县城住的时候,母亲没有带纳底针走,而是将它放回了那个小木盒子,锁到了柜子里。母亲年迈了,而我们常年都不在家里,母亲也就没有再纳过鞋底。那枚纳底针就这样静静地躺在老家的柜子里,那个小木盒子中,再也没出来过。
两个姐姐也学会了纳鞋底、纳鞋垫的手工活,只是她们谁也没有带走母亲的那枚纳底针。加上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也用不到再纳鞋底了。
有次我回家,母亲对我说,现在的棉布鞋总是没有老布鞋好穿暖和。在我准备回老家收拾东西的时候,母亲跟我说,记得带回她的那枚老纳底针,她想再纳一次鞋底,想给我做一双布鞋,回家的时候能换着穿。看着老母亲满脸慈爱的面庞,我忍不住眼底泛出泪花。
我知道母亲不是想纳什么鞋底,而是她想给儿子深深的母爱,做一双布鞋。因为我每次匆忙回家,总是找不到鞋子,所以母亲想做一双布鞋。而且冬天还很冷,穿的拖鞋没有布鞋那么暖和,就更加加深了母亲要做一双布鞋的愿望。
母亲的爱,就像那枚纳底针一样,永远陪伴着我。无论时光有多久远,母亲就是用她的心意以及那枚纳底针纳出了一幕幕温暖。
母亲,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