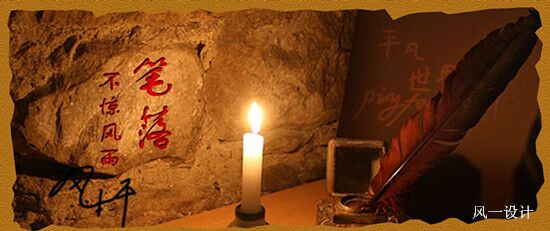【江山·根与魂】【东篱】英雄,从未走远(散文)
【江山·根与魂】【东篱】英雄,从未走远(散文)
一
去年中秋,回老家探亲,我抽出两天时间,去了佳木斯。想它,念它,三十年前,我曾在那里生活工作过四年。
我谢绝了朋友的陪伴,一个人在城里兜着。曾经是这座城的主人,如今是远道而来的游客,心绪复杂。去佳西,想看看我居住过的糖厂小区有什么变化。结果是变化太大,小区已经由一片平房,翻建成为一座座楼房。别后音讯杳杳,还到哪里去相认1994年那方红墙绿瓦,还有我可敬可爱的房东大哥大嫂。
只好拍了几张照片,便折身而归。走在平坦宽阔的马路上,几多感慨。我出生的村庄,生活过乡镇,一直隶属于佳木斯市(合江地区),1991年划归双鸭山市管辖。但地理的划分无法切割我对它的感情,土地相邻,道路相通,风俗习惯相同,我一直还把它当作故乡,从未动摇。身为游子,希望它不改容颜,等自己有朝一日,衣锦还乡。只是,归期遥遥。但这样,何其自私?它也要适应时代的变化,跟上时间的脚步啊!就拿我脚下这条友谊路来说,曾经破烂不堪似根烂绳,现在早已变成双向四车道的通衢。路两旁的行道树,垂柳、云杉、榆树、紫叶李、丁香密密匝匝,尤其两旁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间或出现一段段浓荫如毯的绿廊。这条友谊路,从市区红旗路到远郊敖其村的笔直大道,全长约20公里,当年,路两边分布着佳市主要的工业企业,厂房林立,机声轰鸣。
但如今,路上车流喧嚣,路旁多变成居民小区,变得相对安静。走了大概不到一刻钟,直觉就到了原来的佳木斯纺织厂(简称佳纺)附近,这个距离我太熟悉,和我以前住的小区其实只隔着一条铁轨。以往,将货运列车开进厂里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厂。铁道口的栏杆,起起落落几十年,拦住了人们的脚步,却没有拦住岁月。那些行人走远了,那些岁月也不知去向。佳纺是东北第二大纺织厂,员工一万多人。在佳西,佳纺就是中心,一个小社会,医院、学校、商店应有尽有。我们平时理发、洗澡都愿意去佳纺,那里选择多,价格实惠。
过了铁路不远,不经意间,往路的对面看过去,惊见刘英俊烈士陵园的大门牌匾。忽然,我的心扑通了一下。刘英俊,这是我从小学课本里就熟知的名字,英雄,并没走远,他还在这里。也许,很多人都淡忘了这个名字,但这座城市记着他,我还记着他。我激动地从马路直接穿过去,顾不得违章,也顾不得车来车往。只觉得,刘英俊跑了过来,在搀扶着我,我心里踏实。如今,我老了,他依然年轻。
二
时间正好,才下午两点钟,不需买票,我径直走进了刘英俊烈士陵园。看介绍,我三岁的时候,这座陵园就已经建成了。第一次来这里时,我二十六岁。当时,我调进佳市工作不久,正高兴着呢。我是打着饱嗝,饭后散步,并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只把英雄当成了普通人,当成了自己的邻家兄弟。
走进陵园,迎面是2002年新建的刘英俊勇拦惊马的铜像。忆那时,那是一个怎样惊心动魄的早晨啊!?1966年3月15日,刘英俊所在连队到佳市市郊执行训练任务,拉重炮的炮车走到佳纺这里,有公交车摁喇叭,辕马受到惊吓,径直奔向前面不远的6名儿童,千均一发之际,刘英俊奋力将缰绳猛向后拉,同时,用双脚绊住马的后腿。6名儿童获救,刘英俊却被炮车压在下面,光荣牺牲。为此,当年7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人民的好儿子》,高度评价刘英俊同志的英勇行为,他的先进事迹,在全国引起轰动。
向前走到底,是新修葺的烈士之墓,墓后是一块仿棺形背景墙,红色底座,黑色幕屏上,“人民的好儿子”五个鎏金大字金光熠熠。这份荣誉,质朴无比,像乡亲们夸奖自己的孩子;这个称号,沉甸甸的,因为它是以人民名誉颁发的。烈士墓左侧,是1966年4月立下的一块石碑,此处是英雄牺牲之地,曾经,这里天倾地摇,此刻,惟余一丝风声。右侧则有一座“刘英俊同志永垂不朽”纪念碑,是佳市轧钢厂1987年树立的。碑顶是刘英俊铸铁塑像,造型和刚进来时遇到那座铜像一样,是个微缩版。非铜是铁,正好象征,一个年轻的军人,有着钢铁般的意志。
我在墓碑前徘徊了一会儿,脑海里,涛起云涌。那时,人们以在国营厂上班为荣,每天以厂为家,甘于为国做贡献。就看这块轧钢厂制作的墓碑,就知道大家有劲往一处使,这方耸立的墓碑,仿佛一股团结的力量从大地深处喷涌而出。那时,正是佳木斯各大企业效益不错的时候,人们的心劲心气十足。我不知道后来这些工厂的现状,包括这个陵园对面的佳纺。几年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它们漂向了何方?还有那些老员工,他们“分流”到了哪里?我就是在这个时候举家南下的。为刚才在外面的时候,没有找到佳纺的大门有点遗憾。我凝视着刘英俊塑像良久,他的表情里似在流露几分凝重。那时,连名气响当当的佳造纸、佳纺、佳发电、佳电机、佳糖、佳联合收割机、佳中药、佳肉联,这八驾马车都觉行进艰难,同样需要有人站出来,救工厂于低谷,岂止是“黄了”两个字了事,时代呼唤英雄辈出。
至今记得,当时有一期《三江晚报》,头版发表了一个记者的调查长文《拯救佳木斯》,在全市乃至全省都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以为,家“丑”不可外扬,文章说得太尖锐了,捅了政府职能、企业管理中的一些痛点、淤点。我一直将这位记者当成英雄,英雄不问出处,是他的挺身而出,敢说真话,唤醒了一座沉睡的城。
三
最后,我来到西侧的刘英俊烈士纪念馆,改扩建后,又增加了一块牌匾,上刻“佳木斯革命烈士纪念馆”。原来,政府及民政部门,已将两座纪念馆进行了整合,将这里打造成了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和青少年思想教育基地。
据说,在清明节、以及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五四青年节参观的人比较多。有些企事业单位搞团建,也会来到这里。的确,当时人很少,这样适合我,可以静静地看。刘英俊的事迹,我几乎可以倒背如流。但我还是浏览了一遍。我想,一个英雄的诞生不是偶然的,他平时就处处以雷锋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比如,做校外辅导员、用津贴给学校买书,当“业余修理员”,出差途中,好事做一路。平时就是个无名英雄。
我的目光,久久的在一张照片上停留。那是他救下的六个孩子的一张合影,我想,那应该是被救下后记者为他们拍的。他们表情平静,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没人会责怪这些孩子,他们还不懂死亡的含义。如果英雄还活着,他也一定希望看到孩子们的天真,天真得像白云,无忧无虑。为纪念刘英俊,六个孩子中的四个孩子改名字为刘继英、赵继、赵英、赵俊。他们非但每年在英雄牺牲这天去墓前祭拜,还为英雄的父母养老送终。他们都很平凡,只知道尽“儿子”的责任,只懂得这么朴素的报答。
接着,我看了其他几个展区。这还是2018年新布展的展区。展出佳市建党初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命英烈的事迹。其中两个名字引起我特别注意。
孙西林,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转为中共党员,后随第一批干部由延安奔赴东北,被任命为中共合江省(合江地区前身)委委员,佳木斯市副市长。1946年1月31日,正在市长办公室开会的孙西林,被冲进来的特务杀害。为纪念他的光辉业绩,佳木斯人民将其葬于西林公园(公园因他改名)西园内,并命名一条主要街道为“西林大街”,惯称西林路。是一条繁花的商业街,几个小时前,为辨别去老单位的路线,我还在西林路和解放路的路口停留了几分钟呢。
另一位是邵云环,新华社驻贝尔格莱德女记者,1999年5月8日晚,在北约野蛮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不幸遇难。由于她在佳木斯纺织厂小学读过小学,为纪念她,佳纺小学更名为云环小学。此刻,云环小学里书声朗朗,和纪念馆只隔着一条荣歌巷。恍惚觉得,童年的她,正坐在教室里读书呢。
看了他们的事迹,我做起假设。假设那天早晨,孙副市长把警卫员留在身边,没让他去护送省工委李书记去北满分局开会;假设1999年3月,邵云环安于现状,在《参考消息》工作下去,不再主动请缨到南斯拉夫去做常驻记者。他们都可能还活着,活得好好的,活得心安理得。但没有,因此,他们有幸成了英雄。只是,这两个字,是用鲜血写成。他们的事迹,或许不够惊天动地,他们都是“小”英雄,容易被红尘埋没。家乡人直率,怕忘记,不只是树碑立传,还干脆就把他们的名字刻在路牌上,刻在公园门口,刻在母校门口。
还是一位记者说得好:“只要我们记着,他们就还活着。”是的,记住他们,无需千言万语,我也是他们一块移动的墓碑。
四
时针指向三点,我从纪念馆中出来。这时,我一眼看见,对面数十米外,是刘英俊烈士的另一尊雕像。他左手高举毛泽东选集,高举一颗炽热的红心,身背钢枪,右手紧握着枪筒,枪筒里是待发的铮铮誓言——扎根边疆,保卫边疆。
再靠近些,我停下瞭望,仿佛看见英雄脸上闪过一丝微笑。他看见,有几个老人,在纪念馆前甬道旁,围拢在一起下象棋,他们有时会争执起来,有时还发出阵阵笑声。尽管入园须知上有许多条“严禁”,但并不具体,我看见,在烈士馆四周有些场地,很适合跳广场舞,那些大妈们一定不会放弃这些地方。他们把这里当成了公园。老百姓开开心心,想必是烈士们乐见的吧。有的市民累了,索性就坐在雕像底座的台阶上。英雄无语,市民们从没觉得他离去,把他当成外人,他或许更喜欢这样,和老百姓离得近,每天在一起。
出了陵园,我又站在友谊路上,因为刘英俊陵园和云环小学,市民们亲切地称之为“英雄路”。忽然好生感动和自豪,我曾是英雄路上的居民。
叫了出租,打算返回宾馆休息。路上,我的眼前,烈士们的面庞和林立的高楼交替闪过。我的城市,变得熟悉而陌生。由于它是东北老工业基地之一,国企多,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中,遇到了不少经营困难,比如刚刚路过的佳纺。但这座城市,遗传了英雄们不放弃、不逃避,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基因,它不会就此一蹶不振的。过了友谊路立交桥,车右转弯,右侧就是一片蓊蓊郁郁的园林,这就是佳木斯西浦植物园。植物园的南端,余晖晚照中,气氛有几分肃穆。果然,是佳木斯烈士陵园,刚才看过的孙西林、邵云环等58位烈士就安息在这里。
车子驶上的这条路,地图上标注为圃东街,符合人们的称呼习惯。但叫我睁大眼睛的是,一块路牌写着浦东路,蓝底白字,清清楚楚。不管是本意,是笔误还是巧合,这路牌立马温暖了我。我现在的家就在上海浦东,而佳木斯,是我的故乡,冥冥之中,都拉着我的衣襟,都是我的不舍。或许,佳市在有意向浦东学习,浦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试验区,经济发展走在中国前列。这样想着,很美好。
再向前走一点路,路左侧,就是市政府大楼。市政府,将市中心地块腾出,给投资商使用,造了一座购物中心。因此,市政府于2005年搬迁至此,离烈士陵园很近。莫非父母官们想时刻警醒自己,不忘先烈的遗志,用榜样的精神激励自己。利用党中央振兴东北的大好机遇,自我加压,借势发力,勇毅前行。我仔细阅读了佳木斯市《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它没叫苦,只是默默实干。面对东北冬季漫长,企业投资成本高,2023年省市重点项目仍开复工200项,完成投资228.8亿元,投资完成率129.5%。实干加巧干,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实现480.1亿元,同比增长3.6%,列全省第4位。一直引以为傲的全市农业,粮食总产量达到228.6亿斤,实现“二十连丰”,真正成为全国粮食压舱石中至关重要的一块。等等,成绩喜人,可圈可点。再展望2024年的工作目标,没列举一条客观不利条件为自己谋取资本,处处是扩大、培育、推进、提升、壮大、激活、坚持等积极昂扬向上的字眼,令人鼓舞,令人振奋。崭新的友谊路,通往城市几个主要经济技术开发区去,里面包括众多外地、外资企业,它名副其实,真正地成了一条共享繁荣传递友谊的纽带。
一座崇尚英雄的城市,永远充满希望。和平的年代,每个奋斗者都是英雄。现在,我虽然远在他乡,做不了什么,但我愿把我的祝福留下。祝愿英雄城佳木斯,越来越好。假以时日,不久的将来,一个文明、富强、繁荣、美丽的佳木斯必将在黑土地上重新崛起。
忘了交代,佳木斯,满语,原名为甲母克寺噶珊、嘉木寺屯,意译为站官屯或驿丞村。它地处三江平原腹地,现已发展成为黑龙江省东部地区中心城市。写罢,难掩激动,我的耳边响起一首歌:“美丽的松花江,波连波,向前方,川流不息流淌,夜夜进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