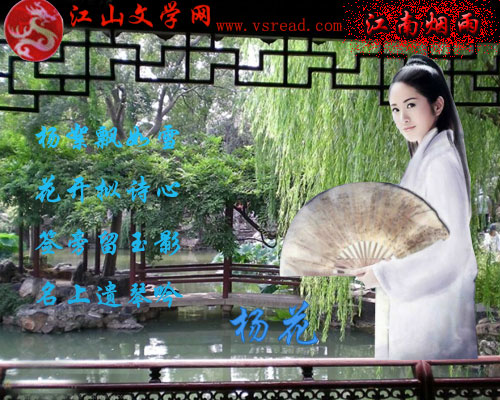【江南】半截黄土墙(散文) ——我眼里的家乡
【江南】半截黄土墙(散文) ——我眼里的家乡
沿着西禹高速向东走,右转进入苏坊街道,一直往南经过一座桥的时候,向左便看见东边的一个村子--崇德村,那便是我的故乡,我出生在这里,并一直长到二十岁,生活在这里,究竟吃过多少碗饭,喝过多少杯水,我说不清,只知道一生下来就在这片黄土地上和泥巴,对这里发生的起起落落,哭哭笑笑,我听过一些,见过一些,也写了一些。
以后上学在外,工作也在外了,对村里发生的事情就慢慢不知了,但对乡村的历史更多的是来源于我的大伯,大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现在却呆在城里,他总是断断续续给我讲着地讲着村子里各个家族的许多往事,让我对这个村庄的人们更加的好奇,更加的想知道他们的过去,知道这块黄土地上每天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将是怎样的悲欢离合。
现在,我只觉得逢年过节,回到家里,就像鲁迅回到了鲁镇,村里的人都很可亲,我很感谢他们,大家都在家里忙着杀鸡宰羊,为过年做着准备年货。我一个人到村子里转悠的时候,不时也碰到儿时的伙伴领着他们的儿子,寒暄几句,便无话可说了,我知道我们之间有了很厚的隔阂。
有时回家赶上农忙,村子里连个人影也没有,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家里一点地,机械化程度的发展,他们农忙也不会来。老人们都下地干活去了。凑巧我在家休假,独自一人,转入转出,感到村里很悲凉。地里的庄稼一年比一年收成好,但总是卖不到钱,贫的更贫,富的也不怎么富,家里的支出也日益增大,孩子要上学,老人要瞻养,没钱就没有办法,而村里人缺的就是钱。他们每天没日没夜地为钱而劳作着,养鸡、羊、猪……换几个零用钱,妇女们早上卖点羊奶都要掺二斤水,每天早上在村子西头都能听到为此而吵闹的声音,男人们有能力的都出去打工了,留下来的还继续在那块地里刨着。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已是村里人习惯了的生活模式,羊叫狗吠,打骂哭笑。始终笼罩着这个村庄,伴着这群善良的人们。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描写他们,如何去述说他们,我只知道,中国像他们这样的人太多了,他们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的父辈和他们一样,没日没夜的在这这块地上刨着,为自己刨着生活,为儿女们刨着希望。夕阳西下,人们一个一个扛着锄头,提着草笼,走在那条充满粪味的小路上。边走边议论着,今年的收成怎样?地里庄稼长得怎样?东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西家的孩子又犯了什么事,这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即便那些事情与自己并没有关系。回到家里,洗一脸盆的黑水,拿个冷馍,拔根葱,三五成群的坐在一起吃着谝着,这是他们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候,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生老病死,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着。
那时候,通常老辈的男人衣裳鞋帽都是女人亲手缝制。女人心灵手巧,姑娘时候就学着做针线活,会绣鞋垫,鞋垫上绣上各种花卉小鸟或者象征吉祥幸福的图案,会做布鞋(布鞋治脚病,软和舒适),会织毛衣,毛衣针在灵巧的手上会变幻出上各种好看的图案,更会织土布,纯棉的那种,然后缝制成床单、被罩等,在如今被各种化纤布料缠绕的情境下,那种手工织的土布穿在身上夏天吸汗,冬天保暖,贴心贴肺。躺在土布床单上,那略微粗燥的土布床单好像妈妈温暖的手,给疲乏的身心是轻轻的抚摸和安慰。男人迈不开脚走四方,很大程度上是女人的温柔和贤惠牵住了他们。
女人心底温柔善良,知足安乐,对男人没有过高的要求,哪怕男人拿回家的是一粒麦,女人也从不嫌弃男人没出息。男人天生有一种优越感,恋家情结,不管年轻时关中男人脚步迈的多远,干了多大的事业,老了都是要归根的,他们老了肉体是要回归关中这片黄土的,那样他们的灵魂才可安息。儿孙们也觉得把自己的老人带回家乡安顿是孝的体现,不管多么贫穷,老人去世时就是东挪西借也要把老人的丧事办得体面,这在当地是对老人最后的交代和告慰,也是当地不成文的习俗。
现在,在这里仍然可以看到一个老头牵着一头老牛在默默地耕耘,后面跟着老太婆在慢慢地吆喝着,历史的脚步在这片土地上延续着它的足迹,不管外边的机械化如何便捷,大部分关中男人的思维仍然停留在老婆娃娃的“热炕头”和“两头牛”上。
村子东头墙根下几个晒太阳的老大爷,吧嗒吧嗒的抽着旱烟,这是老人们最休闲的时刻,他们或许也知道这样的日子不多了。忙起来的时候,他们也拿起锄头,提上笼,南塬北塬的去给羊割草,老人年总归是老人,黄土埋了半截了,能干点啥干点啥,也没人要求他们,但他们总是闲不住。身旁的收音机总是播放着秦腔,他们寡言少语,沉重的生活重担折磨得他们面容憔悴,如一尊尊被岁月的风雨侵蚀的雕像,但只要有了秦腔声在天地间响起,他们的喜怒哀乐,便仿佛随着曲调的高吭或低回,便顿时会引发他们的悲喜感情,如长江黄河般滚滚奔流,一泻千里。驼背五爷曾对我说:“娃呀,你不明白,听了一曲秦腔,流了一回眼泪,我这心就舒坦了,再苦的日子也不觉得累啦。”我听到了自己的血液在周身上下的血管里奔流的声音。一种荡气回肠的浩然雄风,瞬间掠过我故乡那些层岩叠嶂的山峦。
很小的时候,常常围着他们听他们讲过的故事,讲着村子里的变化,村子里的沧桑,他们和我们一样大的时候有着不一样的童年,不一样的担当,听着总觉得好奇,这样的老人,现在回家一次,就少一个,他们是村子古老的见证,他们是村子里的一块碑。碑文是他们那一脸的皱纹和弓形的腰。他们现在也乐呵呵的享受着今天的生活,很满足的样子。其中,有一个老汉,因父辈的矛盾,骂过我,也骂过我大。我生活在这里,我了解这里的人们,我憎恨这块土地,只觉得这里的人们太苦了,但话又说回来,对他们这样一群没有上学的老汉,我能说些什么?我很恭敬的递上烟,他摆摆手,指着自己的烟锅说,没我这抽起美。我笑了,这里的人到什么时候都讲究实在。
村子西头的那口枯井,已经好久没有用了。绞水的辘轳不知被谁偷走了,就剩下一个光光的轴心还在那里。井台上长满了荒草,把井台覆盖的严严实实,井口用一块破木板盖着,揭开一看,井里还有水。井台上的青石板也早已没有昔日的光泽了,就连完整的样子也看不出来。自来水为人们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时间,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快乐与轻松,看来生活的累并不全部在于解放肢体上,而是向我们步步紧逼的生存压力。现在的井沿上再也听不到妇女们洗衣时的欢笑,那辘轳的鸣叫了和那挑水人那吱咛吱咛的扁担声。古井,像一个老人,独自守后在村口。
村里三条路都很烂,坑坑洼洼,特别是巷道,下雨天,水集成河,春耕的化肥运不进来,村里的苹果运不出去。村委会一帮人,整天嘴里喊着修,但一直没修,村里的人们也没有办法,满怀怨气的叫老子骂娘,喊几声。老祖宗把咱们留在这里,谁还能说什么,这条路送走了一代又一代,也迎来了一代又一代,路依然是路。更可气的是,村子中央有几家盖了新房,把自己的地基垫的很高,整个巷道积水不外流。村里的人都是自顾自,别人也不好说什么,只要不淹没自家的房子,也没人去管,看起来让人感觉很不舒服,也很气愤。我,又能说什么呢?何况村里的事情很复杂,有些事情根本无法说清楚,有些人根本就不讲理,谁又能怎样。也难怪。我大总对我说:“好好上学,争取离开这里,你要是在这里呆一辈子,你就没什么出息”。看来他们也很无奈,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他们很了解这里,在这里,没道理的事情很多,不讲道理的人也很多,自个吃饱穿暖,一般不去打抱不平的,他们只有三五成群的议论着,发表着自己的看法,说些闲言碎语无关痛痒的话,一笑了之。
我大是当兵出身,从过几年政,因为一些原因,也成了农民,在村里,也算是一个懂政策,有文化的人,能写能算,也能写一手毛笔字,所以,是不是会有人叫他去帮忙些一些东西,我大到也热心,谁叫都去,每次回来都说说,谁家的孩子离婚了,谁家的儿子不养老……听了,很气愤也很无奈,我发两句牢骚,我大总是说:“能怪谁呢?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清官难断家务事,劝劝就行了”。
上了大学后,回家的次数也少了。偶尔回去一次,村里的变化也只是看看村貌的变化,谁家有盖新房了,谁家又买了摩托车,谁家的儿子又娶了媳妇,其余的枝枝叶叶,我全然不知,总觉得对村子在发生着变化,常想回家转转。
但每次回到家时,除了到村子里到处转转,也没地方好去,倒是喜欢坐在我家后墙外的那棵桑树下,桑树长得很大,很像一把伞,下面是乘凉的好去处。我大在桑树下放了几块石头,每每农闲,人们都聚在桑树下面说闲话,又吃饭的,纳鞋底的……,我一出后门,就坐在那块石头上,听着他们说这,说那。从他们嘴里了解这村里的变化,大娘大婶们都很亲切,喜欢听我讲城里的事情,我也偶尔说一些,但不常说,因为他们总觉得我说的太离奇,也难怪,他们整天生活在这里,对外面的世界了解的很少。树下,有一位常客。他是我远方堂哥的孩子,今年十六七岁,智障,腿脚也不灵便,不上学也不下地,常常坐在树下,目睹来来往往的人们,人们也喜欢和他开心,故意逗他,他总是笑着脸,有时也胡骂,人们都哈哈大笑。我总觉得他很可怜,按辈分他的管我叫叔,但是从来也没有叫过,直呼我的名字,有时还骂我,我总是笑笑。
这里的人们,生时落在黄土炕上,死了埋在黄土堆下。恰逢村里的一位长者去世,他是一位老革命,干过国民党,也打过共产党,也当过村干部,很守旧,见不得村里青年男女的嘻嘻哈哈,打牌娱乐,他对他家族的成员管的很严,别人家也管一些,管的让人有点烦,他死了,有人高兴,有人悲痛,悲痛的是他的儿女,高兴得是路人。因为再也不会有人干涉他们的事情,送葬的队伍从我家门前走过,吹吹打打,哭声连天,我看了看,有种说不出的感觉,觉得村里少了一个人,确切的说是一个老人,村子的历史又被埋葬了一些,很可惜。虽然他死得很平常,自然的生自然的死,听说他是个老党员,是个老干部,有什么政绩我不知道,直觉得他是个好人,只是太守旧罢了。
送葬的鞭炮声越来越远,听不到了,我大让我拿锨去埋葬,我没去,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种事,我一点也不愿意去干,我不愿意看见任何一个人被埋葬,即使很自然的生老病死。
在家里的日子很无聊,地里也没什么活可干,我大不让我下地,呆在家里,常常听见隔壁婆媳的吵闹声,骂声一句比一句高,一句比一句难听,娃哭狗叫,惊扰着四邻,起身出门看看,门外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大都在看热闹。这也难怪,隔壁的大女婿误杀了人,跑了,女儿被判刑入狱,留下三个孩子,在这里生活好长时间了,生活中难免有一些磕磕碰碰,矛盾越演愈烈,激化了,也就发生了口舌之争,都是两个老人的孙子,儿媳要闹,他们有什么办法,一次两次,人们还会去劝,次数多了,也没有人管了好像人们都习惯了。看到这场面,我也不知怎么办?该劝谁?谁的错,都不容易,都可怜,相互理解是谈不上,也许闹闹就过去了,也就好了,或许,愈演愈烈,我不好说,我是个局外人,怎么好管那些说不清的事情,最终,他们还是被劝回去了,人们也三三两两的散去。
村子现在已基本上改变了原来的样子,房子高了,也漂亮了,路也宽了。农闲时,时时会看见,树荫下,有打麻将的,有下棋的……,也有三五成群闲谝的,谁家的苹果长的好,谁家的棉花又有什么病虫害了,……说着说着,总会开怀的骂笑。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随着夕阳的西下,一个个三三两两都下地干活去了,这似乎已经成了规律,在这里延续着,村子里又变得空荡荡的,偶尔有哪几位老人,提着凳子,坐在村口通风的地方,说着家常。
村里的人们不断的演绎着生活的悲悲喜喜,相处的也很和睦,东家借点盐,西家借两个馍。谁家的孩子要结婚了,忙去送两鸡蛋,聊表心意。谁家的老人过世了,忙去哭两声,算是安慰。村里的人一生有三件事,盖房,娶媳,养老。村里的新房一座又一座的盖着,盖的很宽敞,很漂亮。日子也过得很红火,老人们也很健康,整天乐呵呵的。唯一让村里人头疼的就是给儿子娶媳妇,他们为了这事,四处托人,到处打听。腿没少跑,人没少托,礼也没少送,事情倒没办成。村里大龄青年十几个,外出打工不安心,三天两头往家跑,打牌、赌博倒是样样在行。我转身走进一家破烂的土坯房,这里住着我儿时的一个伙伴,比我大几岁,家里也很穷,只有祖上留下来的这三间瓦房,一间厨房,他们的院子比村子所有的院子都大,看起来更凄凉。初中辍学,打工几年,没有什么起色,无奈之下家中七拼八凑把他送到普田学院学了个厨师,现在在南京的某个酒店打工,听说干的还可以,我倒是没看出来。为了他的婚事,他母亲总是叹息,父亲是个老实憨厚的农民,家里什么事情都是女人做主,说东就东,说西就西,从来没有任何意见。一家人这样也到过的很好。他母亲一看见我总是恭维我两句,就说起他儿子的婚事,不知是家长为儿心切,还是实在无奈,她竟托我为她儿介绍对象,我听了都不知我的腿长在哪里,随便说几句不相干的话,就走开了。儿子娶不到媳妇,父母脸上都无光,村里人还是很忌讳这个,但事实是这个样子,有什么办法呀!是命?非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