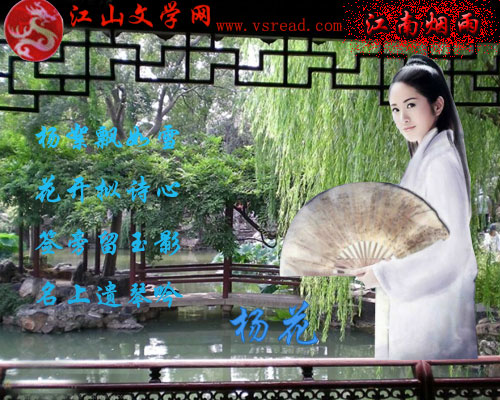【江南】早上皮包水(散文)
【江南】早上皮包水(散文)
清明小长假,老公的弟弟从苏州赶回来过节,按惯例,第二天一大家子要去老街皮包水吃早茶。
早上七点,公公骑自行车先行出发,节假日人多,老人家怕没位子。可一到皮包水,买早茶券的人已排起两条长长的队伍。如今吃早茶的,除了讲本地话的,还多了许多来泰州旅游,讲普通话的外地人。
公公一看这情形,连忙打电话叫孩子们过来,兵分两路,自己排队买券,孩子们楼上找位子,原本想早一点吃的,结果还是等到了八点半。
楼上大厅里人声鼎沸,交谈声、寒暄声此起彼伏,有的端起茶杯正抿一口,有的夹着干丝往嘴里送,有的低头吮吸蟹黄汤包汁,有的呼呼地吃着鱼汤面,个个眉宇舒展,满足与惬意的样子,一幅春意浓浓的早茶图跃入眼帘。中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泰州时曾赞叹,泰州城不大,但各种尘世的幸福很多。我以为,泰州的早茶文化算是尘世的幸福之一。这种民间饮食习俗,留存至今的凤毛麟角。
旧时泰州人称“吃早茶”为“早上皮包水”。一壶上好的龙井,配上一盘烫干丝,一碗鱼汤面,再加上一笼蟹黄包,慢条斯理地喝,慢条斯理地吃,慢条斯理地品,这早茶许要吃到中午才结束。
茶是翠绿碧清的,玻璃杯里芽芽直立,幽香四溢。烫干丝我喜欢五味的。朱自清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详细描述过烫干丝的制作过程:“先将一大块方的白豆腐干飞快地切成薄片,再切为细丝,放在小碗里,用开水一浇,干丝便熟了;逼去了水,抟成圆锥似的,再倒上麻酱油,搁一撮姜丝和干笋丝在尖儿,就成。说时迟,那时快,刚瞧着在切豆腐干,一眨眼已端来了。”先生描绘得极传神,不过他这里说的干丝,要加上肴肉、虾米、青红椒丝、香菜以及花生米这五味,那味道才更好。五味不单单指五种食材,也指味道独特。
一家人入座后,每人前面有一盘干丝,搛一筷子入嘴,慢嚼一下,鲜香的味道,立马把沉睡了一夜的味蕾叫醒,此后越嚼越有味,干丝的浓香与菜蔬的清香并存交融,一唱一和间,便上演了一幕五味调和的好戏,直吃得人连连点头,交口称赞!等那好滋味咽到肚里,才悠悠地啜一口茶,和家人唠两句。
泰州人对于干丝的钟情,一个懂字值千金,你懂我的味觉,我懂你的期盼,两情相悦似的,天上人间只有你我。味蕾掀起的爱意,汹涌澎湃,如此来这般去,那一碟厚厚实实的小山,不经意间见了底。一年四季,这碟打动人心的菜品,让泰州人的生活充满了温情,充满了闲情,冠上了慢生活这三字,便也吸引了无数的外地人。
走在泰州的大街小巷,早茶店其实随处可见,有的在街口,有的在深巷。再忙的泰州人,早上一碗鱼汤面是必不可少的。鱼汤面考究的是鱼汤。天刚麻麻亮,店老板已燃起炉火,支上一大锅,用野生鳝鱼的骨头、小鲫鱼、大猪骨葱姜煸炒,以大火慢慢熬制。袅袅热气中,隔街就能闻到阵阵鱼香味。
客人落座后,店老板迅速将早分好的一坨坨跳面放进另一只大锅里,搅动两下,面条在沸水里上下滚动,不出两分钟,抄起来就放入备好的鱼汤碗中,撒些小胡椒和蒜叶,顷刻间端到客人面前。叉着鲜滑的面条,喝着醇厚的鱼汤,齿颊留香。鱼汤面营养丰富,不仅味道鲜美,食后不上火、不口干,还能够润脾健胃,泰州老食客们对此津津乐道,说是“进嘴厚得得,下肚润胃肠”。
因为小叔子回来,公公今天特别点了一笼蟹黄汤包。蟹黄汤包是江苏传统小吃,以泰州靖江的最为有名。每一只汤包,宛如一朵饱满圆润、含苞欲开的玉菊,给人以美白如雪吹弹欲裂的柔嫩美感。
吃汤包很有讲究,所谓先开窗,后喝汤。意思就是要先用吸管戳一个小孔,把里面的汤汁吸完,再吃馅和皮。传说当年乾隆皇帝微服私访,到靖江品尝汤包,曾留下了一个笑话。汤包一上桌,乾隆皇帝迫不及待地抓起一只咬上,顿时里面的汤汁烫了嘴,还溅到了衣袖上,可是因为汤包味道太过鲜美,又不舍得丢,还想吮溅到袖子上的汤汁,结果手上汤包里的汁水甩得半后背都是,留下了“乾隆吃汤包甩到半背”的佳话。
笑话归笑话,这满满的汁水到底怎么来的,我问了度娘才知晓。蟹黄汤包的馅料中不光有蟹肉蟹黄、猪腿心肉、鸡汁和姜蒜,最重要的有猪皮熬成的胶冻,一经加热,就融为了汤汁,全部浸入了馅料里,不见踪影。这种汤汁据说制作工序繁琐,有三十几道之多,凝聚了汤包师傅的全部心思,不稠不腻,味道鲜美至极。
一大家子都在低头认真做着“先开窗,后吸汤”的动作,唯恐少了一点滋味,那美妙、奇特的品尝过程,有点像从不识庐山真面目,读到了诗酒趁年华。孩子们忍不住吃吃地笑,那笑在“皮包水”的催化下越发灿烂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