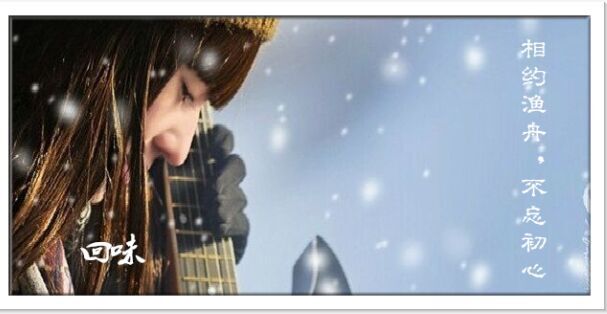【渔舟•风雅】人生有味是清欢(散文)
【渔舟•风雅】人生有味是清欢(散文)
![]()
一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八岁左右,每天晚饭后去菜地里浇水,总是要走过村子里那条巷子。
巷子一边是财主家的深宅大院后墙,一边是少有人居住的破烂旧屋,狭窄,阴森。大姐夫家的门,就开在巷子中间地主家大宅院的后墙上。
那是解放后政府分给他家的。
大姐夫家是典型的雇农,一家人在解放前是帮工度日的,穷得叮当响。本来他父亲是村里有名的石匠,用上好的青石块,帮人打猪槽、火盆以及石磨之类的,也有一定的收入,但那个年代不准做手工艺,就依然贫穷。贫穷真好,至少不用被批斗。
越穷越光荣,在“文革”时期,贫雇农被贴上了比较光荣的标签,说他们根正苗红。要是地主富农就糟糕透顶了,我父亲被人家批斗怕了,就把大姐许给了他家,就可以少受人欺负。和大姐结婚后,大概在1969年春天,大姐夫也当兵去了,我们家沾了军属的光,批斗父亲的次数果然就少了很多。
人民军队是一所大学校。大姐夫原来不识一字,当兵回来后就识字了,他带回来很多小说书,我最记得的就是那本线装竖排从后面往前翻的《水浒传》,而且全部是繁体字。还有一大摞他的战友们送给他的精美笔记本,笔记本的扉页上都有题字签名。笔记本他基本不用,我读书后大部分送给了我,我后来就用作了日记本。
那时当兵回来是分配工作的,大姐夫就被分工到县上的农机厂去当工人,每月有了十多块钱的工资,这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收入。于是,每到周日回家,他就买点菜回来,家里都有他的战友或者同事来喝酒。喝酒时,最好玩的事就是听他们讲当兵时候的故事,而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们讲的水浒三国之类的故事。
每天晚饭后,母亲总让我去菜地里浇水,走过那条小巷,我就到大姐夫家,听他们天南海北的瞎吹。他们每次都要倒点酒给我,那时候粮食酒很珍贵,一般人家是喝不起的,大多是那种廉价的甘蔗渣酒糖末酒和山上那种野生的麻梨果酿成的酒。我酒量很小,一两左右就脸红红的烫得厉害,但为了听他们的故事,还得在晕乎乎中好奇的听着,直到母亲找来,责骂大的小的,大的不正经,小的不听话。
那时候还没有电,晚上家家都用煤油灯。一天晚上,听他们讲到武松把他大嫂杀了,把头砍下来祭奠在他哥的牌位前,说哥我为你报仇了,突然一阵阴风,从牌位后面闪出一个披头散发,满身血污的人来说,兄弟我好苦呀……一下子把我吓得面如土色,就不敢走黑路回家去。
还有一次,也是讲武松的故事。姐夫他们一喝酒就相互嘲笑,说人家武松吃了十八碗还去景阳冈打死了一只吊睛白额的大老虎,真得很厉害,你喝一小点就醉了,还算是男人吗。另一个人说,武松算什么,人家李逵回家去背他母亲来梁山享福,半路上母亲口渴,李逵就去找水,他母亲就被一只母老虎咬死,带去给它的三只虎崽子吃,被李逵一口气四只都打死了。我插嘴说,李逵也太不仁义了,好像天下只有他有母亲知道尽孝,那只母老虎还不是为了它的孩子不被饿死才吃了他的母亲。你小屁孩知道什么,他们说我道,我说“生来不会拈针线,正是山中母大虫”的顾大嫂也不是母大虫吗,这大虫就是老虎,为什么“到处人钦敬,孙新小尉迟”的老公孙新不怕她,武松或者李逵为什么不把她打死,还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呢?一阵哄笑中,他们就答不出来。
母亲天天骂我“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师娘(巫师)跳假神”,后来我才知道这话是近墨者黑,近朱者赤的意思。我天天跟大姐夫他们在一起,慢慢的他们就把我当成了好朋友,不论去那家喝酒,或者是去山上打猎,到河里捉鱼,都让我跟着去。
慢慢的我也学会了喝酒,慢慢的我知道了要读更多的书。
走出山村去读书之前,我因经常被父母责骂,就不再喝酒,但我依然参加大姐夫他们战友和同事的集会,很少落下,感觉那是很快乐的事情。
多年以后,大姐夫们渐渐老去了,他们那个红火一时做打谷机以及锄头镰刀之类的农机厂也改制,民营化后被年轻的老板改成了酿酒厂。但那些英雄虎胆的故事,那些酒桌上尽情的开怀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
二
二叔是个教师,一直在村子里的家庙中教孩子们读书。
本来他也是我的老师,但我爹说,我家生活困难,他领着工资呢,就经常照顾我家,称我爹叫大哥,就让我叫他二叔。
读小学的小朋友很喜欢他,因为他是教语文的,不像算术那样枯燥无味。一周时间中,他总是会给孩子们讲故事,比如送鸡毛信的海娃,放牛的王二小,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等等。在那个时候,我们在晒场里看的露天电影大部分是《沙家浜》《红灯记》之类的革命样板戏,长长的唱腔,看得人心烦。
二叔讲故事时候绘声绘色,一大场孩子围在他身边,村民说,他领孩子就像老母鸡带小鸡,家长们都放心把孩子交给他。有时候也会教我们唱歌,当时,村子里的大喇叭天天播放的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而他教我们的是“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歌声低沉深情,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幼小的心。
就在我到小镇读初中的那一年,他也倒霉了。村子里那个麻子队长和上面来的工作队,说他是臭老九是反革命分子,天天教孩子们些不三不四的东西。他就被开除公职,白天要到田地里参加劳动,接受改造和群众监督,晚上隔三差五就要被揪到他教书的家庙里批斗。
由于他的事情,他在信用社工作的妻子也受到牵连,被单位开除后,前来和他住在家庙旁边的破旧厢房里,等晚上他被批斗且被民兵们拳打脚踢鼻青脸肿之后,他妻子总是搀扶他回家,含泪为他上药。
周末我从小镇回家,总是去看他。他高高的个子,眼眶深陷,那件缝满补丁却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套在他瘦得像一棵甘蔗的身子上,当年的文静儒雅荡然无存。我晚上经常去看他,那时他眼睛就泛起亮光,叫着我的小名,很真挚而严肃地对我说,小宝,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要像海娃一样勇敢,我频频点头
那时候读书不正常,三天两头停课去参加批斗大会或者游行之类的。初中未读完,我几次考取大队上不让去县上读书,说要贫下中农推荐,无奈之下,就去代我爹放牛放羊。我爹早年出去赶马帮,麻子队长说那么多年才回来,肯定参加过国民党估计是特务,就经常和二叔以及村子里的地主富农轮换着批斗,由此也波及到我读书的事情。
那段时间内,我从大姐夫和二叔那里借些书来,带到山上去看。不懂的,就在晚上去问二叔,他即便被人批斗踢打得鼻青脸肿,还是很耐心地给我讲解。
1976年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不久,听说恢复高考了,我总算得到了读书的机会,二叔兴高采烈的来到我家,对我父母说哥嫂呀,总算有机会来了,你们赶紧让孩子去考试。我爹说,他二叔,这家里一分钱也没有,孩子考试要到县城,这可咋办呀,二叔说,诺,这是他们搜家时候没有搜走的一块表,你们想办法卖了给孩子作路费和以后的学费,一定要去考呀。
当时的录取分数线很低,很简单的,我就考起了。告别了父母亲人,告别了满眼期望的二叔,也告别了伴我三年多的牛羊,我走出大山,成为我们那个小山村第一个出去读书的人。
二叔没有等到平反,更没有等到我放假从学校赶回家。多年的批斗和身心的折磨,二叔因心脏病死在一个无人的夜。
这是两年后的事情了,我还在学校上学。那时候,他妻子已经被在县城的单位叫回去上班,说要值夜班那晚就没有回家,何况还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在身边。我接到家里写来的信,早已是一个月以后了。
二步死后多年,就平反恢复名誉了,我知道后,专门找到县城他家里,婶婶对我说,落办的人说了,你二叔不是反革命,他是好老师。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盈满眼眶的泪水从脸颊上流下。
二叔对我祈盼的眼神,如父亲一样的关爱,一直印刻在我的心底。
三
一个偏远的粮店,在一条小河边。
八十年代初,我毕业参加工作,领导说你本来就是山里来的,就去山里守粮店。放心,哪里工作很清闲,根据情况,隔一段时间,运粮马帮把需要供应困难农户的粮食运来,把当地收起来的油菜籽运出来。
两排旧瓦房仓库旁边,是一间简陋的小瓦房。就这是我的住宿煮饭生活学习的地方。粮店前面有一条不太宽的小河,弯弯曲曲,水草丰茂。河边,有前任留下的两块菜地,常年可以种植蔬菜瓜果。
离粮店最近的村子也有几公里路程,平时就我一个人。到季节时候,收一下附近群众种在山地里的油菜籽。这里是偏远山区,田少地多,粮食自给困难,多年来,国家就减免了老百姓的公余粮,反倒是在每年冬季,供应他们救济粮。
小粮店成为我的世外桃源。
每天早上起来,沿马帮小路我去跑步,跑到两三公里外的山头上,对着莽莽群山,大声喊,大声背诵唐诗宋词,听对面山间传回来的回声。之后再走回粮店,就开始工作,打扫仓库周围卫生,除草扫枯叶什么的,检查仓库是否安全,比如有没有老鼠打洞,有没有房屋漏雨等等。
一天的工作早早就做完了,就到小河边的菜地里打理蔬菜,浇水施肥。那时候没有电,煮饭全部烧柴火,小锅小甑子,上午煮一次,下午饭就热着吃,菜就从菜地里新鲜摘来,肉类马帮来时会帮我带点来。下午时间差不多的时候,我去小河边钓鱼,有前任留下用竹竿做成的简易钓竿,在河边挖点蚯蚓,个把小时就能钓到很多小鲫鱼。
晚上是我的快乐时光,那盏有玻璃灯罩的煤油灯,被我擦得锃亮,就着那张简易的三抽桌,听着屋外的虫鸣蛙叫,我读书写字,乐在其中。到冬天寒冷时候,就在床前烧一堆火塘,小瓦房本来就黑漆漆的也不怕熏黑。
穷居山野无人问,富在远方有亲人。那时候二十多岁的年纪,一点也不知道害怕,何况从小就在山里长大,就知道还是要读书,以后才能调出去。在粮店不到两年的时间,我每天把一天的见闻经历写成日记,然后读毕业时候班主任老师送我的《红楼梦》,然后再写读后感。
长夜漫漫,实在没有事情做的时候,我就把书中人物罗列出来串成一线,看看贾史王薛小姐丫环三百七十多人谁和谁是什么关系,就想贾宝玉为什么命这样好,有这么多的女孩子喜欢他,想金陵十二钗和副册的那些女孩子。再没有事情做的时候,我就读那本跟随我多年的新华字典,查繁体字和简化字的区别之类的,直到鼓捣到困了,在地处孤独却毫不孤独中安然入眠。
一年到头,春夏季一般没有什么事情做,只要保证粮食不出问题就好了。我比前任厉害的事情很多,比如在春夏两季,尽量少运粮食来,因为供应量少,存多了时间长了会发黄和生虫。到了秋冬,事情稍多一些,秋季就收前面说的油菜籽了,冬季就该供应粮食。
有时候也会思念,没有思念故乡的小河,而是思念故乡的亲人,想逐渐年迈的父亲母亲还好吗,姐姐们有没有回家去看看他们。有时候也思念学校时候的老师和同学,自从那日分别后,想他们是不是想我,于是我就写信,等马帮来的时候,几十封一摞捆上托他们帮我到小镇邮电所寄出,他们来的时候,也带一摞回信给我,隔空和老师同学倾心交谈。
在夏夜,凉风习习,我会出去看星星,看累了就在场院里吹口琴。那只上海牌口琴,是一位亲戚在我读书时候放假回家,给我两块钱后买的,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虫鸣蛙叫的合奏声好听还是我的琴声好听。后来有一次出去县上开会,忍痛花了半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把吉他。于是,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自弹自唱自宽心,我弹唱汪明荃的《家乡》,满心满足于“青青绿草铺满山下路边开野花”的意境,我弹唱《万水千山总是情》,我“不怨天不愿命但求山水共作证”。
时光荏苒,那些成长的岁月,不论是风雅还是粗俗,都已淹没在记忆里,现今的我们,正享受着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
老弟辛苦了!
相识是缘,相知是情,关于文章,需要向老弟学习的还很多。
惺惺相惜,你的小说独具一格,也是我喜欢的,虽然很多时候没有留评。
同为文字,我们相识在江山,是为了共同的爱好。这一杯友情的酒呀,甘醇绵长……
谢谢回味,辛苦了!
文章草草而就,依旧是友情支持,不参加评选。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