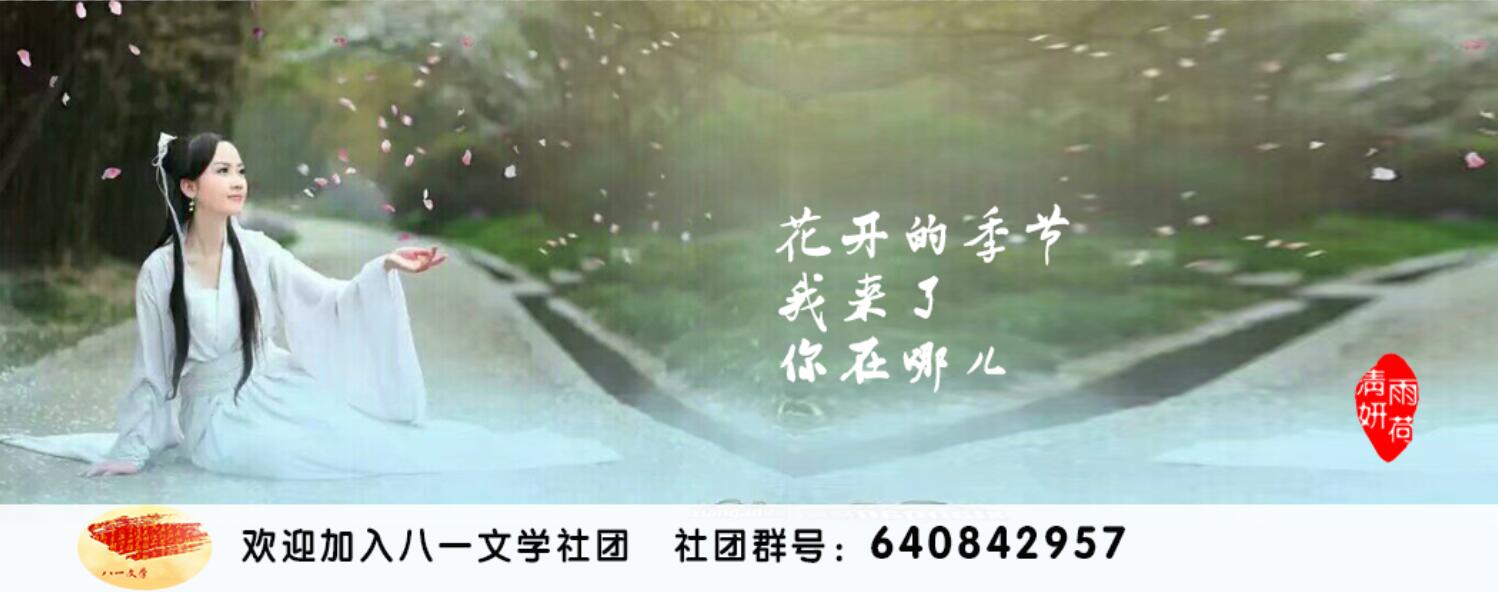【八一】窝头、花卷和馒头(散文)
【八一】窝头、花卷和馒头(散文)
![]()
一
我每次去菜场买菜,走过那些林林总总的馒头店,总能看到那些大大小小的馒头,整整齐齐地码在笼屉上,如同被世人检阅的士兵一般,横成排竖成行,规规正正地立在上面。白的雪亮,黄的如金,黑的似泥,花的迷人,那么美那么媚地擦亮了人们的双眼。每每看到这一切,我就再也走不开了,那些馒头好像伸出无数双温情的小手,拉住了我的心。我呢,也身不由已地要了方的要圆的,要了黑的要黄的,买上满满一大包。这不能不说是发自内心深处难以抑制的不舍情结,如同农民对于庄稼,园丁对于花草树木,工人对于机器零件,思想与行为在没有任何指令的情况下,做到惊人的一致。看着馒头在车篮里洋洋自得地摇头晃脑,我的眼前就升腾起一片往日的云烟……
小时候,我总是看到奶奶矮小的身子端坐在灶台旁的木墩上,一把又一把地送柴入灶,红红的火焰热情地舔着大铁锅,不时地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母亲腰扎围裙,用力地在瓦盆里和粗粮面。等面块成型,母亲就把面盆搬到灶台边上。这时候,蒸汽已经从锅盖下突突地钻出来,丝丝缕缕地升腾起来,水已经迫不及待地沸腾了。奶奶见状就站起身来,匆匆地洗把手,也来到面盆前站定。
母亲接下来打开锅盖,放入笼屉。她们婆媳二人双手各抓起一团面,灵巧地在手中团着,手和面便摩擦出有节奏的嗞嗞声。面团圆好后,她们就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从面团中间嵌入,然后右手不断挑动,左手不断转动,一两圈过后,四周及顶部的厚度相当,中间的空洞合适,就放置于笼屉之上,一个标准的窝头就做好了。待笼屉放满,面似乎还有一半之多,这时她们就改变了做法,不再做那种窝头,而是做锅贴。在我的小脑袋里,锅贴就是窝头的衍生物,做锅贴与做窝头前面的步骤大致相同,只是团好面团,改用掌心相对,来回拍打,“啪啪--啪啪”,只几下,一个面饼便拍好了。拍好的面饼沿笼屉周边,紧贴着锅的周围放置,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锅贴。等锅贴将锅的一圈填满,面也刚好用完。这时,母亲盖上锅盖,用铁砧压好周边,再放置半盆清水。
一切就绪,就是奶奶大显神通的时候了。奶奶一边放入几把柴禾,一边哐咚哐咚地用力拉着风箱竿,红艳艳的火就呼呼地窜出火苗,不一会儿,厨房里就是一片云雾缭绕如同仙界般的景象了。等到这时候,奶奶就悠闲多了,她从腰间抽出那杆永不离身的旱烟杆,在烟锅里仔细放入一搓烟丝,从灶口抽出燃烧的柴点上火,美美地吸上一口,奶奶皱纹纵横的脸就如同一朵盛开的菊花一样悠哉美哉了,或是传说中的老神仙那般安逸慈祥了。
“你去摸摸,看那盆里的水温热了没有?”
我听到奶奶的一声令下,箭一般地冲至锅前,踮起脚尖,把小手放在盆里摸了摸,“热了热了!”我一连声地说着,心里自然希望奶奶揭开锅盖,这样我们就可以开饭了。
奶奶并不着急,轻轻地用火棍拨了拨灶膛,侧头仔细看看火势,再抬头望望蒸汽,然后缓缓地对我说:“再稍等一会儿。”
等到母亲拾完一大筐窝头,用锅铲铲完一圈锅贴,再用盆装好笼屉下面煮好的红薯,奶奶、爸妈还有姐姐哥哥和我,一家七口人,就在灶前围成一圈开饭了。手拿了锅贴的总是先撕掉焦黄的部分,“嘎吱嘎吱”香香地嚼着;拿了窝头的就在窝窝里填满豆瓣酱、咸菜丝,掰开边沿部分,一小块一小块蘸着吃。奶奶总是要我们先吃红薯,打个底,再吃窝头,这样好节省一些。
我想自己对窝头的情感也是在奶奶的嘱咐声中,一点一滴沉淀下来。这样的饭菜我们一吃就是一年,所以对于窝头和锅贴,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顿顿如是,日日如此,年年岁岁总相似,就这样习惯了。“吃饭了!”听到这一声吆喝,就是闭了眼睛,伸手一抓就是那个千篇一律的窝头。放在嘴里细嚼或慢咽,吃出的也只是杂粮面那种粗涩的滋味。对于窝头,我说不出恨,也谈不上爱,只知道是它伴随着我们一家,走过一个个严冬酷暑;陪伴着我们兄妹,一天天健健康康地长大了。
每当奶奶和母亲做饭时,我小猫般蹲在地锅灶旁,一声不响地把这一幕幕场景印在脑海深处。尤其是奶奶和母亲那双手和面团摩擦出嗞嗞的声音,直接钻入我的耳朵,深入我的骨髓,好像千万只小猫咪伸出爪子,不停地抓呀抓,痒痒得我总想穿上隐身衣,悄无声息地抓上一个大大的面团,躲在旮旯角里,也让它尽情地在手中嗞嗞作响,魔术般地变幻。我知道母亲和奶奶是不会同意的,也曾经把这种想法响当当地提出来,可还是不成,她们怕我糟蹋了来之不易的粮食。
二
奶奶说如果糟蹋了粮食,上天是要惩罚的。她还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小麦杆上分出的是无数个叉,长出的是若干个穗,人们有吃不完用不尽的小麦粉。一户殷实人家的小娃娃,娇生惯养形成了刁蛮任性的坏毛病,缠着正做饭的父母,非要一个白面做的马来骑。父母扭不过,就果真做了一个。小娃娃高兴极了,在院子里“驾驾驾”地骑着。这时正碰上玉皇大帝来人间私访,他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想不到人类竟是如此胡作非为!盛怒的玉皇大帝立即颁布一道圣旨,要将所有的麦穗一律收回。多亏众仙们跪地求情,才勉强同意留下了一颗麦穗。”奶奶说这就是如今人们见到的小麦的样子,也就是我们吃不到白面馍馍的原因。
当然,奶奶和母亲是深深体会到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滋味,更清楚我们对白馒头有着多么强烈的渴望,才给我们杜撰了这样一个故事。
那年月,如果说想吃白馒头,就只有等到过大年的时候才有。“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蒸馒头;”这是我们儿时唱的最动听的歌谣。小时候的我们是多么盼望能有白白的馒头吃啊!盼来盼去,终于挨到了腊月二十六。这时,母亲却不再允许我们到厨房去,而是给我们布置这样那样的事做,用架子车去村外沙丘上拉黄沙,年三十撒在院子里迎新用,或是清理院落。总而言之,厨房成了禁区。等我们抽空儿想要钻进去,母亲就堵在门口,递给我们一人一个白馒头,说声去吧!我们就手捧着白白胖胖的馒头欢呼雀跃了。记不得是哪一个春节了,我和哥哥拉回一车沙土就拿一个白馒头吃,吃到最后,我自己都记不清楚吃了多少个。
奶奶和母亲把做好了的白馒头,凉在苇席上,等散尽了热气,一排一排地码在厨柜里,我们狂吃了一整天的白馒头就销声匿迹了。不用说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对于窝头的那份抵触是不言而喻的。一直到除夕夜和大年初一早上的那两顿饭,白馒头才得以重返江湖,露出它可歌可泣的面容来。其余的还是要等到客人来了才用的。
记得有一年春节,母亲做了一个个头最大的馒头用来孝敬奶奶。年初一早饭热在锅里,等吃饭时揭开锅盖一看,好端端的大馒头不见了。其实早被极具好奇心的我狼吞虎咽进了肚子。母亲正要发火,奶奶说算了,大的小的还不是一样吃。站在一旁的我吓得浑身直哆嗦,大过年的若是为此再挨上一顿打骂,太不值得了。在奶奶的劝说下,母亲的脸色一点一点地缓过来,我那颗悬到嗓子眼的心才重又放回肚子里。从那以后,我贪吃的故事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
三
大姐刚入高中时住校,受不了学校做的饭菜。用她的话来说是用铁锹摊成的玉米面,再如粪土般切割开来,做成了硬度不亚于砖头瓦块的玉米馍,饿得她几次哭回了家。其实当时家里吃的也是那种杂面窝头,比大姐说的好不到哪儿去。母亲就用杂粮粉和小麦粉,制成了极为好看的花卷,让大姐带去。带去的自然等不得一个星期,又怕大姐再哭着回家影响学习,就差人去送。有一次农活实在太忙,找不到合适的人手,就让年仅六岁的我接受了这项任务。我提着小篮子,徒步走了七八里路,才把花卷送到姐姐手中。姐姐笑逐颜开地接过去,顺手赏了我一个,就上课去了。
我心里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不说,还得到了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花卷。往回走的时候,我一边啃着花卷,一边哼着小曲,小脸上洋溢着的喜悦光芒,如同天空那轮初夏的太阳。或许是应了乐极生悲的那种说法,走着走着我就掉进了路边的大水渠里。湍急的水流不仅卷走了我手中的花卷、臂弯的小篮子,还灌了我几大口水,差点要了我的小命。我大声惊呼救命,被一个路过的老农拉了上来,这条小命幽幽地在鬼门关外转了一圈又回来了。浑身湿漉漉的我狼狈不堪地走回家,总算是把淌着水的衣服差不多暖干了,我也被暖出一场重感冒来。
能吃上白馒头是在八零年以后,那时候我家的小麦已经不再是用一口缸存放,而是有了一大囤。奶奶总是背靠小麦囤,眯起一双幸福的小眼睛,爱抚地摩挲着手中的白馒头,笑吟吟地对我们说——这样的好日子是她做梦也没有梦到的!
几多苦涩,几许甜蜜。对于窝头、花卷和馒头的情结,就这样一笔一划地镌刻脑海,今生今世,难以忘怀!
感谢老师赐稿,期待更多精彩。问好老师,遥祝春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