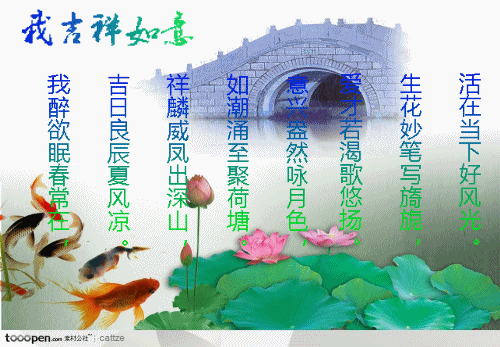【好韵】生命拐杖(散文)
【好韵】生命拐杖(散文)
我的童年是在饥饿中度过的。
上世纪60年代初,国内连续遭受三年自然灾害,豫东大地饥荒蔓延。为了生存,人们吃树叶,啃树皮,挖野菜,嚼草根。有的倒下了,就永远倒下去。死神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
我是一棵苦蕖菜,在贫瘠的土地上生根发芽。长期的营养不良,使我身体弱小,骨瘦如柴。我是家里的独苗苗,父母爱我如命。母亲常常抚摸着我自言自语:“啥时候能长成大人啊!”
那时候生产队吃大伙(集体食堂),每天不到开饭时间,男女老幼就排着长队在食堂前等着领饭。说是领饭,实际上是每人一个馍,一碗青菜汤。按年龄馍分成三级,十八岁以上的吃一级馍,十岁以上不满十八岁的吃二级馍,我不满十岁,当然吃的是三级馍。一级馍大如拳头,三级馍形如鸡卵。然而正是这大小不一的等级馍,成了当时人们赖以延续生命的源泉。每天当母亲把馍领回来塞到我手里时,总是说:“孩子,这是你的。”每次接过馍我三口两口就吃完了,然后眼巴巴地盯着母亲手里的馍。母亲就是母亲,每如此她总是说:“还想吃?给。”说着把自己的馍掰下一小块递给我。我说:“娘,我不吃你的馍。”母亲笑着说:“傻孩子,娘的馍比你的大,吃吧,吃饱了长成大个子。”因为饥饿,我每天几乎都要分享母亲的饭食。以致成为我终生的心灵自责:那时太不懂事,真不该多吃母亲那份馍!
为填饱肚子,饥饿的人群整日像野狼一样到处觅食。一天傍晚,我在村西一个废弃的油坊里发现一堆发霉的油渣饼,白白的,上面爬满了蛆虫。饥饿使我的双手伸向那堆变质发霉的腐烂物……我一边吃,一边满满装了两裤兜。
夜里,在腐烂物和胃酸的作用下,我的肚子开始爆疼。母亲心疼地说:“孩子,那东西不能吃。”我说:“娘,我饿。”
“饿,也不能吃,吃了要生病的。”母亲一边说一边轻轻为我揉着肚子。
母亲的轻柔,使我的疼痛得到些许缓解,但终究肚子里装了不该装的东西,我一阵阵疼痛,在床上直打滚,脸色苍白。母亲紧张起来,果断地说:“孩子,我送你去看先生!”
我知道,父亲出远门去南乡没有回来,家里只母亲一个人。可实在疼得熬不过,只好顺从地趴在母亲脊背上。母亲背着我出了门。那时候乡里没有正规医院,只在离家五里多地的顺和集有一个老中医开的私人诊所。
母亲生于民国初年,封建礼教的毒害使她幼年裹了脚,以致成为她终生生活的羁绊。夜色深沉,母亲背着我,迈着一双小脚,深一脚浅一脚,硬是在乡间的土路上走了五里多地,这对一个小脚女人来说该是多么的艰辛呀!后来在老中医的诊治下,我躲过了此劫。不,应该说是母亲从死亡线上帮我捡回了一条小命。
10岁那年,我在乡小读书。学校简陋,没有食宿。家离学校有五里多地,每天要往返几十里的路程。为学习方便,母亲说:“每天中午你不要回来了,你大爷不在家(我管父亲叫大爷),我给你送饭。”我说:“娘,你走路不方便,不用你送。”母亲说:“那怎么成,一天三趟往家跑会耽误学习的。”就这样母亲天天掂着小脚给我送饭,有时候下课铃没响,她就早早提着盛饭的小罐子在校门口等着了。无论春夏秋冬,我都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
初秋的一个上午,下起了大雨,直到放学时雨都没有停歇。我想母亲是无法送饭了,再说下这么大的雨,我真不希望她老人家再为我奔跑了,我冒雨向家跑去。
在通往家乡的小路上隔着一道古寨墙的护寨沟,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翻过这道沟。沟又陡又深,就是不下雨时翻越这道沟也要加倍小心,不然就会掉下去摔个“泥巴猪”。好在有心人在沟的两坡挖了许多小坑,形成一个方便上坡下坡的土台阶。
当我望沟兴叹的时候,濛濛雨中发现沟底有一个身影在蠕动。她艰难地向上爬着,手中好像还拎着什么东西。一次次快要爬上沟沿时,脚下一滑,又摔到沟底去。当我的目光最后一次定格时,我惊呆了,是母亲!我哭喊道:“娘!慢点!”我从沟旁折下一个树枝,把树枝的另一端递到母亲手里,母亲抓着树枝慢慢爬上来。母亲身躯佝偻,头顶一个湿辘辘的麻袋片,一双尖头布鞋包裹着一双小脚,浑身沾满了泥巴。一只手紧紧地提着一个盛饭的黑土罐子,罐子上翻盖着一个粗瓷大碗,里面斜插着一双筷子。罐子下端还残留着没擦干净的黄泥。我泪流如注:“娘,雨这么大,路又滑,你不该再给我送饭了。”母亲一边摘下破麻袋片披在我身上,一边把小罐子递给我:“傻孩子,下恁大的雨,我不送,你咋回家吃饭呀?”我接过罐子,迟迟没有打开,两只眼睛痴痴地看着母亲,半天没有说出话来,任凭泪水流满双颊。
风雨路上,我掺和着雨水和泪水吃完了那顿午餐。母亲说:“快去学校吧,不然又该迟到了。”说完,蹒跚着一双小脚消失在雨雾中。
在母亲的呵护下,我顺利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从一个弱小的生命逐渐长成了一个身强力壮的大男人。如今有了一个子孙满堂的幸福大家庭。
往事如风,几十年我摇摇晃晃一路走来,母亲是我生命的拐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