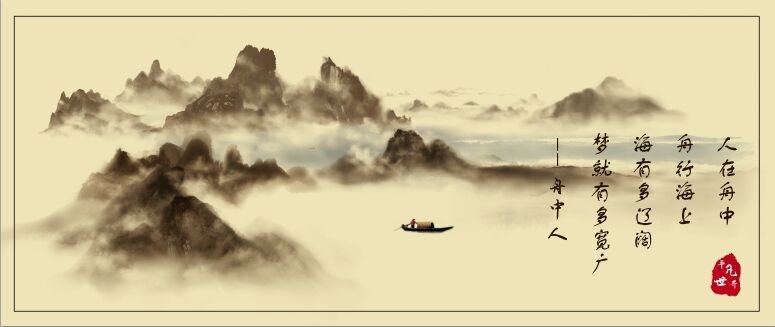【水系】纸上还乡(散文)
【水系】纸上还乡(散文)
这是一个听来的故事。叙述者是我的外公,他已经八十四岁了。他在向我叙述这些往事的时候,有时用第一人称,有时用的却是第三人称。当然,他所讲述的这些可能是一群陌生人的故事,与罗岭有关,但与我的祖辈无关,而我也很有可能用我的想象进行了别有用心的篡改。所以,我的故事在偶数的段落里,而他们的故事散落在奇数的往事里……
0
这里就是罗岭。它的原名叫罗家岭。现在的一个镇,曾经的一个乡。
很久以前,我只能这样说,最先到达这块土地的应该是姓罗的一对父女。和其他所有的地方一样,这里尚未命名,人迹罕至,荒芜一片。然而,他们还是打算在这里安顿下来。其实,到哪里不都一样么,对于无家可归或是身处动乱之中的人来说,哪里都是归宿。我曾经无法想象那些把家安在山里,甚至树上的那些人群,居高望远,他们的脚或者心思一定比常人走得更高,更远。一切从头开始,从清理一棵杂草开始,从捡拾一粒石子开始。从无到有,他们把家建在一个朝南的小山岭上。我不知道,他们父女俩在新搭成的茅屋前,是怀想故土,还是筹划新的开始,对于未来的种种勾画。
更多的命运相似的人们,远远的便发现了升起炊烟的茅屋,发现了这里。在穷途末路的人眼中,即使是再简陋的茅屋,再稀薄的炊烟,也会给人以难得的温暖吧。罗家父女肯定热情接待了一批又一批迁徙或逃难的人们,而这其中可能也包括我的先人。于是,他们决定就在岭头紧靠罗家的地方安下身来:走的路已经够多了,哪也不去了。他们相信这里就是命里的归宿,这里就是传说中的风水宝地。自然,他们也感谢接纳了自己的这个地方,罗家岭,他们将这个精心策划的地名传到比他们跋涉的路更远的地方,朴素,却无比真诚。
我无法揣测他们在一起时是怎样的劫后余生的心情,而当他们对望时又是怎样的惺惺相惜的眼神。我只能在心底把罗家那位素昧平生的女儿和我的母亲相提并论,虽然在我的假想中她无疑是美貌且异常聪慧的。
1
你不可避免地要穿过这一片孤荒的坟地,因为这是外乡人进入罗岭的唯一通途。
当年我爹爹(江南方言,指爷爷)就是被逼着跳进了这片坟地,那时的他,像条狗一样被人追杀,他躲进杂草茂盛的坟堆里,逃过了一劫。你或许还可以找到那个坟堆和坟堆上竖着的一块石碑,写的是“先考罗公英德之墓”,而时间早已斑驳模糊,无法辨认。我知道当时我爹爹就躺在这草窠里,很久都不敢探出脑袋。他向外扔了颗石子,只听见几只鸟雀振动翅膀的声音。他靠在石碑上,伸着两腿,一闭眼,竟睡了过去。
再醒来,他就成为罗岭名副其实的一员了。
我的爹爹江子麟是大清国的最后一代武举人,我曾经在无意中见过他的袍服和顶戴花翎,是那么鲜艳,那么精致。只是,好像从未见他穿过。此外,他还有十八般兵器,亮光光的,锁在一个巨大的箱子里,我也从未摸过。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凶暴,或许是因为我大大(江南方言,指父亲)最终让他的希望落了空吧,当他拿着棍棒在院子里横扫狂舞的时候,我大大就站在旁边,一声不吭。就像后来我大大拿着铁尺追到野旷上逼我读书一样,那神情简直和我爹爹如出一辙。这恐怕就是遗传吧。
我大大最终继承了爹爹开办的“江家饭店”,那时他才二十岁刚出头,一听到食客们肆无忌惮的荤话就会脸红的一个嫩小伙。我大大后来告诉八岁的我说,这份家业是多么沉重,沉重得几乎把我给压垮,我像只蜗牛,把你和这个家背在身上,我一生都要背负着这么一个灾难,那一大堆四书五经,根本无法教我做生意。我就毫不客气地嗤笑他的迂腐,并将他书桌上的古籍统统扫到了地上。我大大好像就在那一刻,看到了他唯一的儿子江继淮此后在罗岭的不同于他的一生风光和艰辛。
2
一个村庄就是一个世界。村庄萧瑟。罗岭萧瑟。
农历十一月。寒冷覆盖田野。霏霏淫雨,已连续下了五日,还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万籁俱寂。行人埋首急走,身影模糊,仿佛被玻璃板压住的一滴水珠,我也只是如此的一个神色慌张的行人。这是多么熟悉的一条道路:曲曲折折,坑坑洼洼,两旁少有树,只有齐膝的杂草。我背着书包走向学校,我牵着爱人的手往家走去,我就走在这路上,离开,经过,或者回。
罗岭多山。有几座山是我和母亲常去的,不是玩,而是耙柴,为整个冬季准备足够燃烧的松针和干果。多年未去的山上,依然野草繁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它们的生命多么富有韧性。而我最近所知道的两个人,一个在路上出了车祸,一个夜里睡去就没再醒来,我们对他们以及他们对自己的突然离去,从未预料。他们,或者他们的孩子,也曾经背着竹篓在山上砍伐野草吗?而现在他们的坟头,恐怕也爬上了杂草了吧。生命萧瑟,我只能如是说。
和许多人一样,我已找不到竹篓,甚至镰刀也早已失去了踪影。它们躲藏起来,要么已经腐烂了吧。没有谁再去关心它们,正如山上的那些日益繁茂的野草和野物,自在的,安静的,生长,然后,消失。
第六日,小雨渐止。
3
野旷。什么是野旷?
乌云向天际一侧拼命奔跑,仿佛从马戏团中逃出重获自由的狼,它的利爪带起阵阵腥风,迅速袭卷了整个田野。我想起很多年后日本鬼子进入罗岭的时候,也是像群饿狼一样,霎那间,罗岭街每个幸存居民的鼻孔里都钻进了一阵又一阵的血腥气,这种腥气在半夜里在熊熊火光中渐渐腾空而起,并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完全笼罩了整个罗岭。
想到这,我总是感到全身颤栗不止,两侧的肩膀向胸前无限延伸,而后背则拼命地向内脏向肚皮挤压过来。在田野上,在空旷得近乎凄凉的田野上,我不知道自己是在被寒冷残酷地撕扯,还是被恐惧狠狠地啮咬。这种感觉好像伴随我已经很久了,记得那个叫柳生的年轻的日本兵高高举起刺刀的时候,我也是如此地像只被掏空了的皮囊,在风里摇摇欲坠。那个叫柳生的日本兵才十八岁,就学会了用锋利的刺刀刺进龙毕老婆的下身,并挑破了她的肚皮,他的脸在鲜血飞溅的一瞬间扭曲得如同噩梦中的魔鬼,而“她还是个孩子啊”,龙毕的老妈痛心疾首地看着自己的儿媳一动不动地躺在青石板上,这样说,竟忘了大声号啕。猩红的血似朵朵灼目的梅花,就这样永久地插在了罗岭满目创痍的伤口上,鲜艳欲滴。
罗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我的眼中,就是一个巨大的野旷,任何时候,任何似血的红,都足以让人们恐惧,甚至恐惧得突然死去。
4
罗岭,离最近的城市安庆只有六十里。那么,离最远的又有多远?从城市进入乡村,只需九十分钟,而从乡村进入城市,我不知道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
爷爷在一次招工中成为城市中一名优秀的厨师。他切的冬瓜片总是透明的,薄如蝉翼。他离开罗岭的时候,我没有为他送行,随他而去的是他的儿子,我的父亲。剩下的,他的母亲和妻子,他的三个女儿,留在罗岭。二十五年前,他的母亲逝世,他的妻子离开罗岭去往他的城市。二十五年后,他的妻子,我七十九岁的奶奶再次回到罗岭,按她的意愿,我们为她准备了崭新的上等的寿材;他的三个女儿,一个在巢湖,两个在他所工作的那个城市;他的儿子,我的父亲,在罗岭已经生活了近三十年;他的小孙子,我,正好二十五岁。
爷爷离开罗岭后,就没有再回来。我每年一次去往爷爷的城市,和他一起买米,和他一起去菜市场。他们都说,爷爷最喜欢我,我最像他,而我却感觉到莫名的陌生,我不知道他在城市中怎样的工作,他也不知道在罗岭的他的孙子日常的生活,他和我中间隔着几百里的距离,甚至可能更远,尤其当他中风之后,他的嘴偏向一侧,显示出我所惊讶的陌生来,那个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优秀的厨师靠在躺椅上,躺在床上,看着我们,仿佛有许多的话要说。直到一九九二年的冬天,他的儿子捧着他的骨灰重新踏上了罗岭的路。那个冬天分外的寒冷,他或许也看到了他的小孙子正在田埂的小路上,朝他飞奔过来。我是来接他回家的。他最后的归宿是在罗岭的一座小山上,坐北朝南。我每年要去看他两次,一次在清明,一次在腊月。每次去,父亲都要在烟雾缭绕纸钱飞扬中向他描述起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还有罗岭的哪些人也陪在了他的身边。我不知道,无所不知的他是否也和那些人,说起我们,说起罗岭的过去,而我知道,少言寡语的他一定是将更多的话留在了罗岭,留在了他的亲人身边。
5
人们常常看见我大大江文元站在“江家饭店”的楼上,遥望。他总是站在楼上。
四十多年了,这条罗岭街还是那么古朴,破败,又是那么喧闹。他熟悉这里的一切,不用望远镜他也能看得见街道的尽头。他知道白雪覆盖下的青石街道,踏上去会有一种清凉透心的感觉,仿佛一捧雪在心里慢慢融化,融化成水,融化成温暖的寒气。他曾经赤着脚从这头走到那头,一共三百零三步,而到她的门前只需一百零一步。
雪还在下,却看不见落在地上。偶尔几只饿得厉害的麻雀飞到雪地上,也是赤着脚从这头踱到那一头。此刻,他知道她是不会突然出现在一片雪白之中的。其实,自从自己按照父亲的意思娶了月霞之后,她好像就从街上消失了,而且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晃就是二十年了。据说,她嫁到了百里之外的地方,一户富足人家。她和罗岭的绝大多数的女儿家一样,离开本土,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成亲,生儿育女,一年到头,难得回一次娘家,这仿佛是此地特有的风俗,又仿佛是她们自己最终选择了她们的命运,幸,抑或不幸,谁知道呢?
文元将领口封了封,冰冷的感觉反而更加强烈。他伸手摸了摸身上厚厚的布棉袄,虽不光滑却十分顺手。这是月霞亲手缝制的。他想起自己曾无数次地抚摩着月霞身上的绿袄,心里却莫名地想着另一张百步之外的面孔。他失神地盯着自己的掌心,好像那上面也沾染了一层鲜亮的绿,可再一看,却什么也没有。
人来人去,只剩下横七竖八的脚印印在雪上,重重叠叠。文元感觉那是一张巨大的网,一点一点地凸起,紧紧地裹住了自己。他想挣脱,却力不从心。他看到一点红色在百步之外缓缓向他走来,他想迎上前去,却怎么也挪不动脚。一道寒光闪过:什么都没有。“网”就随意扔在了地上,怎么看都更像一个无底无边的空洞,整个身体,整个罗岭,都深深地陷在其中。
6
看见我走在路上的我的母亲,在路边的龙塘里洗着衣服。在母亲的眼里,我一点一点地高大起来。而在我的眼里,母亲一点一点地弯下腰来。弯下腰来的母亲,显得比以前更矮了。
我不止一次地提到过母亲和鱼的亲密关系,其实母亲在对鱼产生感情之前,曾尝试过许多不同的职业,干的最长的是在罗岭小学当炊事员。在罗岭,是少闻炊事员这个称谓的,人们一般只是说“烧锅的”,简洁,形象。母亲蹲的时间最长的应当就是那段时间,她在锅旁灶间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宝贵的十多年。每天晚上,我都要陪她到学校去。有时并肩而行,有时我就故意搂着她的肩膀,像个可以依赖的男人一样,保护着她一起穿过一段黑暗的路。她蹲下来,将煤炉底座的通气孔封上,为的是让火焰能够一直烧到第二天。而我就在厨房里四处走动,唱歌,或者朝窗外漆黑的寂静张望,无所事事。歌声是有回音的,然而我却总听不清,正如我一直没有看过煤是如何从夜晚燃烧到第二天清晨的。
接下来,她到北京。到铜陵。到浙江。最终,又回到罗岭。她重新把鱼装进篮子,铺在鱼布上,再散上点水。她蹲在那里,直到阳光垂直,直到鱼全部离她而去,直到父亲来寻她,直到我发现她再也站不回曾经的高度。
7
我母亲月霞纳了二十年的鞋底,却总是忘了给自己纳一双。
有时,月霞也会停下来,把鞋底和针索放在竹箩里,然后向屋后的田野深深地望过去。田野上是一望无际的雪,白茫茫一片。她想起枞阳老家的门前是有一片茶岭的,与这里的空旷绝然不同。每到灿烂的四五月间,新茶便冒了尖,郁郁葱葱的,那绿色沿着梯形的茶岭,蜿蜒直上。她喜欢绿色。她也喜欢和那些村姑们一起,采摘茶叶。她们的手是多么娴熟灵巧啊,只消在茶树尖上一抹,嫩嫩的两瓣茶叶就躺在了腰间的小竹篮中,而那个一触到绿就忘了唱山歌的姑娘不正是自己么?
女人的怀念总是这般没有缘由,没有头绪,伤感却又无比幸福。月霞看见一只灰色的野兔飞快地跑过田野,雪地上一对对小脚印,就像是绣在鞋面上的那两朵并蒂莲,那是成亲的头天夜里自己一针一线地绣上去的。她至今也不明白,自己为何一边绣花边一向着母亲流泪,明天就要到罗岭去了,母亲也一再地说他是个本份老实的孩子,其实自从她那天第一眼见到表舅身后的他,就相信了自己的命,而且一信就是整整二十年。
有时,月霞也会登上前楼,站在总是站在窗前的文元身边,也只是默默地站着,一声不吭。他有时也会伸出手来在自己的绿袄上抚摩片刻,那一瞬间她发现他的眼里仿佛酝酿着少有的温情,又仿佛充溢着痛苦的冲动,使得自己不得不红着脸低下头来,却又听见深深的一声叹息,自己的心便慢慢沉了下去。她是知道丈夫心思的,然而却只能怜悯地看了看他,又恨恨地盯着百步外的那座绣楼:那只是空空的一座孤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