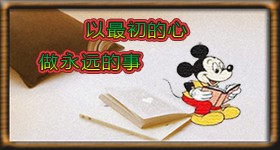【流年】春梦(短篇小说)
【流年】春梦(短篇小说)
一
大年还没过,春天就来了。春天真是好日子。不会再天未黑就降霜打凌,每二天太阳出来,霜惊凌醒,路便泥泞得无法下脚了。不会再夜里悄悄一场雪,厚厚堆积,早晨起来推不开几乎被掩没的门坎,水田堰塘结起的冰层可以承受小孩的嬉戏了。但杯子坪的春天依然寒冷,顺着大梁下来的风很凛冽,吹得脸生疼生疼,耳廓的冻疮被春天的太阳照着再被寒风一吹,微痒里有一丝痛,直钻到心里,久久不散。
从大年初一开始,岳希云就坐卧不安,心神难宁。他希望日子停住,一直就在冬天里,每天晚上窝在火坑边,微眯着眼,吸叶子烟,打长哈欠,迷瞪一会又醒过来,清醒一阵又迷瞪去。他希望冬天留住,是因为害怕春天。前年春上,从来落枕即睡的他突然做起梦来,梦一开头,就没完没了,每天晚上,他似睡若醒,一直在梦里来来去去。春过梦去,他安心了,以为只是偶然。但去年春来,整整一春,又是无休无止的梦。春去梦止,他再也无法平静,他明白,自己被梦寻上了,春天再也不是好日子了。他记得周家大少爷念过一句诗:春梦了无痕,觉得写诗的人一点也不了解春梦,他的春梦痕深迹重,梦里的一切清晰可见,总在眼前。
正月十三,是立春的日子。岳希云坐在火坑边,一边吸着叶子烟,一边不停地打哈欠。夜已经很深了,风停歇了它四处乱串的脚步,归巢安歇,杯子坪安静得有些死寂,除火苗窜起的呼呼声,听不到任何声响。岳希云的老婆见他呆坐在火坑边不停地打哈欠,催促他:搞啥子名堂,瞌睡来了,就去挺!岳希云郁积于胸的烦恼与闷气找到了释放的地方,气急败坏地低吼:臭婆娘,就知道挺尸!虽然骂着,他却知道,赖着不睡不可能,骂婆娘也只是出出气,躲不过的就是躲不过,于是,边说边从火坑边起来,脸不洗,袜不脱,钻进被窝。
梦,如约而至。是刚刚开始热的时候,十来岁的岳希云,挎着书包,跟在一蹦一跳的周家大少爷身后,急匆匆往月溪场赶。周家大少爷穿着整齐的中山装,风纪扣扣得严严的,留着中分发型,头发随着身子的蹦跳,一起一伏的。岳希云跟在周家大少爷身后,一心想听明白少爷念的诗,但不管怎么努力,都只能听到“春梦了不痕”这五个字。他不甘心,跑到前面,说:大少爷,你把这诗从头念念。周家大少爷疑惑地看了他一下,从头念起来,很奇怪,前前后后的诗句喑喑嗡嗡听不明白,就只是“春梦了无痕”来得清晰明了。岳希云问了不知多少次,周家大少爷也很耐烦地不知念了多少次,“春梦了不痕”的前面是什么,后面有什么,岳希云却一直没弄清楚。突然,就到了月溪场的新式学校,周家大少爷跑进教室,上课去了。好几位陪自家少爷到学校读书的书僮跑过来,想岳希云与他们一起玩。岳希云不理他们,趴在教室外,隔着窗户听老师讲课。很奇怪,老师正好在讲大少爷路上念的诗,诗有八句,“春梦了无痕”是其中一句里的一部分。岳希云听老师讲来,有点痴,有点醉,痴里,醉里,却只有五个字:春梦了无痕。
二
春梦了无痕,折磨了岳希云一整夜。他早早地醒来,屋顶的亮瓦透进一团淡淡的光晕,照到床边,应该不是明月,而是天已麻麻亮了。他爬起来,披上棉袄,趿拉着鞋,拿起铁皮喇叭,推开房门。
杯子坪刚刚醒来,东山边的光晕随着晨风到处乱窜,赶得黑魆魆的夜无处落脚。房门一开,寒冷一下子包裹了岳希云,他边哆嗦着边踱到家边的小土包上,用象征生产队长权力的铁皮喇叭吼起来:男劳女工,大娃细崽,今天,给小麦淋粪。声音经过铁皮喇叭扩散,传得很远很远,在静寂的山村引起一阵狗吠。其实,这并不是出工令,而是起床号。起床号响过,各家各户慢慢有了声响,亮起灯火,炊烟渐起,溢出屋瓦,与晨雾缠绕着,飘飘忽忽,摇摇曳曳,聚向东方,迎接晨曦。不知不觉,太阳出来了,岳希云吃罢早饭,挑着粪桶出门时,又用铁皮喇叭吼一声:走了,走了!于是,家门家户,男女老少,只要能挣工分的,都扛锄挑担出了家门,按照岳希云的安排,来到田边地头,开始一天的劳作。
岳希云在杯子坪大队三生产队当着队长,兼着记工员。他出身贫寒,祖辈是大户周家的长工,周家主人见他长得伶俐,派他做大少爷的书僮。大少爷先在杯子坪的私熟里背《百家姓》、《三字经》、《幼学琼林》,后到月溪场进新式小学学新学。岳希云跟了周家大少爷四年,帮挎书包,热天打扇,冷天提烘笼,趴在教室外听隔壁戏,学了一点东西,能写字,会算数。解放后,因为苦大仇深,又有识字算数的底子,大队书记康可德便安排他当三队的队长,兼记工员。
挑了几担粪,几个来回,身上开始冒汗。岳希云估摸时间差不多,放下粪担,从衣兜里掏出记工分的小本子,开始巡视工地,记工分。大队早就定好了工分标准:全劳力的成年男人一天10分,半劳力的妇女小伙一天6分,半劳力都算不上的姑娘娃崽一天4分,上午下午各半。标准是死的,记却是活的,记工分之所以成为一种权力,是因为记工员在大队定的标准之外还要进行现场确认。谁劳动不认真,谁迟到早退,谁磨洋工,谁损坏生产队的农具,甚至谁不太顺眼,记工员都可以多多少少扣谁一点工,究竟怎么扣,每次扣多少,也只有记工员一人知道。年底分粮时,同样劳力同样出工的人户有了差异,慢慢一回忆,就会想起自己某天劳动时不上心曾被记工员漫不经心地斜觑过。后悔肯定是来不及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来年认真劳动,尽量不与记工员作对。岳希云叨着叶子烟,一手执笔,一手捏本,棉袄敞着,里面一件好几个破洞的土黄色毛线衣特别显眼,这件毛线衣是女儿出嫁时女婿孝敬他的,穿了已十多年。他走过三队的每一块麦地,时不时用圆珠笔在本子上画一下,他的到来,仿佛无声的动员,刚才还杵着锄把在地里家长里短的妇女全弯下腰,挥动锄头,松土锄草,刚才还坐在扁担上吸着叶子烟悠闲地吐着烟圈的男人都站起来,挑起粪桶,快步急走。朱益英见他远远地走来,直起身子故意声音脆脆地叫:岳队长,向他送来妩媚灿烂的笑,笑里有份讨好,有份暗示,甚至还有份挑逗,有份激励。岳希云不理她,木着脸,有些庄重地走着,边走边记,既不回应朱益英的问候,也不与婆娘们开平时总是要开的荤得不能再荤的玩笑,令麦地里的男男女女觉得他今天有些怪异。
三
其实,今年岳希云的第一个春梦并不只是“春梦了无痕”这句诗。昨天后半夜,他还梦到了朱益英。梦里,朱益英向他送来妩媚灿烂的笑,笑里有份讨好,有份暗示,甚至还有份挑逗,有份激励。现在看到朱益英与梦里完全一样的笑,他疑惑不解:以前,朱益英见到自己也会笑,笑得平常,笑得浅淡,甚至笑得有些公式,有些应付,为什么今天就笑成如此这般呢?朱益英嫁到杯子坪那天,非同寻常的装束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看出了她的妖娆与妖艳。他还知道,朱益英男人死后,杯子坪很多男人钻她的屋,连康可德也与她有一夜缠绵。奇怪的是,妖娆艳丽的朱益英却引不起他的任何激动,他对朱益英不即不离,冷眼旁观,是杯子坪为数不多的几个不去他家凑热闹的男人。
岳希云正值中年,个头高挑,长得高高大大,周周正正,当了二十多年的队长,显得精明能干。他身强体壮,搭谷挑粪抬石头扛木料,什么样的重体力活都能干,他农活娴熟,犁田栽秧播种做冬水田都是好手。这样的男人,手里又握着派工、记工的权力,惹女人喜欢是自然的事情。他不去朱益英家凑热闹,却并不吃素,乡村男女的那些苟且,不是没有。他与队里的另外几位女社员关系不一般,大家都知道,大家都不说,女社员的男人假装不知道,在一些特殊的时候故意不落家给他提供机会。他经常利用队长和记工员的权力,给她们派轻松的活,出工时有耽搁也不扣她们的分。她们随便找个理由说一声,就可以不参加不记工分的集体劳动,见到他有事无事地笑,笑得别有深意,很是暧昧,他也跟着无声地笑,笑得他老婆牙齿咬得“吱吱”响,只要一有机会就横眉竖眼、咬牙切齿地指桑骂槐,那几位女社员不搭腔,不还嘴,怒气遇不到阻力,找不到着力点,有骂无人回,有气无人理,令他老婆更加气恼,只好回家找他发泄,蚍蜉撼大树般地与他干仗。
岳希云的老婆个头不高,不仅比他矮了许多,早早地就皮肤松弛,满脸皱纹,背部佝偻,而且头不认真梳,脸不认真洗,衣不认真穿,邋邋遢遢,窝窝囊囊,看上去比他要老出许多,很不班配。媒婆郑秀菊越看这两口子越不明白:狗尾巴花配了青冈木,当初真不知是谁说的媒?他老婆虽明知不是对手,却屡败屡战,一点也没有罢休的样子。打架多是晚上,岳希云不出声,耐着性子让老婆的数落顺耳而过,忍无可忍之时,就下狠手痛揍。他老婆先是絮絮唠叨,继而高声叫骂,最后撒泼嚎哭,夹杂着痛哭的诅咒,在夜深人静的杯子坪四处回响,不用尖起耳朵,都听得一清二楚。与岳希云没有瓜葛的家庭,听着觉得过瘾解谗,偷偷暗笑,被骂到的人户,男人颜面无光,女人脸红心跳,背靠背掩被假睡。每天收工,夜幕降临,许多社员内心暗流涌动,期盼希冀越垒越厚,越积越深,刺激得大家坐卧不安。岳家的响动左右着大家的情绪:哭骂传出,如释重负,兴趣盎然地欣赏;一夜平静,大失所望,郁郁不乐地入睡。久而久之,队长老婆的哭骂,成为大家必不可少的佐梦佳品,成为三队特有的夜间娱乐。每次战斗,岳希云都能取胜,但不是完胜,头夜他老婆一“外宣”,第二天他脸上,脖子上就会留下鲜红的抓痕,像母老虎抓伤一般。
曾经有一段时间,郑秀菊经常往岳希云家里钻,说是给他儿子提媒。开始,岳希云的老婆信以为真,殷勤接待,经常拉着郑秀菊说长道短。没多久,她看出问题了:很多时候,郑秀菊都是在她出工,而岳希云在家的时候去。一天,她出工中途返回,敲开紧闭的房门,看到郑秀菊头发零乱脸庞红红;岳希云尴尬难堪讷讷不知所言地从屋里走出来,她忍不住胸中的怒气,也不怕郑秀菊不给儿子提媒,戳着郑秀菊鼻子,叫着郑秀菊的名字痛骂起来,郑秀菊狼狈不堪结结巴巴不知如何解释,手忙脚乱地跑开,一点也没有替人说媒时的伶牙俐齿,沉稳大气。事后,郑秀菊的一位同行想起以前郑秀菊经常对岳希云婚姻发出的疑问,揶揄郑秀菊:当初幸好不是你说的媒,要是你说媒,你一定会把自己说给岳希云了。
四
两年没完没了,无休无止的春梦,令岳希云重新成长了一遍,记事以来的一切,几乎全在梦境里重现。杯子坪的山山水水,坡坡坎坎,一沟一壑,一草一木,每院每家,每人每事,许多不曾经历不曾知晓的事,一些曾经接触和不曾接触的人,在梦里变幻,大事小事,正事丑事,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有,只朱益英和她的那些事从未进过他的春梦。昨晚梦醒,他并不在意,既然杯子坪的人都曾梦过,梦到朱益英也是情理中事,妩媚灿烂的笑只是世事入梦后的正常变异。在麦地边见朱益英送来妩媚灿烂的笑,她笑里那份讨好,那份暗示,还有那份挑逗,那份激励与梦里如出一辙,他疑惑之余,有些魂不守舍。
中午歇工,岳希云一直呆在麦地边,等大家都走后才拖着有些疲惫的脚步慢走。太阳暖暖地挂在天空,春风里有一股子醇香,月溪场上的酒厂是不是正在出酒?他想像着酒入酒缸的汩汩潺潺,深深地吸了几口气,仿佛啜入好几杯老白干,竟然有点慢醉微熏,不辩东南西北。家很近,与麦地隔着一条小溪,向西,下浅沟,上缓坡就到,他心里想着回家,步子却迈向东北方,顺着山势,慢缓缓往上爬。等走到朱益英房前,他呆了:怎么就走到这里来了呢?
刚刚回家正弄午饭的朱益英见他有些发呆地站在门外,掸了掸腰间的围裙,热情的招呼:岳队长,进来坐,他从慢醉微熏里醒过来,怔了怔,顺着她的招呼踱进屋去。屋里的灶坑上挂着一只铁锅,锅底一小碗米饭,旁边的菜砧上是切碎的青菜。岳希云知道她要做烫烫饭,看着年里她准备的一点荤腥也没有的简陋午饭,他内心突然涌出无限怜惜,一个女人,过日子真是艰难,以前日复一日积累起来对她的全部不屑与鄙夷,陡然间消失得一干二净。朱益英有些殷勤:还没吃吧,我给你煮面,一边把剩饭倒起来,洗净铁锅,一边把灶火烧得旺旺的。她脸上铺满微笑,自然纯正,妩媚灿烂,见不着讨好暗示,挑逗激励。柴火的光焰和从门窗透进的太阳光辉包裹着她,她曾经妖娆妖艳的眉眼如婴孩沉睡般平宁安详,静谧无欲,澄明清爽。岳希云怔怔地盯着她,疑惑豁然开朗,她上午的笑只是笑,不存在讨好暗示,更没有一星半点挑逗激励,他上午见到的只是自己的梦境。他回过神来,觉得自己澄明清爽了许多,急匆匆说:别煮了,我马上回去,不等朱益英反应过来,就跨出了屋门。
刚跨出朱益英的屋门,岳希云就与自己的老婆撞了个满怀。因为跨步太急,他老婆被撞了一个趔趄,差点跌倒。她后退两步,站稳脚跟,跳起来戳着岳希云的鼻子,一语双关地骂了起来:臭不要脸的,中午也不歇气,跑到这里偷人来了。岳希云满心的平宁安详,被老婆骂得烟消云散,灰飞烟灭,怒气奔涌,抡起手臂一巴掌扇过去,等他老婆连打好几个转停住身形时,他已没入坡下的树丛,不见踪影。岳希云的老婆抹了抹被扇出的鼻血,回转身去,见朱益英靠着自家屋门,两眼怔怔地盯视着前方,仿佛在看她,又仿佛在看远山,表情淡雅空漠,静谧无欲,找朱益英出气的念头被她怔怔的眼神阻止,悻悻地返身跑下坡追赶岳希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