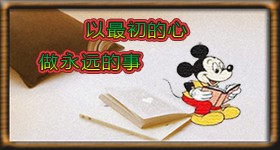【流年】救赎(散文)
【流年】救赎(散文)
题记:在去年的十二月初,八十岁的老父亲患脑血栓,在老家的市中医院住院,在半个月的陪床中,我看到了一个个生命的痛苦和挣扎,也深刻地感受到了不同生命的锐气、坚韧、迫切,还有生命的必然。许多给病人陪床的亲人,也与我一样用爱在完成自己的救赎。
父亲患脑血栓,先后住院不到两个月,就离开了我们。一想起父亲,就想到医院里同样经历病痛折磨的人们。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最令人恐惧的是一片寂静,那不是宁静,那是死寂。只要能听见声音,看到笑脸,也是个热乎气,体现人间温情。这是我始终追寻的感觉。
(一)
通辽的风很大,路上的冰雪、树木和枯草透着寒气,我的心薄凉。
我到了父亲住院的中医院,走到生病父亲的床前,父亲似乎认得我,还张嘴哭了。
后来父亲始终在嗜睡。这是脑血栓的症状。医生说,老爷子有医保吗?姐姐说,有啊。便找出了医保本。医生说,那昨天说没有。姐姐怯怯地说,刚回去找出来的。医生说,连看也不看一眼,气咻咻地甩下一句话,重新调整医疗方案。看来有医保,没有医保治疗是不一样的啊。有什么东西在嗓子里哽着,说不出来。
有医保的,治疗费就没有底了。原来是临床陪护的病人家属,那个男人说。
那穷人呢,就等着死吗?
我问父亲的病怎么样,医生说,脑血栓就是恢复的问题了。只要不出现并发症就不会有大的危险,可是老人毕竟岁数大了,又有气管炎,心脏病,一口气上不来,就过去了。
当静下来以后,我环视着病房。病房,只有两个病人。一个是父亲,另一个是个女病人。
女病人姓张,在床头的病历卡上写着。陪床的是她的丈夫,头发稀少,额头发亮。我以为是个老师,原来是郊县工商局干部。耳朵有点聋,他说是放炮崩的。耳膜穿孔了。
他笑着,很庆幸的说。那次很危险,命差点丢了。他听着收音机,收音机里是评书,我听着像《薛刚反唐》。他说是《童林传》。听着听着,就听见了他的鼾声。
收音机是一直响着,我不知道他听清了没,我却没有听进去。躺着的妻子抬腿要起来,要下地。他连忙上前扶起,给穿上鞋,扶她下地,扶着走到门外,到走廊的厕所。
一会儿回来,妻子自己一步一挪地走了回来,很费劲的样子,到了病床的柜子上,端起杯子的水,用吸管慢慢吸着,又拿一个苹果,用刀片一片片削着,哆哆嗦嗦地放进嘴里。
男人说,妻子才六十岁,是从糕点厂退休的,得脑血栓六七年了,现在小脑萎缩,又得了帕金森综合症。你没有看她手哆嗦吗。他痛苦的脸有些扭曲,用下巴给我示意,指着他妻子的正在拿苹果的手。
最痛苦的事,她说话不利落。男人跟我叨咕。我说呢,一下午了,我没有听到她说一句话。
是脑血栓后遗症吧。
他有一个儿子,现在沈阳做珠宝生意。一个女儿在大连打工,现在回县里生小孩。
我问,大姐想儿子吗。女人眼睛湿润了,话不流利,听不清楚。男人听清楚了,告诉我,儿子做生意忙,女儿孩子太小。丈夫成了翻译了。
可见,她的心里一直想孩子。
病房里来了几个男男女女,来看着俩口子。男人告诉我,这是妹妹一家,是开超市的。
一会儿,都走了,他俩也跟着去了。男人说,他妻子晚上睡不着觉。
晚上,我才知道,父亲是重症监护,晚上灯是不能关的,医护人员晚上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来,查体温、量血压,问情况,监控仪不停地响着。
我这个正常人都睡不着,何况一个病人呢。他俩人不在,我们陪床的也有地方休息了。
他们每天都这样,白天做个针灸,喝一份中药汤药,就去妹妹家住了。有时,他们也不想去,可是每天车在楼下侯着。
女人的腿脚好多了,话也流利很多。我看到她的病床上有一张纸。是《希望的田野》的歌词。男人说,医生说,多念些文章,就是练语言的。看来女人在男人的妹妹家书没有少练习。
七八天时候,女人的儿子和儿媳妇来看她。是开车来的,三百六十多公里,跑了大半天。儿媳妇给她买了一个玉镯子。跟女人说,这是辟邪和保佑的。
女人说话流利了不少,脸上有了红光,连声说着,我听出来了,是这么破费。手却麻利的套进了镯子里。
男人一直笑着。作为父亲感到好宽慰。
第二天,儿子、儿媳妇一起来的,找医生办理出院手续。回家看看,他指着妻子跟我说,看到儿子、媳妇了,她想外甥孙子了。见点好了,回家养着吧。
我问,没有医保吗。男人说,有是有。报的不多。再说,这是慢性病。
也许正如人们所说,病在养,亲人的抚慰是最好的药。
(二)
一天早晨,窗外下着雪,雾蒙蒙的。犹如我的心境。
我无时无刻地担忧父亲的病情,每天输十几瓶液,也看不出好转呢。
我陷入了深思和静默。姐姐一直在向上帝祈祷。
就这个病房,就这个床位?一个大嗓门的女人跑进来。女人也就是六十多岁,穿着红色防寒服,胸前挎着个小包,跟市场卖菜的似的,脸黑黑的,胖胖的。精神头很足。
护士进来,指着父亲对面那个床,让我们把东西收拾好。来病人了。收拾下好吗?比医生要温柔多了。
抬进来,慢点。她声音中有点嚣张。
只见一个衣着黑色羊绒衫、里面穿白色衬衣的老人,坐着轮椅被推了进来。
老人又被几个人抬到病床上。老人脸很白净,很瘦。躺着床上就哎呀的喊疼。
女人掩饰不住的疼,问,怎么了?
老人说,咯的。女人风风火火地跑出病房,又拿来一个跟病床上一样白色的被子,看来跟医院的人很熟悉。
他只是点了点头,躺下了。
她对一同来的一个女人说。老妹子,回家找个凳子,不然怎么坐呀。
她又对两个男孩子说,去出去定几个菜和饭,你爸愿意吃的。她很豪气。
女人坐下来,扒橘子给老人吃。老人只吃了一瓣。翻来覆去,难受的样子。
更长的沉默。只听女人说,今天那个医生休息,明天早晨检查。
老人睡觉,好像很累。老人话很少。
她跟我小声说,那人是她老公,她指着手里拿着病历卡片,说姓刘,今年76岁,是建筑工程师。市里很多高楼都是他设计的,说到这,声音也又高了起来,不无得意和自豪。
我说,你老公显得很年轻。女人说,他脸白吗。
女人说,他得脑血栓也七年了,现在脑萎缩,好几年不能走路了,也是在这医院治疗的。我跟他们很熟。
她是做水果生意的,有两个儿子,也一起做,做的很大,有钱。
她絮叨着,这两天,他吃不下东西,吃啥吐啥。是呀,我看老人脸黑瘦的,病就不轻。
一会儿,俩个儿子送来饭菜,她老公只吃了几根土豆条,半碗米饭就撂筷子了。
她边收拾东西,边对两个儿子说。去忙你们的。有我陪你爸就行了。
晚上,开始俩人躺在一个床上。后来,她老公翻来覆去睡不着,把她赶下床来。
她急了,找来一张海绵垫子扑在地上,躺着。她老公总是哼哼。她就说拍着床沿,训他,真虚。极力装作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样子.
她一夜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有时坐起来,跟我聊天。
吃不进喝不下的。她总觉得老公不是好病。她摇着头说。她问我,你父亲多大岁数了,我就跟她说了年龄和病情。
她好有经验似的叮嘱我,这种病,治疗方法都一样,没有并发症就好恢复。看几天,回去养就行了。
人岁数大了,就难治了。她指着睡觉的老公,这七八年可糟心了,吃喝拉撒都我管,别人我不放心。她说,老公在建筑公司当工程师,为这个家没有少挣钱,退休了没有事干,在家坐着。她做买卖,也没有时间管他。老公风光惯了,也不会做饭,有一口就吃一口,自己喝闷酒,还挺能喝,慢慢就做了病。
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吗?你知道我是多么脆弱和恐惧吗?硬挺吧,只要他活着就好。越说她越来越难以控制情绪,也许压抑了好多年吧。
她那样直率,我原来以为她是老人的保姆呢。两人的性格差距太大了。我心里愧愧的。
第二天,老人去做CT,X光检查了,各种化验呀。我们几个陪床的帮她抬着。看来来到医院都这样,都要让机器审视一遍。我以为中医院,只有望、闻、问、切诊呢,原来也要走这样的流程,这是进步,还是悲哀,我不得而知了。
在推向检查室,要从住院部六楼下去,到另一个楼的一楼。没想到,那么瘦的人,抬着还很沉。我当时很恐惧。我抬父亲去做检查也是这样的感觉。
说句灰色的话,死沉死沉就这样来的,人的身体缺乏元气是离死亡很近的了。我感到很恐惧。
女人取来片子,让医生看过。就跟老公说,我们转院吧。这里的医疗条件不如市医院好。老人只是点点头。
两个孩子来了,这次转院是用的医院120。
女人临走时,让我看好拿个凳子,一会有人来取。
出病房门,她低低地跟我说。检查了,脑血栓没有大碍了,是肝癌晚期了。她戚戚地说。我不相信地盯着她,是真的吗。
我说呢,她为什么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了。她的心都要碎了。钱再多,救了命吗?!
我不敢送她们,只是朝窗外看着,120车鸣笛开出院子。
我无言地坐回椅子上。
(三)
雪后的天气,格外的冷。屋子里闷热,窗外只欠一个缝,一股凉丝丝的风滚了进来。
下午,一大帮人进了病房,一个戴着圆帽,身穿紫色戴圆圈的大襟棉袄的老人走了进来,手里拿着收音机,还在唱着“二人转”。
坐在父亲对面的病床,男男女女忙活着。听着,好似是儿子、女婿、外甥们。
老人嗓音嘶哑,不时的说着什么,我也听不懂。晚饭是外甥女从饭店拿来的。菜是回民菜,我才恍然大悟,老人衣着打扮就是回民呀。
饭后,老人房间里外走,一点也坐不住。
我就跟他唠嗑。他说自己姓曹,75岁了。是回民。是郊区粮库搬运工。我一听,跟父亲是同行。我说,我父亲也是粮库的。也许你们还熟悉呢。他说,你父亲多大呀。我说80岁了。他说,也是脑血栓。我说是的。一脸的关切,我很感动。
他嘶哑着,很费力地说。我们那时候累呀,可是生活还行。粮库的人还缺粮食吗,饿不着。我对老人多了一份亲切感。
他说,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开大车,二儿子瓦匠,大女儿是老师,小女儿是做生意的。
我一看,都是小女儿和女婿在忙活,手续也是小女儿办的。小女婿,胖胖的,头大大的,脖子上戴个金链子,是个爽快人。
他跟我说,老人十年前得的脑血栓,现在小脑萎缩。现在旧房子拆了,置换了新房子,家里热的,就发病了。不会享福。他叹了一声。
我说,他老伴呢。他说在外面打麻将呢。说完止住了话。他妻子进来了。高高大大的一个女人,穿金戴银的,貂皮大衣最显眼,很是讲究。
晚上陪床是小女婿。他出去买了一瓶酒和熟食。我俩坐在地上边喝边聊。他家是做肉食生意的,说起来,我有做生意的朋友,他都认识。
他说,这个家很复杂,老人没有人管。老太太每天在外面打麻将,老岳父在中秋节一个人,就一盘花生米,喝了一瓶散白酒,喝的胃出血。一年见不着儿子女儿几回。
我问,啥原因呢。他说,还不是钱惹的祸。老人旧房子拆迁了,给几套房子和钱,都想争呀。我才不跟他们争呢。看他们那点出息。
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几个儿子、媳妇轮流陪着老人在走廊里走。就是后半夜也是这样。
我跟他小女婿说,越不睡觉,越熬心血,心血不足,越睡不着,拿不是恶性循环吗。是的,他点点头,本来老人就血素低,贫血。
可是老人,不行,不走,就两眼圆睁,背着的收音机声音开的大大的。
就这样,无奈和苦恼也困扰着他们。
第三天,他小女婿跟我说,原来想去长春了,那里看脑血栓最好了。现在准备去北京看病,原来检查结果,是喉癌和胃癌,没有几天了。
我疑惑地看着他。他很悲伤,掐灭了手中的烟头。
(四)
窗外黑漆漆的,楼道里静静的。
病房里进了一个女病人。姓于,是脑出血。护士给挂上了病历卡。
只有一对年轻夫妇和一个老太太送来的。年轻女人穿着红色上衣,也就是三十岁左右。还不停地喊着,老姨醒醒,老姨醒醒。要哭的样子。
那个老太太是年轻女人的母亲,是女病人的姐姐。
安排完,输上液。年轻女人病房静了下来。
年轻女人坐在那里默默的,握住女病人的手,喃喃自语。一如我刚来看父亲的神态。
我看她紧张的样子,就想跟她聊聊的,缓解下情绪。她说,女病人是她老姨。老姨家在辽宁义县,在这铁路中学食堂打工。下午五点吃饭时,嘴歪歪,说不了话。
我问,她家人呢?她说,老姨夫在老家里,有很多地,正在打粮食。儿子也成家了,媳妇坐月子呢。明天来。
护士来给病人量血压,血压高,血糖低,头上出汗了,眼睛也不睁。也是嗜睡的状态。
不知道是几点了,女人醒了。想解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