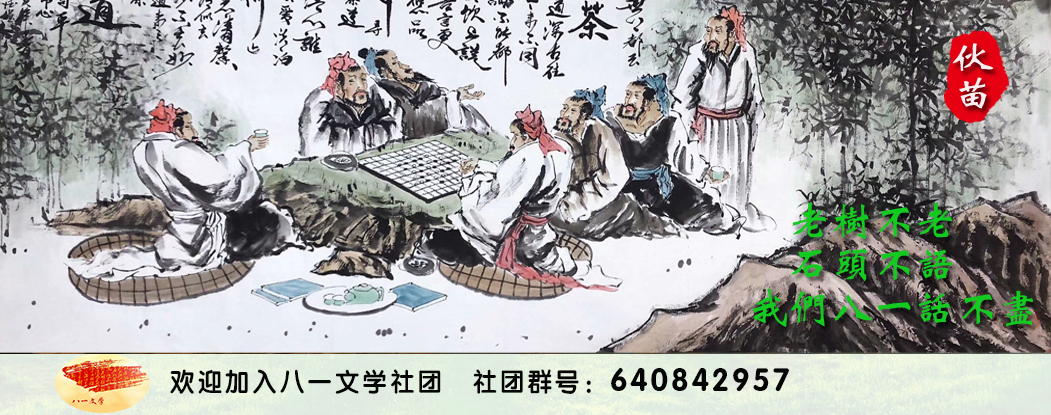【八一】杨梅花开(小说·家园)
【八一】杨梅花开(小说·家园)
![]() 一
一
我再次踏上了梅村的土地。
六月了,天空还飘着朦朦胧胧的细雨,就像四月梅雨天,乡村笼罩在压抑的氛围里。
阮叔院子门前挑起两条土白色幡布,门楹贴张无字的白纸,这是当地办丧的习俗,告诉人们逝者还不到该去的年龄。我身体都软了,扶着门框的手,缓缓往下滑,跪到了地上。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杨梅了。
阮叔失神地看着我,眼睛像池塘里牛儿打滚过的浑水,几十天不见,人都苍老了。大半晌,声音沙哑道:“杨梅告诉我,你有事离开梅村几天就回来,几天过去后,她就病倒了。我日也盼,夜也盼,盼你回来她就冇得事。唉,现你再也听不到了,她白天黑夜里不停喊你‘哥’。”
我双拳狠砸自己头,哭声里,发出绝望的吼叫。阮叔伸手拢住我双肩,说:“娃,别把你身体也伤了。这是她的命,三伯婶说,她是被后院杨梅树精迷失了心智,临走前,还藏着躲着绣那杨梅花。杨梅花能绣吗?自古以来谁不知,谁见杨梅开花谁倒霉,她偏偏犯下了忌讳。”
“绣的花呢?”我哽咽着问。
阮叔把我从地上拉起来,到厅堂坐下后,这才说:“在她坟前烧去了,后院几棵杨梅树我也砍倒了,不想让它去再害人。她屋里东西都没有动,我怕她有什么要留给你,等你走前到她屋里看一看。”
“爹,我不走,留下陪你作个伴。”我由衷地道:“留下来,每年清明到杨梅坟前点上两根蜡烛一柱香,让她知道这世上,还有人惦记着乡里有个女孩叫杨梅。”
“这声爹,俺就厚着老脸应允了,俺心里也早就把你当作女婿待,女婿也算半个儿。”阮叔端起袖口揉揉眼,眼睛已经没有泪:“杨梅说得对,梅村不是你呆的,乡里人土头土脸混不了出息。歇几天,待到心平再走吧。杨梅刚去那两天,我陪她身边也死去好几回。但活着的人还是要活呀,咱们不好好过,杨梅在下面也会过不好。”
阮叔拐进天井旁的正厢房,他曾说,这间要留给杨梅结婚做新房。阮叔磨蹭了大半天,才从屋里走出来,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封面写着我的名,内疚说:“梅村有电后,公社知道你会鼓捣水电站,就跟大队来要人,是我顶住了,说你没有改造好,还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革委会的李主任,打土匪时,我曾救过他家老少的命,他也拿我没办法。上个月,公社又在问,你有冇改造好。你说不去美国了,那就到公社水利工作站吃公家饭。杨梅说得对,这人呀,好歹也得往高处走。别怪爹私心,我嘴不说,心里可明白你和杨梅好着哩,当时我只想咱家三口在一起热热闹闹过日子。”
下午我独自到杨梅闺房呆了好一会。几年来,我头一回迈进这间小屋子,窗户面对后院的菜园,几棵杨梅树不见了,青菜长成杂草似的,园子荒芜了,放眼望去满目的萧条。床上被褥整整齐齐地码着,枕边摆着我送给她的北京布鞋和柠檬香的抹头油。靠里墙,一方方小手绢叠起来有书厚,她曾经一张张拿给我看过,这些都是她空闲时绣的花。我静静站在小屋里,注视着每一样物件,不忍伸手去触碰,生怕惊动了杨梅远去的灵魂。只是苦了我,从此后,再也听不到她叽叽喳喳的声音。
晚饭时,没忘记在杨梅坐的位子前,摆上一付碗和筷。我和阮叔白天把话都说完,两人对视一眼开始抿起杨梅酒。接下来,我喝多了,端起碗来往杨梅的碗边碰一下,“叮当”响一声,扬头喝一口,阮叔也迷迷糊糊在学我。“叮当,叮当,叮叮当”,清脆的声音,在寂静夜晚是那么的响亮。
我做梦了,梦到杨梅树开了花,梦到杨梅在杨梅树茂密的绿叶间,探出月亮般干净的脸盘。她露出那颗俏皮可爱的小虎牙,两口小酒窝,三分浅笑带着七分甜。
二
梅村村口有棵老榕树,伸出来的粗枝上吊着一节短铁轨,铁棍一敲起,“当当当”地飞上了天空,落入山谷后,又传来“嗡嗡嗡”的回响。响声中,村里狗儿先赶到,它们聚在榕树下,这只亲热舔舔那只头,那只轻轻咬咬这只尾,或是撒娇似在地下打着滚,或是绕着榕树转。几只凑热闹的公鸡和母鸡,混在狗堆里。它们张牙咧齿,一惊一吓地,扑闪着翅膀,这边飞,那边跳。
渐渐地,榕树下围满人,他们是梅村能挣工分的劳动力。阮叔是生产队的小队长,这时他就是大领导。他人不高,人可精神着,为了让大家都能瞅见他,每次讲话都是站在盘出地面的树根上,这一来,比乡里人自然高出一个头。他左手拿着笔记本,右手食指头探到唇边沾口水,翻看着。昨晚油灯下,本子里,他已经安排好生产队今天做的活。
村里懂得写字的没几个,阮叔是其中的一个。年青时,他是梅村的民兵,白天配合解放军进山去剿匪,晚上还要来回几十里地走夜路,参加夜校扫盲班。提起这段经历来,他老摇头,说识字比在山里、田间、地头干活还要累。后来我翻看过他的小本本,十个字里倒有一半错别字,只有他才明白写的是什么。比如耙田的“耙”,写成了“八”,开渠的“渠”,写成了“区”,蓖麻油的“蓖”,直接写上“屁”。
阮叔干咳了几声,一双不大的小眼睛,犀利地在四周扫一遍,人群安静了下来:“谷子灌浆了,田里还得施次肥,催催它。仓库化肥不多了,每组安排两人随杨梅到大队挑尿素。”
阮叔嘴里说着的杨梅,站在我身旁,几天前才认识她。
大前天,大队通信员领着我,沿着崎岖山路绕着山岗转。衣裳都被汗水浸透了,喉咙火烧火燎干渴着。晌午后,走进了梅村,在路边一道围墙下歇下来。这是一户人家的后院,主人种了几棵杨梅树。那果儿,一粒粒,红彤彤,绒球似的,闪着亮晶晶的芒刺,一簇簇坠在枝叶间。
通信员干咽着空气中的杨梅味,喉节上上下下地滚动。他放下了行李,蹲在墙根下,拍拍黝黑宽厚的肩膀,对我说:“来,你身轻,摘几枝果子解解渴。”
我迟疑:“可以吗,主人你认得?”
通信员大咧咧道:“哎,乡里乡亲,晓不晓得没有关系,采几个果儿不犯法。”
我也渴,听他这么讲,踩着他膀子爬上土墙头。冷不丁,围墙狗洞窜出一条大黑狗,吓得通信员蹦到路边一堆柴垛上。就刚才,还跟我显摆他在部队当过侦察兵,如何如何的英勇,一条狗,让他颜面突变吓怯胆。
那黑狗,仰起头,一会左,一会右,冲着我们“汪汪汪”叫。它的利爪深深抓入泥土里,往后屈着腿,鼓出一条条结实的肌肉,整个身子带着力量往前倾,随时准备要攻击。
菜园内,一位十七、八岁模样的少女,身穿水红色衬衣,肩上打的补丁有巴掌大。她左手臂弯挂着小提篮,右手举把小剪刀,弯腰朝紫蓝紫蓝的茄子蒂头剪下去,一根根落到竹篮里。听到狗在叫,她抬头,看到有人骑在土墙头,握紧剪刀贴胸前,脚下布鞋露出的趾头,下意识往草丛藏。也许是没见过这张生面孔,盯住我,转动一对乌黑的眼珠,目光警觉又疑惑。
这一天,我认识了梅村一位可爱的女孩,她有个好听好记的名字叫杨梅。杨梅她爹就是小队长,我是唯一分配到梅村的知青,一切自然由他去安排。乡村是个自然村,没有搭盖知青点。他把前院一间土坯房腾出来,顺口道:“一个大男人,煮饭不方便,俗话说,多个人,添饭不添菜,杨梅灶头不差你一口。吃多少,用多少,这账我会记着呢,到年底,分红时再按人头平均摊。”
阮叔合上笔记本,伸出食指冲着我比划道:“这农活,虽然粗,不比识字要容易。到地里,田埂恐怕你眼下都站不稳,教你现在还费功夫,你也随杨梅去挑肥。”
三
今天一大早,阮叔见我起床后,又是挤牙膏,又是拿雪白香皂往毛巾抹,瞪着双眼像看西洋镜。等我漱洗好,阮叔不屑地摇摇头,嘟嘟囔囔道:“城里人过日子,就是这么瞎折腾?”
“桂花香吧,乡里八月间也有这个味。”杨梅陶醉了,眼睛半闭轻轻地呼吸,脸上露出小酒窝,三分浅笑还带七分甜。
阮叔不满扫了杨梅一眼光:“这个香,那个香,有锅里蒸出的米饭香?还愣啥,出工了。”
话说完,取下宝贝似高高挂在木壁上一截乌黑发亮的铁棍,倒背手,出了门。看得出他对我有成见,两天前,送我来梅村的大队通信员,临走时也没忘记叮咛他:“大队书记吩咐了,他这知青成份不一般,所以才分到自然村,要好好监督他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走吧,我爹敲钟了。”杨梅听到村里扬起“当,当,当”的响声,冲我伸出一截小舌头,扮了个鬼脸:“你别怕,他最凶就是这个相。”
昨晚我就听到他父女俩在嘀咕,原本是阮叔带人去挑化肥,杨梅说:“爹,我替你。天热了,顺便到合作社,剪几尺布料扯两件薄外套。家里没有见得人的衣裳,见了生人都害羞。”
她说完,还端起眼角瞄了我一眼。
杨梅知道她爹的分工,扁担替我带来了,两头扎着捆化肥的棕绳。她把一根两节多长的竹筒挎到我肩上,告诉我:“里头冲的是酸梅汤,口干了,拨开木塞倒着喝,很解渴,防中暑。”
几个妇女交头接耳在议论:“杨梅这丫头,见到外乡人,身上刺儿变软了。”
梅村只有几十户人家,姑娘也只有那么几十个,杨梅是其中最漂亮的姑娘。后来我才知道乡里人给她取个外号叫八角螺,意思是浑身长满刺。那螺生在水田里,是乡里人饭桌上常见的一道菜,要是浑身带着刺,谁还敢去碰,谁还敢去摸,更别提嘴儿对着嘴儿吸螺蛳。这个外号不很雅,但也让人明白她的脾气。乡里人没见过玫瑰花,不晓得拿带刺的花儿打比方。
杨梅不理会,当着没听见,大大方方地吆喝着我跟她走。
回来的路上,我出尽了洋相。在大队部,我跟杨梅抢着装四包尿素挑,她毫无商量地往我扁担一边捆上了一袋。开始还轻松,越走肩头越沉了。上坡时,双脚好像灌满铅,每抬一步都有千斤重。下山时,两腿打哆嗦,一个劲儿想往山下冲。杨梅见我踉踉跄跄喝醉似的,一路抿着嘴儿笑,叫我累了歇一歇。她的话还真不能听,越歇越想歇,被他们远远地甩身后。这可连累了杨梅,她走一程,放下担子回头帮我挑一程,我恨不得地下裂开一条缝,惭愧得没脸敢瞧她。
回到梅村天黑了,我那件白衬衫的肩上,血肉模糊成一片。阮叔见我这模样,想笑没笑出,撇撇嘴,摇摇头,很不满:“你看你,一个大男人,咋是这副脓包相。明儿不许再穿白衣衫,乡里人瞧在眼里不吉祥。哼,戴孝似的。”
“泡泡脚,会解乏,呆会拿针线把脚底水泡再穿透。”杨梅端着小木盆送来了温水,转身又取来从菜园子掰下的芦荟叶,上面插着一枚带着线头缝衣针,教我使用芦荟处理水泡的使法。她累一天,没埋怨,白了她爹一眼:“谁天生下来啥都会?人家可是城里的读书人。”
“闺女咋就偏心了,平日对爹也没这么去孝顺,女大不中留,胳膊儿尽是往外拐。”阮叔带着醋意说。看杨梅粉脸红起一大砣,觉得讲出这话过头了。他对这个女儿特别宠,生怕她使出什么小性子,摇着头又把话儿岔开了:“对,城里人,平日运动就是跑跑步,或是一大伙人汗流浃背抢个球,较起真来啥也不管用。”
然后到屋里拿出一瓶紫药水,帮我抹到肩头上,心疼道:“这瓶紫药水,两年前取回还没拨过塞,上次我手背划破化了脓,也没舍得用,今天倒是给你开了荤。”
四
大队挑肥回来后,我下田泼了几天的尿素。第一天,连人带桶从田埂摔到田里好几回,逗得乡里人笑得差些背过气。阮叔又好气,又好笑,不停摇着头,几乎把我当作废人瞧。正好村里放牛的老田头,患上严重关节炎,要住到嫁在山外的闺女家看病,杨梅央求他爹让我接过老田头的活,摇身一变我又成了放牛郎。
队里水牛有八头,还有两个出生不久的小牛犊。每天早晨钟敲响,我就自觉来到生产队的牛圈。刚开始,拉开木栏栅,任凭我咋吆喝,它们神态安然在牛圈散步似的,许久后,才慢慢吞吞走出来,那对圆圆的大眼睛,和阮叔那双小眼一个样,根本没把我装里头。
水牛一出栏,倒是它们领着我,慢悠悠地往村外那条小溪走。小溪绕着村庄蜿蜒曲折着,河畔长满扭着身腰的河柳,长长柳条疏密有致垂到水面上,两岸如挂起两道翡翠似的幕帘。小溪下游拐出村口处,水流开始有落差。村里人在这里造了一间臼米房,水车筑在小溪旁。水车不知在这转了多少年,木色乌黑乌黑地发亮,阳光下,鳞片似,一闪闪,折射出细如发丝的光茫。
臼米房下方是片烂滩涂,长满嫩嫩的青草,还有一窝窝芦苇丛。牛儿低头啃了大半晌,圆嘟嘟的肚子开始撑出油油润润的光滑。正午日头当空照,火辣辣照在大地上,牛儿趟到浅洼里,打着滚儿水花四方洒,然后眯起眼睛趴在水面似乎在打盹,脊背上抹满一层厚厚的稀泥,待到泥巴干了剥落下,又在水洼里翻去覆来地折腾。
看它们随性的模样,心想,做牛比做人简单和自在。我胡思乱想时,杨梅身穿裁缝昨天交给她的新衣裳,站在臼米房屋檐下,摇晃着小手跟我打招呼。
我从芦苇丛遮阳处爬起来,走到臼米房。她已经把篮子里的碗筷摆在石板上,一海碗红薯粥,几个蒸熟的红薯,还有两根她自个腌制的水萝卜。看我狼吞虎咽的吃相,她抿着两片薄薄的嘴唇笑出声,才开口:“慢慢吃,别噎着,没人跟你抢,明天我早些给你送。”
祝贺老师作品获绝,恭喜恭喜啦,问候老师晚上好,遥祝夏祺。
杨梅的三分浅笑七分甜,阮叔虽浑浊却犀利的眼神,村头榕树的铁轨钟声,神秘的杨梅花等等,每个元素都都令人印象深刻。
小说有那个时代的遗憾和伤悲,也有鲜亮活波的音符。如行走于密林中,时而阳光,时而阴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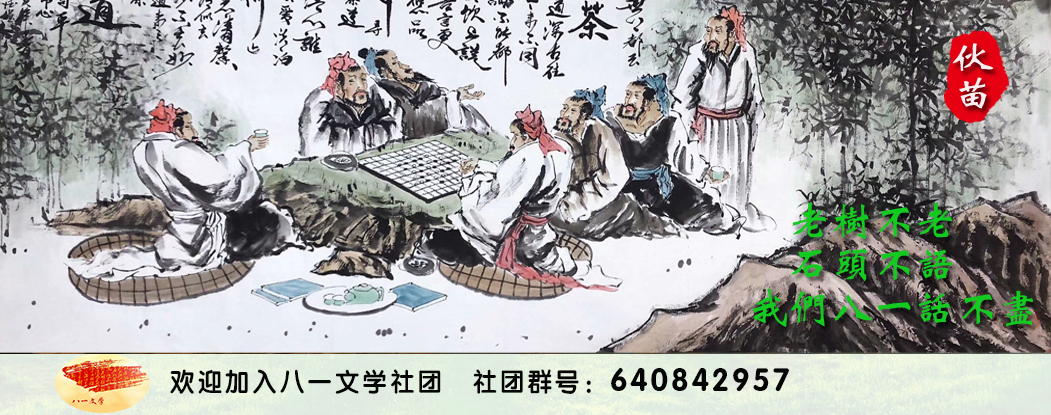
其实老师在这篇小说中已初步展现了地方语言特色,这是一个好的开端,相信会达到老师预期的效果。
关于地方语言的运用,我也尝试过,不过有个明显问题就是有些地方语言非常能准确的表达当时当景、人物表情情绪、人物特点,而且诙谐幽默,但若是一翻译成普通话或者直译成方言表达出来,就没有那个效果了。或许是我本身运用的能力问题吧。
不知老师在这一点上有何感想或者经验可以分享?
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