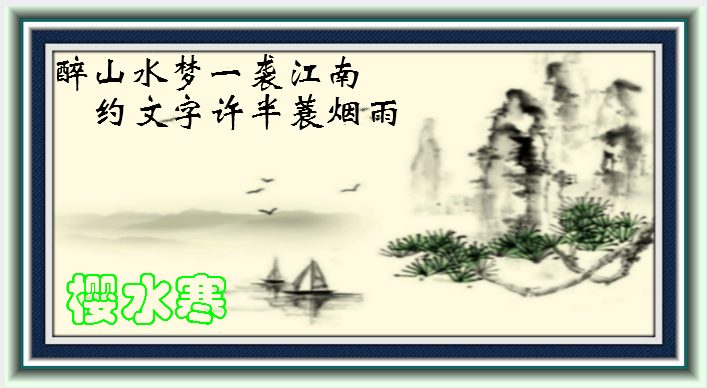【江山·好声音】【流年】时光书:半生心思,一壶江山(散文)
【江山·好声音】【流年】时光书:半生心思,一壶江山(散文)
![]() 一
一
多年以后,当我老去——
老眼昏花,再也看不清江山文学网上的文字。
两耳失聪,再也听不见从江山文学网传来的好声音。
那时,我便开始回想,一遍一遍地回想……
二
二〇五二年,我八十岁。
那年春天快要到来的时候,我隐居在老家月湖边的一间屋子里。
说是“隐居”其实有点牵强,到了晚年,整个人变了。从外表到内里,最大的变化就是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纹路像起伏的沟壑,一层又一层,牙齿也掉得没剩几颗……而内心,越来越向往“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的生活。
那间屋子,建在当初云生住过的那间木屋的原址上,但要豪华太多了。表弟买来最环保的涂料,居然为我把墙壁刷成紫色,那如薰衣草浪漫的紫色啊,是我年轻时最喜欢的颜色,可以让我安然入睡。
家具都是原木的,早在半年前就让家具厂做好了,晾晒仓库里。衣柜、床架子、床头柜、书柜、储物柜、书桌、餐桌、椅子、沙发……把一间二十平米的屋子塞得满满登登。
我从城市回到农村,除了一些必要的衣物和生活用品、小家电,就是十几箱的书了。表弟将车从宁波开到上海,又从上海开回宁波。那天,我坐在驾驶室副座里,耷拉的双眼戴着太阳镜,望着窗外奔跑的车辆和飞扬的尘土,心里空落落的。
表弟也老了,变得啰唆起来,一遍遍地问我,老姐,你哪来那么多书?这些书你都要吗?你还看得清吗?要那么多书干嘛,该丢的就丢了吧?老姐,我只做了一个书柜,这么多书哪里放得下啊!
你不懂!这些书,我需要它们陪着我。
表弟叫来几个年轻人,他们帮我把十几个大箱子从车上搬到了屋里。我对表弟说,你们走吧,我自己一个人慢慢理。
表弟非要帮我把东西整理好,他说,老姐,你行吗?
我行啊,你带他们去饭店炒几个菜,点好一些,我请客!我边说边将他们支出了房门。
我很喜欢这间屋子,终于可以过一段属于一个人的没人打扰的时光了。
我把那台旧得不成样的老唱机先拿了出来。这老家伙,陪了我大半生了。它老了,我也老了。
我找出一张黑胶唱片,马勒的《大地之歌》便回旋在半空,我想到好多好多年前我曾经写过的一篇散文《大地无尽时》。那是我系列散文《无期独行》中的一篇。那年,我带着马勒的《大地之歌》来到西溪南,入住慰颜府。西溪南的这座老宅里收纳了《大地之歌》中所有的悲凉情境,音乐回应着我,赐予我力量以及无穷的想象。
我还听到了老柴的《悲怆三部曲》,那是他写给梅克夫人的音乐情书。那年我写了一篇音乐笔记《听闻远方有你》,用文字纪念这段永恒的爱情。我在文中写下:
苍茫大地,悲怆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存在着,从不曾间断。这种宗教式的精神之恋,只有这样高洁的灵魂,坚韧的心,才能持续十四年之久。不管后世之人,如何去评说这段柏拉图恋情,也不管这段恋情,最后还是没有逃脱曲终人散的境遇,但至少在他们交往的十四年中,被彼此真诚地需要过。无论是经济上的支撑还是灵魂上的相依,都是一种忠诚的互补。至少,他们完成了最初的承诺,这段感情终究没有被桎梏,被污染。
当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奏鸣曲《雨之歌》飘进我耳朵时,我已经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窗外的几声鸟鸣,以及从窗外飘进来的风声和花香将我唤醒。我想起那年自己写下的另一篇音乐笔记《绝弦》,那是献给音乐家勃拉姆斯和他爱了一生的女子克拉拉的。这篇文当年有幸被“蓝素电台”的主播萧秋水老师朗读,这些年我一直在听。特别是这一段,萧秋水老师的声音太有磁性了:
一百多年后,关于勃拉姆斯和克拉拉的往事早已湮没于尘土中——这个世界里再也不会发生那样的爱情——绝口不提“我爱你”,却爱得无比深沉。
我所相信的,一如勃拉姆斯与克拉拉的,那些从来没有被说出来的爱情。
法国诗人阿尔蒂尔·兰波写过一首诗,是对勃拉姆斯所坚守四十三年爱情最完好的诠释:我将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动;无边的爱却自灵魂深处泛滥。
古典音乐多多少少是带着点傲慢的,听久了,自然也会沾染上古典的气质,我一直所怀念的音乐和爱情其实都是一样的,那是一种灵魂之间的飞翔,以古典的方式深爱着彼此,有着旧式的素朴优雅,永远是初始的模样。
如果愿意去怀念,最好的办法便是如我这般纵身跃入勃拉姆斯的音乐中,不要说话,像恋人一样互相倾听。
……
我又在听了,虽然听力越来越差,但我还是甘愿眩晕在这美好的世界里。文学和音乐一直牵引着我,慢慢地走完生命的最后时光。
下午阳光好极了。我的屋子外面,是一大片的菜园,绿茵茵的,看着很舒服。
还有一大块平整的水泥地,这是表弟找人帮我铺的。那里,正好可以用来晒晒我的那些书。我找出一条旧床单在地上铺平,将书一本本放在上面,到日落之前再收起,这样跑来跑去折腾了一下午,就没力气再把这些宝贝们放到书柜上了。
表弟夫妇俩来了,为我送来晚上吃的饭食。我胃不好,前几年还做了两次手术,到了这一年只能吃些流质,表弟送来了小米粥,我喝了一小碗。随后,他帮我把书放到书柜里。
这个叫傅菲的作家,太能写,怎么写了那么多?表弟拿起一叠书问我,他看到这本署名傅菲,那本也署名傅菲,有些惊奇。
傅菲可是散文大家,他出版的所有的书我都有,我是他的铁粉呢。想当年,他还是我们流年社团的特邀作家、文学顾问,我费了好大劲才把他请来流年。你看,这些书大部分都有他的签名……我接过表弟递过来的书,数了数,一共二十一本:诗集《在黑夜中熬尽一生》。散文集《星空肖像》《生活简史》《屋顶上的河流》《南方的忧郁》《饥饿的身体》《大地理想》《草木,古老的民谣》《故物永生》《木与刀》《我们忧伤的身体》《河边生炊烟》《关关四野》《森林归途》《深山已晚》《瓶子里的鱼》《灵兽之语》《元灯长歌》《山河故人来》《风过溪野》《鸟的盟约》……
这位叫“吴昕孺”也厉害啊!表弟从一个纸箱里翻出来吴昕孺的书,说道。
他是全才,诗歌小说散文样样拿得出手,他也是我们社团的特邀作家,是我找来的。当初,我为了能联系上他,特地去天涯社区注册了一个博客……你老姐,厉害吧!
表弟点点头。把书递给了我。《原野》《天堂纳税人》《文坛边上》《他从不模仿自己的孤独》《牛本记》《旋转的陀螺》《心的深处有个宇宙》《君不见——李白写给杜甫的十二封信》,这八本书,我把它们放在了最外侧的书架上,可以随时拿出来阅读。
除了这些,还有那些年文友相赠的书,一些我自己重读的经典文学作品,如木心先生的书,迟子建的书,李修文的书……还有我们流年社团编辑们出版的书,一朵怜幽的小说集《荒城》,江凤鸣的散文集《烟雨里的粉墙黛瓦》,石语的散文集《地衣》等等,当然还有我自己的三本散文集《亲爱的旧时光》《暮春的潜台词》《时光书》。
表弟说,老姐,我还是喜欢你的书,看着亲切,读着舒心。我笑了。幸亏有他帮忙,才与我一起将这些书放进了书柜里。
后来的日子里,我经常坐在沙发上,拿着放大镜,看书上的那些文字,它们在我眼前不停地晃呀晃,仿佛又将我牵回到很多很多年前的岁月里。那时的江山,那时的流年,还有在一起读书写字的伙伴们。
三
二〇四二年,我七十岁。
身体出了新的状况,膝盖做了一次手术之后,经过了漫长的康复期,下地行走变得极为艰难。这一年原来预想的计划——出门拜访流年的兄弟姐妹,只好搁浅,这一生再见面,怕是难了。
我想到自己江山文集里的系列散文“时光书”。那是那些年友情的印证,我一直有个心愿,要将他们印在纸上,打印成册,赠予那些被我写进《时光书》的友人们,作为永久的纪念。
“时光书”系列散文一共收录五十六篇,分成三个小辑:《人间惊鸿客》《江上晚吟风》《杏花弦外雨》。
第一辑《人间惊鸿客》收录了十七篇散文共计七万八千字:“灯影后、春庭雪、她依旧、惜君如常、安如磐石、时间都知道、念起,心欢喜、温柔的独语、暮春的潜台词、唯有深情最动人、十年踪迹十年心、唇齿之间的痕迹、相逢处有千言万语、每个少年都前途无量、是你,温暖了我的时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流云,飞渡时间之河的思念。”
第二辑《江上晚吟风》收录了十七篇散文共计八万字:“雪的断章、隐约江南、秋声四起、心灵的秘境、静静的白桦林、通往原色的幽径、相思千年说红豆、杜鹃花开深似海、朵朵村的时间画布、携一缕诗韵过江南、乡愁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写你,那一瓣静静的雪、能团圆,才是最好的中秋、探寻荒山中的那一次惊魂、小巷,一帧简约的心灵底片、原来,苦也可以开成一朵花、江南深处,那些明晃晃的美丽。”
第三辑《杏花弦外雨》收录了二十篇散文共计六万字:“花境、从前、音尘绝、茶禅书、萌芽记、岁月缝花、好人千古、孤独路538号、春天不曾远去、雪落下的声音、一米之外的风景、此去经年泣露寒、春天远去,你也远去、意境为师,安澜如诗、母体的村庄、岛上嘉木录、粥,凡尘之外的味道、你的离去如此猝然、若惦念,请来旧时光里寻我、一切皆因你开始,因爱永恒。”
那天,收到印务公司送来的书册,封面装帧精美,虽然没有书号未经出版社常规出版,但依然是我最喜爱的。
时光书,有江山时光的纹理,有流年文脉的印记,厚厚的,像一块砖石,置于掌心,我能感受到它的厚重。
这本书册里收录的五十四篇文章,能映现我在江山那些年投入的爱与深情。书写,是一场漫长的抵达,我用了半生的心思,几经修改才完成这册《时光书》。
只是,《时光书》里的有些友人早已不在人世了。
《时光书》无处可寄。
比如我的恩师花木早(林华章)。
他一个人独自走完了七十八年的人生,于二〇一二年五月告别人间。他活着的时候,支撑着病躯,为了支持我的社团,重新整理修改文稿,然后一篇一篇地投到流年。当我向他流露出想学习古典诗词时,他从武汉的书店里为我淘来诗词格律方面的书籍,连同他的《词林菁华》手写稿一起寄给我,耐心地为我讲解,为我修改不成样的诗词……
其实,林老师的学生遍及天下,在文学、音乐等领域都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可就是这样一个谦逊的老人,在心爱的文学面前,甘愿卸下所有的傲气,用自己有限的时间,扶持像我这样的文学后辈。
这册《时光书》里,收录的散文《孤独路538号》是我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年秋天写下的。那时,他的八弟林幼章先生委托我整理编著两部书稿,林老师的长篇小说《孽海冤家》,诗词作品集《月照水流光》。我与他别后多年,在纸上再度相逢。在编书的过程中,我发现竟然找不出一个词语精准妥当地形容他的一生。
我用了七天时间,完成了这篇散文,因要作为代序,刊印在老师新书《月照水流光》里,所以反复修改,但改完自己还是觉得不太满意,在编辑群说了一下,这篇散文的编辑“策马南山”看了,在文后写了一大段评:
“飞雪的《孤独路538号》读完之后,我们也能看到作者用文字表达的心情和情绪,这里有今人和古人的孤独、恩师和木心先生的孤独、作者和孤独者的互为孤独、作者本人的孤独、读者读完之后发现自己的孤独,还有书中提到的人物生平经历的事情,使用过的物品,居住过的环境,都在孤独。——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飞雪的此文是很不错的,已营造出了独特的孤独气息,不必再担心自己没写好。飞雪之所以感到没有写好孤独的隐喻,是她太想把自己的心思让所有的人都明白了,这是不可能的,一千个人心里都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回复道:我还是不够自信。写完一篇文,就像在黑夜里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总也走不到尽头。这篇文中关于“孤独路”的意味,以及那些我内心想要表达的却不愿意用文字直白地表达出来的,南山你都读懂了。真正的孤独者是从来不言说孤独的,只是享受,而生活从来不会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进行,但终究会给我们一段时间,去孤独去仰望。我那故去的老师便是如此,木心先生也是如此,他们用孤独抵制孤独,认认真真地活了一辈子,认认真真地苦了一辈子。就像张爱玲,以孤傲冷艳的姿态,笑看尘世。孤独其实就是一座岛屿,我们的一生到了最后,终究是要走上那片岛屿,告别尘世,与孤独签订一个协议。
比如曾任流年诗歌主编的“银杏树”大哥。
我们亲切地叫他“树哥”。他在时,几乎包揽了流年所有的诗歌。二〇一五年五月的一天,他悄无声息地走了。没有与我们告别,他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是:“各位大编们,俺眼睛提出强烈抗议了,看什么都是双影。后台有诗稿拜托了。”远方的红梅带来他去世的消息,流年编辑群哀鸿一片,没有人相信,那棵守护着江山和流年的银杏树,还那么年轻就急匆匆地走了。
这文字第一眼就爱上了,因为有似曾相识之感。开篇第一句我就读出了《百年孤独》的味道;读到“它老了,我也变老了”,我又想起了《额尔古纳河右岸》里的那句:“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看老了”;读回到故乡时,屋里简单的陈设,让我想起了曾经在异国他乡的张爱玲……这篇文字,里面包含的东西太多了,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能说清的,只有感动。
这篇文在我手里写按,真有点明珠暗投的感觉。雪妞妞凑合看吧。


我想说的是,生命的文学,文学的生命,都将永垂不朽。
提前祝贺雪社又一篇“好声音·征文”精品诞生。
辛苦。辛苦。敬茶。
灵魂对晤、以心悟心,逝水的时光变得更丰盈和饱满。
善待别人的文字,用心品读,认真品评,是品格和品位的彰显!
我们用真诚和温暖编织起快乐舒心、优雅美丽的流年!
恭喜,您的美文由逝水流年文学社团精华典藏!
感谢赐稿流年,期待再次来稿,顺祝创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