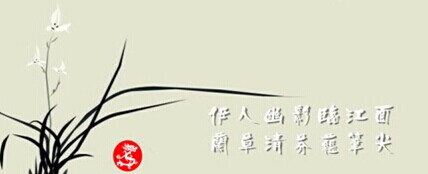【文璞】又见上海(散文)
【文璞】又见上海(散文)
![]() 一
一
在高铁速度的时代,我对慢时光的绿皮火车依然情有独钟。经济实惠是一方面,更喜欢一觉醒来的惊喜,尽管这份惊喜完全在预期之中,然半梦半醒之间,终点站倏忽而至,场景的陡然切换,还是不由得一声欢呼。
十一月二十日,一觉醒来,皖北小城的我已置身国际都市上海。
七点钟出地铁站,千里之外的上海居然也是阴天欲雨,连灰暗的程度都和小城一模一样。看天气预报,两地高温差不多,但上海低温比我们高四度。我一身加绒卫衣卫裤,外面套一件黑色羽绒马甲,从家里穿到上海,原以为马甲只是备用,如今看来穿上也不多余。
老公的战友老团长驾车接我们去吃早餐。我点粥,竟然没有,原以为粥在南方更为普遍。我只好重新点了碗馄饨,又嘱咐店家用白水煮颗荷包蛋。
饭后去看望老公的另一个战友,某公司董事长。他一眼瞧见我的满头银发,问我染的吗?我摇头,自然白发,退休后不想花精力染了。他说这样好看,并让我看他的白发,他也不想染,但是没办法,公务在身,精神面貌不容忽视。
六年前,老公的上海战友们到过我家,董事长个高,斯文帅气;团长中等身材,肩宽威武,忠厚沉稳。如今再见变化不大,只是董事长看起来略有倦意。
董事长和我提及他的两个小孙女,眉眼含笑,满满的幸福感。他拿着手机,一个接一个刷视频我看,进行细节补充讲解。这些视频他应该看过无数遍,平时工作忙,视频化解了思念,也是他陪伴孙女成长的一种方式。
我理解董事长的心情,我们都是这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对后代疼爱之余更添了稀罕的附加值。
怕影响董事长工作,我们暂别而去。临行董事长特意为我们安排好住宿,离我们就诊医院很近的大饭店套房。不管都市还是小城,“战友情”都是一样的刻骨铭心,感人肺腑。
二
团长下午两点在浦东有个会议,开车带我们去附近一游。
团长一路讲解,我隔着车窗目不暇接。突然,路前方出现一个斜倒的不锈钢雕塑,有几分雷达状。不知是不是我坐在小汽车里的缘故,感觉雕塑巨大无比。看外观,雕塑科技感满满,目光触及有穿越未来的错觉。只是这种科技感带给观者的不是人类雄霸宇宙的豪迈。相反,塑像头重脚轻,颇有轰然倒塌之势,让观者忽生人类科技泰极生否的凄然。透过不锈钢交错的缝隙,上海灰蒙的天空,宛若智能机器战胜人类的科幻画面。
我不喜欢这座雕塑,我说。团长说雕塑名曰《日晷》,2000年为迎接新世纪而建。不可否认,设计别具匠心,寓意巧妙,只是仍觉造型与周遭有些格格不入。
远望上海的建筑也低于预期,小城也有高层,尽管数量不多,也算有所见识。
汽车即将驶入越江隧道,团长喊我看。受位置角度影响看不到头顶涌动的黄浦江,却足以让我兴奋。团长喊我再看,我眼前一亮,瞬间变成上海的小迷妹,欢呼雀跃。
上海中心大厦、环球金融中心、金茂大厦直插云霄,造型别致,灰蓝色的玻璃幕墙熠熠生辉。我喜欢至极,上网检索了解,不觉莞尔。网友戏称三厦:“开瓶器”、“注射器”和“打蛋器”配成一组“厨房三件套”。确有几分形象,便于分辨记忆,却不传神。三楼组合实则高端大气,三分凝重七分现代,尽显国际都市建筑风范。
团长指着远方另一楼群,隔着车窗玻璃也深感年代久远。团长说确实是古建筑——万国建筑群。我还是喜欢现代建筑,爱极了上海中心“三件套”。仅仅是隔窗一瞥,恍若置身未来都市。“三件套”强势拉开与普通建筑的距离,却没有发展得太超前,刚好在我向往的审美范畴。
中午时分,车停。我的双足终于触碰到浦东大地,抬起头,心心念念的上海中心“三件套”近在眼前,每一个角度都有不同的惊喜,每一个抓拍都是城市建筑的巅峰之作,令人赞叹,难以忘怀。
踏上花团锦簇的方砖铺路,我们隔着黄浦江,于浦东看浦西,外滩风光无限。只是近观东方明珠倒没了想象中的激动,想是一路牵挂太久,过早地消耗了热情。
三
午餐自然少不了生煎。凡以老上海为背景的影视剧,纵使人设不同,剧情有别,然生煎必能贯穿始终,似乎不如此突出,便不足以证明影片纯真的地方血统。
我以前是吃过生煎的,只是没有很特别的印象。午饭还想吃粥,好容易看见赤豆小圆子,喜不自禁。团长好奇我怎么顿顿吃粥呢?我说在家并非如此,出门就莫名的体燥口干,吃咸油的东西感觉肌肉都在快速紧缩,不喝口稀饭,整个人都会变成一条咸鱼干啦。团长笑而不语。其实我觉得他口味也完全不像上海人,竟然顿顿吃面条。我外婆一家都是江苏人,比上海靠北多了,都不会擀面条蒸馒头,记忆中家里就没怎么吃过面。
先喝上几口粥,肠胃滋润了方有心情顾及其他。生煎若非点缀着几粒黑芝麻,外观和我们县城的小笼包大差不差。我夹起一只一咬,汤汁四溅,生煎居然内包有汤,我全然忘记。更重要的是生煎如此美味,以至怀疑我以前究竟有没有吃过生煎!吮完汤汁,我开始品尝焦黄的生煎收口捏折,一口酥脆,齿颊生香。老公和团长照旧吃面,外加一盘三黄鸡、一盘肉酿面筋。
我埋头生煎,无视其他。吃完心满意足地擦拭嘴角油亮亮的芝麻粒,两人让我再吃些菜。我连连摇头,说我一大碗粥,六、七只生煎,很饱了。团长一乐,纠正是十只!总共十二只,他吃了两只,余下的被我全包了。
十只!我完全没有想到。有谁会在美味面前考虑数量呢?艺术源于生活,岂止是老上海影视剧离不开生煎,它也是我人生剧本有关上海不可忽略的内容。每每轻咬一口,香气缭绕,现实与影视里的旧时光碰撞交错,恍惚自己就是那个身着旗袍,于悠长的巷内袅娜而至的上海女子呢。
四
午饭后团长去开会,让我们随便走走,会后来接我们晚餐。
环顾四周,全然陌生,我知道自己从来不是上海人。一九九零年冬,我曾与老公来上海买结婚用品。一晃33年过去了,犹记南京路。那时候小城商品也日渐丰富,但上海依然是外乡人向往的购物天堂,只要条件允许,必然会大包小包前来上海采购。
老公的战友,当时上海消防队队长看到我的第一句话便是:你不像小地方来的人,看起来和我们上海姑娘没什么区别。我浅浅一笑,内心激动无比,这句话无疑是上海人对我这个外乡人的最高褒奖。
在此之前,也有上海人给我打过评语。一九七六年,我八岁的时候,和姐姐被江苏外婆家的一位朋友叔叔带去上海。我幼年顽皮,也不讲究卫生。叔叔的父母和妹妹(我们喊她阿姨)都在家中,因而拥挤。晚饭后,阿姨让我们姐俩爬木梯上阁楼睡觉,随后便撤去了梯子,不想我习惯性吐了口口水,自觉落在地板上不妥,却没梯子下去擦拭。正着急,阿姨听见声音走过来,边擦边叽里咕噜说着上海话,我听不懂,揣摩语气知道是在责备我,大气不敢出,缩在被窝里安分了好半天,后来又无意识吐了一口。这下阿姨气坏了,直接用普通话训斥我,说我这样的乡下孩子就不配住上海,没规矩,又蠢又笨!
如今早已想不起叔叔一家人的模样,但这些话依然记得。其实我的父母并非乡下人,但在她眼里,或许唯有上海人才称得上真正的城市人吧。
这些从六、七十年代上海下放到我们县城的知青身上也可见一斑。虽寄人篱下,但腰杆挺得比谁都直,和当地人交流时不时冒出几句上海话,十足的优越感。九零年我到上海,周遭上海话此起彼伏,感觉不是必须使用普通话沟通,上海人能少用一句则少用一句。方言对其他地方人就是家乡话,对上海人而言可能多了一种身份的象征。
五
前方世博会红色中国国家馆赫然入目,梁柱交错,古建筑与现代艺术高度融合,古朴典雅。形状若古代王者之冠,寓意“东方之冠,鼎盛中华”。正门石阶巨大的团花铺设散发着宫殿的华贵与精美。
踏上馆侧自动扶梯,馆内光线幽暗,在特设灯光的照射下,四壁的画作尤为醒目。或两三一组,或整墙巨幅。每一幅都代表了一个特定时期,无声地讲述着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与文化。
走出中国馆,竟不知该往哪里去了。九零年到上海,我和老公基本没有离开过南京路,整天逛商场购物。老公的队长见我大包小包竟然没有买小城人手一件的缎子棉袄,深感意外。我也是嫌弃缎子棉衣土气,看都没看一眼。结果正月十六结婚前夕,又满大街急购一件,光毛衣外加毛呢外套根本挡不住小城的寒冬。可见土气有时候和审美无关,更多的是环境使然。
三十年后的我,再没有上海购物的愿望。网购抹去了地域界限,购物快捷实惠,款式空前多样化。今天的我也不会觉得缎子棉袄土,以前选择少,大家都穿,未免俗气。其实任何衣服都是因人而异,没有绝对的美丑之分。
我不爱旅游,走走就累。和老公进“星巴克”点咖啡,慢悠悠地喝了半天,想去卫生间。“星巴克”没有,指点我们出门前行进商场。商场很大,底层是儿童游乐场,只可惜空无一人。进卫生间,厕纸、烘干器一应俱全。坐便器、洗手台一尘不染,光可鉴人让我心生感动,有上楼购物的冲动。可家里网购的服装尚未拆封,另外我们小城实体店的衣服已价格不菲,大上海寸土寸金,让习惯了网购低消费的我望而却步。正犹豫不决,一眼瞥见电子墙上字幕介绍一楼“星巴克”,方知之前去的“星巴克”归属商场,略感欣慰,不管多少也算有过消费有过贡献。
再次回望冷清清的商场,三十年前在南京路疯狂购物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上海商场竟会冷落至此!
六
下午四点,团长会后接我们去外滩。天色阴沉,团长很遗憾我们未能一睹阳光下的外滩。我却觉得我们在最好的时段遇见最美的外滩。
灰色的外滩犹如绝美的画卷!黄浦江浓灰深沉,天空浅灰空灵。高耸入云的“厨房三件套”与并肩而立的建筑群尽显灰色魔力,同色系中每一个建筑的灰色元素都是那么卓然不群,灰中透蓝,蓝色的适当添加让整个建筑群极具层次感。楼层中少量灯火次第亮起,增加了建筑群的透明度与神秘感。“厨房三件套”前方金属黄、深潭绿、翠鸟蓝等几栋楼给灰色的基调增加了一抹生动。东方明珠犹如塔身串珠,灰暗的天幕下,银灰银红双主打色妆扮的东方明珠越发低调奢华,独立于鳞次栉比的建筑群分外耀眼。
团长说外滩灯光秀要天黑以后,我们先去欣赏万国建筑群。之前曾乘车一瞥而过,感觉远不如上海现代大厦震撼。走近方知判断错误,万国建筑群的每一栋楼都独具一格,异域风情裹夹着久远的岁月风尘,一眼便是一世。我后悔没有早些过来,天空彻底暗了下来,万国建筑群灯光璀璨,金碧辉煌,宛如黄金打造。至此始懂,众人喜欢探古寻幽,多是被其所蕴藏的历史气息吸引,哪怕并不了解,光看外表就有很强的冲击力与代入感。
团长之妻单位离此不远,下班后与我们相会。我和团长同岁,她比我年幼,我称之弟妹。团长让我以后直接喊他名字,毕竟现已转业。我点头,其实我更愿意称他团长,喊一声,秒回儿时的军营生活。
弟妹出现在人群之中,偏瘦体质,五官端正,为人坦率真诚,很多观点和我一致。我俩越谈越投机。进饭店入坐,我尝了尝鳝丝觉得对于我们北方人甜了些,不想弟妹这个上海人也觉得偏甜。其实岂止是饮食,环顾四周,从服饰举止也很区分上海人和外乡客,城镇化的高速发展,网络的全面覆盖,城乡边界日趋模糊。
然城乡消费还是有显著区别的。那盘红烧肉油而不腻,香入骨髓,只是块小量少过于玲珑了。团长纠正不是红烧肉,是叉烧。啃完猪蹄鲍鱼,我开始吃清炒上海青菜帮,尽管团长解释不是上海青,可我总是记不住菜名,看形状就算不是上海青,那也是其他青菜的菜帮子。儿时的我只吃菜叶不吃帮,没想到上海这菜帮子也不舍得多给两片。一道青翠的豌豆苗吸引了我的目光,那么大的白色圆盘,只盘心一小把豌豆苗。对比强烈,让我不由得好奇价格。88元,团长答复。
这么贵!我惊道,难怪要用那么大的盘子装,漏掉一支可不得了。老公说这里的菜都贵,荤菜一盘200左右,青菜一盘近百元。
我小心翼翼,看着精致的菜品不舍得动筷,还好我的粥及时赶到,服务员端至面前,我“噗嗤”一乐。这也叫碗,根本就是一蘸料碟,放两只饺子都挤。
弟妹说这家地段好生意兴隆,所以贵,其他地段价格就便宜些。
我端起粥,一口一粒米,不再问价,怕拂了团长夫妇美意。菜确实够贵,但团长夫妇之谊也够暖,暖到我想立刻将他们带回我家,遍尝小城经济实惠的美味小吃。
七
二十一日,我们去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老公做鼻息肉手术,依预约完成术前各个手续。我这段时间感冒,好了多年的鼻炎突然复发,也临时在上海耳鼻喉专科医院,挂了个普通号。
我满头白发,一般人会以为刻意漂染,只有白发资深人士才能够一眼看穿。维持秩序的老妇人看到我惊道,你这是多大了?我说56岁,头发白早了。
团长说这三样上海都有,比我们小城多了生煎。
我们小城的锅贴我不爱吃,因为不爱吃焦底,嫌累牙。生煎的焦顶酥脆到了极致,加上鲜香的内馅,怎么吃都不够。是我吃过的面包馅食品里最美味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