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风】我的舅妈是姑姑(小说)
【西风】我的舅妈是姑姑(小说)
![]() 一
一
我很不喜欢面对二舅妈。不是她不好。相反,她是我三个舅妈中对我最热情最实在最无私的。在物资极其馈乏的年代,过年走舅舅家,只有她打开那个终年上锁的柜子把一撮红糖捏到我的手心里,看我填进嘴里;见我进门就麻利地把家里准备好的吃食端过来,硬往我手里塞。
“吃,多吃些。”她说话的声音有些哆嗦,面容慈祥而亲切。有些感动,又有些接受不了。她咋跟妈妈说得完全不一样呢。“舅、姑妈。”被她热切地牵住手往门里拉的时候,我嗫嚅着轻叫了个古怪的称呼。对了,这就是我怕见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我见了她不知道是喊舅妈呢,还是喊姑妈。父亲要同行,他就会说,去看看你姑妈。看着见到我激动起来的二舅妈,我也有些激动。我的激动是从知道她是爷爷的女儿,父亲的亲妹妹开始的。不知道的时候我不会激动,见着她的激动还有些不知所措。不过现在我知道的东西多了,我知道她激动的成分中,有好大一部分是把我看作至亲侄儿,而不是随便一个亲戚家的孩子。
“在大舅家吃过了,大舅妈的炕包子还等着呢。”我嘴上推辞,手却诚实地伸过来,把平时吃不到的东西捧到手里。我实话实说,从大舅家出来的时候,母亲是叫我去去就来的。
母亲打发我看二舅,没说让我看二舅妈。我还没见二舅呢。
“二舅呢?”我站在被西北风吹得树枝乱喊的小院天棚下四下张望。三个小表弟从厨房门上的厚门帘边伸出脑袋,目光锐利地盯着我手里捧着的东西,馋涎欲滴的样子,好像他妈做的好吃的他们从没尝过一样。
“他,他去喂羊去了。”姑妈淡淡地说,表情有些凝滞。她一定知道我母亲怎样嘱咐过我,也知道我来他们家就是走个过场。年是别人的,永远不是姑妈的。
“那我去看看羊。”没等她答应,我已经跑出门外,找放羊的二舅去了。麻花油饼吃不下不当紧,装兜里吧。我的棉衣口袋就是个百宝箱,啥都能往里装。当然,装得最多的还是各种吃的东西。干馒头,沙枣最多,平时不会有沾油的东西,只有过年才有这种可能,所以根本不知道会油了衣服。
以我当时的智力,还无法感知姑妈看我一溜烟跑出去后会是什么感受。我根本不去想,随我而走的那双眼里包含的是渴望还是失望,或者还有酸泪欲滴的委屈。
跑出去好远我才想起来,见了二舅妈,我好像没正经叫一声姑妈。这不怪我,我实在不好选择喊啥好。幸好,经常是我还没喊她的时候,她已经“长生、长生,我的娃来了。”地喊我了。
二
母亲总是跟我们几个刚懂事的儿女说:“二舅是叫你二舅妈勾引到手的。”我那时对她的话没有丝毫怀疑。二舅年轻时穿着军装的相片要多帅有多帅。不过父亲的话又让我怀疑母亲话里的真实性。父亲说,别听你妈胡说八道,她就是见不得你姑妈呢。父亲的话也有几分理由,好歹姑姑是当年的师范生,刚解放时,乡下连个中学生都很稀罕,师范生是个什么名望可想而知,难道不是舅舅来勾引了姑妈?或者,无关勾引,相互对眼呢。从那以后,我对母亲就有了一些想法,对她的教导也多存疑。
比如她说,爷爷吃得太多,伺候不起。爷爷都七十岁了,能吃多少?再说,他吃的也是他儿子我父亲挣下的,为什么不做了饭敞开让他吃饱呢?弄得爷爷扶着拐杖爬到大伯家门口的渠沿上喊大妈:“梁玉香,你给我弄些吃的,我饿得受不了。”大妈碍于母亲的面子,不敢公开给爷爷送吃的,只能做了馒头锅盔让大伯悄悄送给爷爷,爷爷牙齿松动咬不动硬东西,只能把干馒头和硬锅盔掰碎了放嘴里“唆”,靠牙床的力量把被唾液浸软的食物吞下去,实在咽不下去的都像羊粪蛋儿一样扔在炕沿下。
难得母亲这个脾气怪异的人对大伯一家格外亲切。她知道大伯大妈给爷爷送吃的也不会说啥。要是遇见姑姑揣着东西往爷爷奶奶屋里去,指定指桑骂槐地来一顿。弄得姑姑每次回来看爹妈都像个小偷一样。经常是晚上趁夜色趟沙河把吃的从爷爷奶奶住的后窗户递进来,悄悄说几句话,头巾捂着脸拐上小路返回。奶奶在世时爷爷干脆跟我们分开吃。一个小院,爷爷奶奶占了堂屋和右边角那个库房,两个姐姐和我占南厢房,母亲自己住北厢房,西南角的厨房里是母亲做饭的锅灶。朝东的大门靠近北厢房,只要有人进来,妈妈第一个从窗户缝里便可看见。这也是她足不出户非得占着这间房子的原因。
三
父亲姊妹六个,四个姐姐嫁得远,二舅妈这个唯一妹妹嫁到了隔沙河而望的姜家庄。父亲新中国成立前读过几年私塾,土改时被工作队看中,跟着分田分地跑了些日子,就成了国家干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已经成长为公社书记。他身上长满当年干部的所有特征:勤劳,肯干,带头,无私。每次浇水,他都全程跟踪督促,一把亮闪闪的铁锹,一件蓝色棉大衣,一架有些老旧的自行车是他的标准行头,直到全社十三个大队的一轮水浇完,才回到公社宿舍睡个囫囵觉。他有星期天,一月总能回家一趟。星期六下午下班骑自行车回家基本都在天黑以后。工作忙起来几个月不回家是常有的事。我读初中暑假跟他去公社待过一个星期。去了就不见人,每天到公社食堂吃完饭我就跑出去乱溜达,直到星期六下午才见到他的人影。他说去乡下组织收麦。看他一脸焦黑,浑身汗味儿。坐在他骑的自行车上,叮叮当当地往家走。太阳快下山前看见了沙河。刚要过去,他又掉头:“去你小姑妈家看看。”
到姑妈家,把已经沉睡的人敲起来。父亲进门把姑妈叫到一边悄悄嘀咕,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东西递过去,姑妈还在推让,父亲已经出门。我跟在父亲推着的车子后边,沉默半天他叹息一声说:“你也知道,你这个小姑妈命运不好,师范毕业没赶上好时候,成了个农民,养了三个娃子。你看她瘦弱的样子,起早贪黑下地劳作,日子过得太凄惶了。刚给了她几块钱,别跟你妈说。你妈见不得她呢!”
“嗯,我知道。”我说。哪能不懂这事呢,见了那么多,听了那么多,早知道啥该说啥不该说。
四
父亲长期不在家,爷爷平时有事找的都是大伯。大伯是三爷的儿子。爷爷辈里爷爷是老大,父亲在他们这辈里排行老二。大伯身材高大,面容英俊,豪爽正直,文革前当过会计、大队长,现在又被公社干部做工作当了队长。母亲这个农民,基本没下过地,没割过几亩麦子。生产队劳动中,最多去干个轻来薄去的小活。哪像大妈婶婶,一人一天割一亩多地的麦子。母亲的理由是有病。有病也不去医院,没人知道她到底有没有病,得的什么病,只听她整天躺在炕上唉哟哎哟地叫。大门一响,她眼睛往外斜着从窗缝里看着来人,哎哟声便顿时升高。
家里非干不可的那些活,爷爷就去喊大伯。有关我们的一些事情,需要马上办的,母亲也打发我们去找大伯。或许,这也是母亲这个人虽然对好多人都不正眼瞧,却对大妈一家人偏爱的原因吧。包括大伯家的堂哥堂妹,跑来跟我们耍的时候,母亲都会给些吃的,有时候还悄悄塞几毛钱让他们装好买糖吃。这是让我很嫉妒的。因为这种待遇我都不常享受。
关于姑妈常到大伯家的事情,是我无意中发现的。这个发现我装在肚子里从没跟别人说过,母亲临终都不知道。我怕母亲知道了这个秘密,会不会对大伯大妈生出嫌隙。我最不希望连我崇敬的大伯大妈也跟母亲起了矛盾,那样子我母亲在村子里就再也没了信任的人,我们咋还能去叫大伯大妈帮爷爷干活、帮母亲办事?
那天我在沙河里玩水,看见大伯大妈陪姑妈来到河边。姑妈提的篮子里装着些菜,还有看不清的东西。远远看见我,她喊“长生,过来,给。”从篮子里拿出一根黄瓜递给我。我拍拍手上的沙土,接过来往咯吱窝下一撸,狠劲咬下一口。大伯笑说:“你咋没去放羊,一天六分工呢。”我说明天要到学校,今天好好玩一玩。姑妈说:“小心些,别把衣服弄湿弄脏了,你妈身体不好洗不了。”我说:“你到大伯家干啥去了。”大妈笑着说:“看她的大哥啊。”说完他们都笑了。我也跟着傻笑几声,心里有些酸涩。姑妈不看她的亲哥嫂,专程看她的堂兄,唉,也对。亲哥看不到,她也得有个娘家可以光明正大地走,有个诉说心事的大哥大嫂可以依靠。
这时候,爷爷奶奶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五
那年冬天,当二舅被大表弟一钢钎桶死。小姑妈的天就塌了。她左借右挪,不顾妈妈对她的嫌弃,专程跑到亲哥哥面前,让他找找人,看能不能给大儿子办成个精神异常。那时候我们全家都已进城,父亲早就从机械修理厂厂长位上退休。一个一辈子不知道拉关系走门路的退休干部能有什么办法?这件事,最终还是落到我的身上。我虽然是个中学老师,却在社会上混得风生水起。而父亲这辈人,早被历史卷进了故纸堆里。他们当年的那些优秀品质,多数成了死板不通人情的代名词。他当了一辈子科级干部,从公社到县局,关系没维持下,人情没落下,让他找人办私事,更是比登天还难!我找了几个学生家长,把姑妈送来的几万元合理使用一番,事情成了。虽然是杀人,儿子弑父,但没什么民愤,相对好办多了。那些年,找人疏通关系办理比这更严重案件的多的是,只要钱到位,啥事不能为呢!
再说,我也不忍再看姑妈像个祥林嫂似的在各个衙门前卑躬屈膝的样子持续下去。还好,表弟被判了个死缓。送进去打点了几次,获得减刑,在我父亲去世后那年,回到了家里。等表弟回家的这些年里,姑妈的头发变白了,腰越来越佝偻了。
两个小表弟比较幸运地成家单过了,姑妈没了其他事情,一心缀在那个把她青春时期偶像打死的表弟身上。每年都要去监狱看几次,把到城里当保姆挣的钱花个差不多,才算舒坦一些。表弟出狱已经年过四十,开始说话还比较正常,过了一段就出现异常,说起话来胡拉乱扯变得神经,有的没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好似连他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意思。每每这样,姑妈就变得异常小心,生怕那句话刺激到他。她开始信佛,到城里请了尊观音菩萨,敬立于过去立祖宗的地方,每天上一炷香,念叨些经文,希冀能把表弟身上的魔咒解开,让他真正回归社会。
表弟是在回到家第二年开始感觉全身无力,然后,很快就没有然后了。虽然姑妈耗尽了所有精力,求医问药、找巫寻神,最终还是无法把这个一百多斤的中年汉子拯救回来。
白发姑妈送黑发儿子的时候,两眼通红,脸上却放着光彩。她惨淡微笑着对所有前去帮忙的子侄们说:“没办法,他非赶着去给他爹抬脚。他爹托梦了,让他早些去,阳间没他的什么事了。也罢,正好我也耗尽全力了。”她眼里一直汪着的泪终于滑出来,一串串地,在她已成沟壑的脸上开辟出一条新的小道。听着她惨然的笑声,看她不断线的泪珠,我的泪水也跟着涌出来。
母亲是当年冬天走了的。母亲进城后真的有病,是糖尿病。临终前一年多瘫在床上不能行动,我们姊妹兄弟几个轮流伺候过一阵,又让暂时没事的小妹照看了几个月。后来是小姑妈自告奋勇,来家里照顾。那时候的母亲已经成了没牙的老虎,再也不会伶牙俐齿地怼姑妈。或许也是老了,过去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都被操蛋的日子弄得七零八落。姑妈尽心照顾,母亲被动受恩。八十五岁的母亲走得很平静,不知道与姑妈和解的关系有多大,但一定有与生活和解的原因。我去看望小姑妈的时候她说:“我对得起所有跟我有关的人,包括你的母亲。伺候她几个月,我觉得浑身轻松了一截。”
听她把话说得这么有水平,我一下想起她家挂在墙上的那张师范毕业生的镜框来。
六
现在,我的舅舅们只剩下三舅,舅妈中只剩下了姑妈。三舅打小得到母亲宠爱,他的前半生基本是母亲扶持的,包括那个胖乎乎的三舅妈,也是母亲用一些手段,把村里赵家老大闹矛盾的老婆偷摸地联系给三舅的。这话说起来不好听,可事实又不能隐讳。赵家老大婚后几年不育,慢慢传出是老大不行,媳妇闹矛盾。母亲正为年过三十小弟的婚事着急,知道赵家事情后再也不闹病,争着下地劳动,慢慢把赵家老大媳妇接触上,拉回家,不断地给些小恩小惠,明白了她跟赵老大婚姻矛盾的七七八八。又把小舅指引给赵家老大还没离婚的媳妇,为赵家老大两口子离婚提供了更多催化剂。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我终于有了一个最受母亲喜欢的小舅妈。小舅还算是个很有感恩之心的人。对于父亲,对于我们,对于姑妈都很尊重。对于母亲偏爱,他看成是我们全家对他的照顾,这很正确。现在村子里都成了老人,他嫂子我姑妈的一些事情,他也会出面关照一下。侄儿们但有一些对二嫂不恭,他就出面教导。胖舅妈死得突然,他的儿女都不在身边。表弟表妹劝他去城里,被婉拒。说离不开。
老年姑妈的日子很安闲。马上八十了,她又回到了从前。供桌上那尊观音菩萨早已满面灰尘,面前的香炉里空空如也。她让我给她找书看:“看看书比啥都好。看看书,找人来打打牌,活动一下脑筋,你说这样的日子是不是太幸福了?”
年迈的姑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我在心里感慨万千。我说这样好。你保养好是我们大家的福分。她笑笑,不言语。现在他的日子很规律:早上起床吃一口饭,做完家务,帮小儿子把羊喂完,就带把小椅子坐在树下看起书来。午休起来跟三个“花钱雇来(赢了不要钱,输了一毛两毛地给人家)”的老太太打阵子扑克。晚饭后坐在门口看一会来往的车辆行人,回到小康房的大床上躺着看会儿电视,不知不觉睡过去。早晨醒来,电视里还播放着节目。
“做针线没准头了,眼睛看书还行。”看望她的时候免不了受一顿“来看看我这个老太婆我已经很幸福了,还带东西干啥”的教诲,然后说她读到哪本书,联想到了那些,今天的盛世生活如何美好。一身灰尘的小表弟从轻型货车驾驶室里跳下来递烟,我接着点上问了问他的生意收成,他微笑着说都好着呢,平时做点小买卖,赚个零花没问题。难的是大儿子,年龄不小了,媳妇不好找。
“城里房子早准备下了,就等人了。”姑妈笑着插话。
“那就等着他找吧。现在娃娃找媳妇,家长起的作用就是准备银两,其他也起不了作用。”我宽慰道。
“就是。那娃娃最大的问题是没学下文化。”姑妈叹息,目光掠过墙上的学历镜框看向远方。似乎是追忆什么,又像是寻索什么。家里有姑妈小时候的相片,那时的姑妈清纯得像带露珠的月季,跟眼前衰老矮弯的小老太太简直差距太大。
唉,岁月无情的刀啊,谁能躲得过它的雕琢刻蚀?想起舅舅姑妈姨姨爷爷大伯父母,这才发觉,活着才有说话的权利。曾经生活里叱咤风云的所谓强人,不过是被日月风化得更早的对象。而戴着老花镜捧着书本的姑妈,简直就是田野上的蒲公英,年年岁岁,都能开一茬绚丽,播一季未来。
2025年4月15日星期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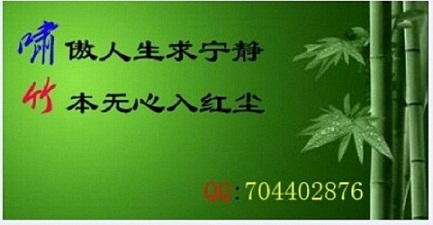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