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风】乡村的土路(散文)
【西风】乡村的土路(散文)
![]() 说到乡村,自然离不开土路。
说到乡村,自然离不开土路。
乡村土路到底有多古老?无从考究。反正爷爷的爷爷时,土路就已躺在那;乡村土路究竟有多漫长?无法丈量。只见它从遥远的山谷河川逶迤而来,又向陌生的村庄集市绵延而去。它们不是特为哪个人或哪群人所修,而是由一代又一代的乡人用带着泥斑的脚板一步步踩踏而成。它们纵横交错,宽窄不一,或坎坷或平坦,牵起一道道沟坡,挽着一片片田垄,抱着一个个村落。它们犹如人体里的血管,分布在冀中平原上,连接着每个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土路上,渲染着一个又一个孩子向往和梦想的烙印,闪耀着一代又一代乡人的诚朴、节俭、勤劳的美德,撒落着一滴又一滴乡人希冀幸福的血泪汗水。
其实,乡村土路是质朴的。老辈人爱说,路上道直,人不走。乡下土路,很少能看到哪条是笔直的。它们如欢乐的孩子那般扭动着腰肢,随意地绕来绕去,哪怕爬高坡、穿草滩也不刻意伸直。它们仿佛在玩捉迷藏,碰到庄稼绕过去,碰到树木绕过去,碰到水洼坟圈绕过去,碰到庙宇古迹也一样绕过去。它们绝不随意践踏哪怕是一棵树,一片菜地,一湾水塘……它们不象高速公路那般霸道,为了拉直,就不计代价地横冲直撞,劈山填塘,穿村破户!这土路的弯曲随意,既是乡村人对世间万物的感恩和敬畏,更是他们最朴素情怀的真实写照。
土路是乡村天然的画廊。乡村里最多的要数草和树了,而土路两旁便是这些草木集中的地方。高大挺拔的白杨,沧桑敦厚的老槐,婀娜妩媚的新柳……它们的枝叶在路的上空交织,夏天的时候,走在土路上,浓荫几乎笼罩了整个路面。阳光透过枝叶间的缝隙在路面洒下斑驳的影,光圈点点,空灵梦幻。时有清风徐来,会让你倍感身爽心怡。冬天的时候,树叶落尽,遒劲的虬枝张牙舞爪地向天挥舞,而树身则如威武的仪仗队般列队相迎乡人。走在土路上,像是被紧密地保护着。即便是寒冷的冬日,也会感到温暖妥帖。土路边的花花草草更不用说了!春天一来,她们便闹哄哄钻出地面,争相拔节开花,蒲公英,益母草,车前草,节节草,青青菜,马兰花……引得蜜蜂、蝴蝶“嘤嘤嗡嗡”闹个不停,真是一个“百草园”呢。秋天里,土路不再潮湿,变得更白了,路旁的野草黄了,野葡萄紫了,野枸杞也通红通红的了,春天的“百草园”转眼又成了“百果园”。偶有牛车慢悠悠地打路上经过,这美丽的乡村画廊就越发有声有色了。
乡村土路是孩子们的乐园。我小时候经常跟母亲下地。母亲在生产队的田里劳动,我便无聊地转悠在田头、路边,自娱自乐。节节草,一节节拔下来,再一节节接上去;掐上两朵马兰花,歪歪扭扭地插在辫梢上;用小木棍扒开路边的蚂蚁洞,把蚂蚁们赶出来,然后趴地上看它们乱哄哄地吵架;用小石子在路面上画狗、画猫、画我最初的“王国”。秋天来了,我美滋滋地发现,路边挤在草丛中的野葡萄熟了。正快乐地采摘着,一扭头,又发现野生枸杞条上挂满亮晶晶熟透的果儿。探着身子拽过枝条,才摘不了几个果子,还没往嘴里放,忽又发现肥胖的蚂蚱展着大翅“扑棱棱”飞到了路的中央。我一个前扑追过去,蚂蚱“腾”地逃跑了。我站立不稳,一个马趴跌到路中央,弄的满身是土,自己却咯咯地笑了。爬起身发现,裤子也跌破了,透过破洞捅捅跌破的膝盖,仍然是咯咯地笑。泥土里爬滚长大的乡下孩子,谁能没有一堆土路上的趣事呢?那些调皮的男生会尤其多些。模仿电影里的人物玩打仗,挖陷阱、摔泥巴、掏鸟窝、玩沙包、爬树比赛,还有摔跤等带些原始野蛮的玩项都是在土路边完成的。在那物质与精神都相对贫瘠的岁月,土路给了我们许多难以忘怀的快乐。
乡村土路是感情的纽带。每年夏天雨水多,大水经常把路面冲垮。雨后,没人叫唤、指派,村民们纷纷自发行动起来,张家出车,李家背筐,你一趟我一趟地把土运来了,把冲坏的路面垫平,夯实。这种和谐友善的团队精神,在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看起来是多么的可贵,但乡村土路却轻而易举地把这种精神凝聚起来。土路不只串连着同村人的道德需求,更传递着村与村之间的血脉亲情,一桩桩婚姻就是靠土路联结而成。村子里的姥姥、奶奶们,当年就是悠悠地横坐在驴背上,披红挂绿地从那条土路上嫁过来的。儿孙们长大了,还要踏上这条土路,去迎娶新娘,或者哭嫁女儿。一代又一代的兄弟姊妹亲情就在这一条条土路上延续下来,绵远悠长。鲁迅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我还想说,世上本没有路,一个人走的次数多了也便成了路。我的姐姐嫁与一河之隔的邻村,平时回娘家都是绕道过小桥,约摸半小时的样子。那年母亲病重,姐姐每天忙完自家杂事就来与嫂子一起伺奉母亲。这时适逢河里枯水,为省点时间,姐姐就在河道里踩着泥泞抄近斜穿过来,每天早上走过来,帮母亲洗涮擦洗喂饭喂药之后,傍晚再踩着原路返回。就这样,每天早来晚走,循环往复,日日如此,半年后母亲去世,原本泥泞荒芜的河床已被姐姐踩出一条磁实明亮的小路。这是一条专属于姐姐的路,一条系着孝心和亲情的路。
乡村的土路虽然质朴,却不失其美丽。在它尽情奉献给乡人的快乐时,也印证了历史的厚重感。站在土路上,如果我能穿越时光隧道,说不定我能看到战争的烽烟,看到时代的变迁,看到百姓的生死悲欢。
日寇全面侵华之后,冀中平原成为抗战的主要战场,平静祥和的乡村土路上遭受了日本鬼子铁蹄的肆意蹂躏。老人们说,日本鬼子一来,远远地就能见路上尘土飞扬,所过之处的村庄,火光冲天,鸡飞狗跳。乡亲们见状便急速奔走相告,纷纷撤离隐蔽,由大路转小路,再小路转到庄稼地里,或扶老携幼避难,或组织民兵伏击。密如蛛网的小路,形成了牵绊鬼子的迷宫,让它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海洋。无数的有志青年也是沿着这土路走向了外面的世界,走向保家卫国的战场。
我的三奶,现在已九十岁的三奶,十六岁那年(一九四三年)的春天,披红挂绿地坐在驴背上,沿着土路进了我村,嫁给了三爷。婚后小两口才过了半年的幸福日子,那年秋天,三爷相应共产党的抗日号召,毅然参加了八路军,走上了抗日战场。当时我的三奶已有四个月的身孕了。三爷和同村几个小伙一起走的时候,深明大义的三奶噙着热泪,在队伍后面跟了很远,很远。跟累了才停下脚步,又朝队伍行进的方向望了很久,很久,直到泪水迷糊了双眼,打湿了脚下的土路,再也望不见了三爷的背影,才一路哭着回来。三爷这一走就再没回来。在以后的日子里,三奶无数次站在路上向着三爷离去的方向张望,等着自己的男人回家。开始是她一个人等,后来是抱着孩子等。两年后,也就是抗战即将胜利的前夕,三奶终于在土路上等来了三爷。可三奶等来的不是三爷本人,而是公家人送来的三爷遗骨。见到三爷的遗骨,三奶抱着孩子,慢慢双膝跪到在土路上,朝三爷的遗骨磕了三个头,然后身子一歪,三奶晕了过去,娘儿俩一起躺在土路上。即刻,土路上升腾起一股悲壮之气,感天动地!
自那以后,十九岁的三奶成了寡妇,带着三爷的遗腹子,也就是我的堂叔,风雨里摸爬滚打,辛辛苦苦艰难度日。无论三九严寒还是七月流火,乡亲们总会看见三奶来往于乡间的那些土路,去种菜,去割草,去洗衣,去放鹅。三奶的苦心没有白费,堂叔慢慢长大了,也非常懂事,后来堂叔上学念书,在学校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三奶苦巴苦结下,堂叔念了小学念了初中又念了高中。由于表现突出,加之烈士子女,堂叔高中毕业后,被县文化馆招去当了宣传干事,负责县志的搜集、整理、编纂工作,并兼给各乡村放映电影。从这个村到那个村,从这条路到那条路,堂叔把自己勤勉的脚印反复叠印在这长长短短的土路上。一部老式摩托车,一架放映机,一支笔,一个工作手册本,是堂叔下乡时全部的设备。在那精神娱乐极度匮乏的年代,电影就象甘泉雨露滋润着人们贫瘠的精神世界,给人们带来无比的快乐。土路上只要远远地看到堂叔的身影,乡人们就会快乐地奔走相告,然后小村就会沸腾起来。据说堂叔最喜欢放映、人们也最喜欢看的是抗日片,如《地道战》《平原游击队》等等。趁走乡串村放映电影的机会,堂叔还搜集整理民间文化,遇到有价值的东西就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随后写成文章编辑成书。堂叔许多关于民俗民风的乡土作品曾在省、市级刊物上发表过。于是那些乡土文化,和堂叔一样踏着乡间的小路走出去,走向外面的世界。
后人们也一代代从乡村土路上走出去了,堂叔的儿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了省城,堂叔的孙子则凭借自己的优秀去北京发展。逢年过节,老一辈子少一辈的,无论是走路还是骑车或者开车,都会顺着土路回到老屋,与九旬的三奶团聚。这时的三奶特别开心。三奶一辈子没有走出乡村的土地,乡村的土路耗尽了三奶的一生,但却没绊住她的坚强和希望,她的志在四方的儿孙们不就是她放飞出去的梦想吗?
乡村的土路就是活着的历史,厚重而沧桑,虽然被岁月蒙了风尘,但却会时时被惊醒,时时然鲜活如初。近年来,随着经济迅猛发展和交通设施完善,许多乡村土路都修成了水泥路,水泥路为现代人提供了快捷的交通,大幅度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我们在感恩水泥路快捷方便的同时,也不能抹杀匍匐于乡间蜿蜒曲折的土路所历经的沧桑和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文明;土路上滚爬长大的我们也忘不掉土路带来的快乐,忘不掉土路渗透于我们骨子里的朴实憨厚、任劳任怨的本性。
今天,走进冀中平原,尽管触目所见的大多是平坦结实的水泥路,然而,土路并没消失,它只是化身做了水泥路下坚实厚重的基础,承担起更重的责任,它依然在飞速滚动的车轮下挺直着腰杆。
不信?你闭上眼,土路上的风烟又会滚滚而来:三爷出征离去的背影,堂叔下乡的脚步,父亲咕噜咕噜的牛车,高大挺拔的大树,娇艳清丽的花草,还有我小时候捉蚂蚱撒落在土路上那天真无邪的清脆笑声……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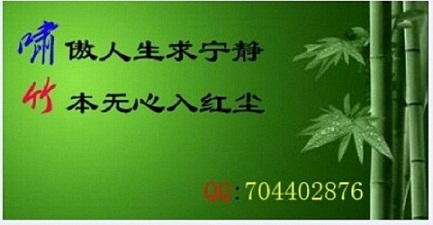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