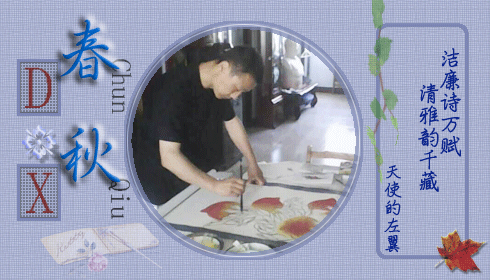【丁香收获】远去的岁月(散文)
【丁香收获】远去的岁月(散文)
![]() 1、黑天天的味道
1、黑天天的味道
去北面野地给鸡鸭割草的时候,一大片绿油油的黑天天秧豁然出现在视野里,果实还没成熟,圆溜溜的,一串串晶莹剔透,如绿玛瑙一般,饱满而有光泽。当然这个时候是不能吃的,要等到上秋变成黑紫色(也有黄天天)才行,那酸酸甜甜的味道,实实在在地丰润了童年的记忆和味蕾。
这种小时候随处可见的野生植物,看似其貌不扬,却也不是无名之辈,它学名叫龙葵,怎么样,是不是高端大气上档次?晋郭璞《尔雅》中说,黄河以北称之为龙葵。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中提到,龙葵四月生苗,嫩时可食,柔滑。渐高二三尺,茎大如筯,似灯笼草而无毛,叶似茄叶而小。五月以后,开小白花,五瓣,黄蕊。结子正圆,大如五味子,上有小蒂数颗同缀,其味酸。看看,人家可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的。不过当年的我们哪管得了这些,哈喇子淌出来多老长,就认一个字——吃。
每年春天,当春风吹醒了万物的时候,田间地头,房前屋后,墙角,仗子旁,天天如精灵一般,和庄稼苗、野草一起高举起鼓胀的芽孢,一点点从土地里挤出一条缝来,它绿色的身影在阳光下伸展,天气一天暖似一天,日子一寸一寸的都有意思,给我们这些馋猫们带来酸酸甜甜的念想。
我们每天放学都漫山遍野地追逐着去挖野菜,看天天秧一点点地长出绿叶,分叉,开出白色的小花,再冒出青绿色的小小果实,然后掐着手指头算天天成熟的日期。盼啊,盼着,这一颗颗小小的心啊,整天跟着黑天天跳动。黑天天由绿转红,由红变紫,终于有一天,黑天天成熟了变黑了,孩子们欢呼着,雀跃着,顾不得和野菜较劲了,把筐和剜菜刀一撇,还说啥呀,先过了馋瘾再说,要不晚了,小伙伴早抢没了。那些黑色的小天天,果实饱满黑亮,看着就招人稀罕。成熟的黑天天一天比一天多,密密麻麻的如满天繁星,眨巴眨巴它的眼睛召唤你,叫你再也挪不动脚步。小时候乡下的孩子基本没什么水果和零食,天天就成了百吃不厌的美食,也渐渐成了流淌在血液里的眷恋和乡愁。
黑天天秧顽强,不需要任何人的眷顾和关注,也不管在什么土壤和环境下,风吹雨打都不怕,在天地间默默地生长、茁壮,默默地开它小小的花,默默结它甜甜的果,不惊不扰,与世无争。我们的童年亦是如此,没有娇生惯养,没有漫天飞的特长班,也没有爬不完的书山,趟不完的题海,整天满世界疯跑,常年的风吹日晒让我们皮肤黝黑,终日的奔跑让我们健步如飞,用老人的话说一个个如天养的一般,生龙活虎,从不生病。
一嘟噜一嘟噜黑黑的圆圆的果实像熟透了的黑色葡萄挂满了枝秧,眼神里充满不可抗拒的诱惑。我们可不管它有啥营养和药用价值,只为了解馋。也没有功夫一颗颗往下摘,大把大把撸下来,大把大把往嘴里送,狼吞虎咽,连梗都不放过,三下五除二全都咽肚里,用大人的话说,要多下齿烂有多下齿烂。嘴里漫过酸甜中夹杂着淡淡的青草味,很奇妙的感觉。常常吃到乐不思蜀,这个时候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无济于事。
吃够了还要摘上一大茶缸子带回家,有的直接割一大捆天天秧,回家慢慢吃。到家先去井院压水,先压出的水倒掉,直到压出冰凉的水后,将天天往里面一镇,凉透的天天,那口感才叫一个爽呢。有时候吃天天时猛地咬破,它的汁液和籽就会迸出来,弄的满身满脸都是,加上天热淘气出汗,脸上黑一道白一道,身上花里胡哨的,舌头黑紫黑紫的,免不了要挨上一顿骂。但跟天天带来的快乐相比,神马都是浮云。
黑天天被我们消灭以后,黑天天秧可是鸡鸭和猪牛的美味,我们把黑天天秧剁碎,拌点玉米糠往地上一倒,鸡鸭们蜂拥而上,风卷残云般,不一会就一扫而光,下的蛋又大又香,还经常有双黄的。或者在大缸里沤两天喂猪,猪们甩开腮帮子一顿造,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滚瓜溜圆,比吃啥饲料都上膘。
童年的记忆,从这一颗颗小小的黑天天里漫溯出来,带着原汁原味的乡野气息一点点将我带回旧时光,带进那些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岁月。儿时因为有了天天的陪伴,快乐竟不曾缺席,每每盘问时间都去哪了的时候,这些记忆穿越时光跳将出来,告诉我们,曾经多么美好。
因为开荒和农药的使用,现在黑天天秧已不多见了,即使有,现在的孩子也不屑一顾,全然没有我们当年的热切甚至疯狂。想想也是,现在超市商店里的水果品种多的数不胜数,谁还会钟意这不起眼的黑天天呢?很多记忆也只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了,所以它便尤为珍贵,更让离家的游子魂牵梦绕。那一颗颗黑天天像一只只黑夜里的眼睛窥视着我们儿时的心事,带我们一遍遍回想,一遍遍反刍经年。渐渐消失的不只是天天,还有我们纯真的少年时光。
2、那时年画
总是感叹岁月匆匆,如流水般一去不复返,不知不觉中,一个四季轮回就这样挥手作别。当集市上花枝招展的年画和醒目招摇的对联在热烈地交头接耳时,才猛然惊觉,年已经准备就绪,搭乘时间的列车一路风驰电掣,说话间就要到了。
如今城里装饰豪华不再需要年画了,即使悬挂字画也与年无关痛痒,唯有乡间还可以捕捉到它们的身影,却与当年大相径庭,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了。现在的画与时俱进,高端、大气、上档次,年画也纷纷效仿,像精心装扮的女子,虽悦目,却总觉得有了一丝浮华与冷傲之气,远不及儿时的那种年画亲切、随和、有吸引力。那时年画纸质一般,如同那时的乡间女子一般不施脂粉,素素的一张脸,虽不加修饰,却有着一种天然的淳朴,眼角眉梢少了风情,似乎藏着某段久远的故事,纯美清澈,虽不是国色天香,但赏心。
似乎所有和我一样年纪的人,对于传统年画都有一种特殊的情结,那些色彩斑斓的图画活色生香了一段童年时光,也见证了那时的生活和心情,折射出鲜明的时代烙印。
过年买年画,给简陋的房舍增加一些喜气和色彩,是每个新年家家户户必备的功课。年画是中国画的一种,历史源远流长,始于古代的“门神画”。相传,唐太宗李世民生病后常常做噩梦,耳边似乎经常有鬼哭神嚎,以至于夜难成眠。大将秦叔宝和尉迟恭知道后,便自告奋勇,一个持剑,一个拿叉全身披挂整齐站立在宫门两侧,果然以后平安无事。李世民感念之余,命画工将他两威风凛凛的形象绘在宫门上,称为“门神”。后逐渐演变成了画像,清朝光绪年间,正式称为年画。年画是民间艺术苑中的一朵奇葩,由早期的自然崇拜和神祗信仰逐渐发展为驱邪迎祥、祈福消灾的风俗,寄托了人们对幸福安康生活的向往和祈祷。
年画的内容也是无所不有,带着芳香的泥土气息。花草虫鱼,植物风景,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国家领导人,英雄人物,十二生肖,神明等等尽在其中。无论哪种都是人们心中描绘的理想的生活图画,表达了对美好的最热烈的追求。像什么鲤鱼跃龙门,莲年有余,招财进宝,吉祥如意,很多利用谐音寓意,直观或是隐喻。门上贴门神,保佑家宅平安,墙上贴一对大胖男孩和女孩,寓意儿女成群,或是子孙满堂,贴领导人和英雄人物,表达了对他们的崇拜和敬仰……虽脱离了柴米油盐,不过是一些无法实现的梦幻,却是普通百姓精神天地的呈现。
而我们那时最喜欢的就要属那些民间传说和故事了。小时候,物质匮乏,生活水平也低,乡下的小孩吃喝都成问题,更不要说故事书了,所以每年更换的年画就成了我们的最爱,是我们最早的启蒙读物。每次妈买年画时,我都要求自己去选,而且一开始是不买的。要挨个摊位去翻看,一次看不完,下次再去,每每脚冻得像猫咬似的,全身都冷透了,在卖画人不耐烦的神情里一步三回头,磨磨蹭蹭地离开。常常拿起这幅,又舍不得那副,再三比对之后,最终选定自己钟情的那幅。看小贩把画小心地卷起,然后轻轻地抱在怀里,欢天喜地跑回家,心里、眼中有花徐徐盛开。每次都央求妈多买一些,恨不得把所有的画都买走才过瘾。
每到贴年画的时候,都特别隆重。全家人各尽其职,妈在厨房生火打浆糊,然后我郑重其事地在年画背面刷匀浆糊,爸两手拿起年画的上部贴在墙上,再用笤帚小心翼翼地扫平整,弟弟则站在一边指挥,看贴的正不正。这时全家的眉眼里汩汩流淌着喜悦和对新年的祈盼、憧憬。这些年画像是给斑驳的墙壁穿上了新衣,整间屋子都亮堂起来,年的味道被渲染得愈发浓郁醇厚。
贴完年画最开心的就是去小伙伴家串门了,跪在人家的炕头,看那些精彩的故事。故事年画是一张画上画出许多大小一样的画面,一个画面下面是一些简明的故事情节。像《牛郎织女》《天仙配》《三英战吕布》《白蛇传》《鸳鸯楼》《杨文广招亲》《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卖油郎独占花魁》等等,多年以后读冯梦龙的“三言”,才知道很多故事出自这里。戏曲剧照如《孟丽君》《花为媒》《沙家浜》等也是特别精彩养眼,比爸妈讲的故事要生动形象的多。那些曲折离奇、惊心动魄的故事,配上惟妙惟肖的人物,活灵活现的画面,色彩纷呈,精美绝伦,丰盈了我们年少无知的时光,满足了我们的求知欲望,深深地烙印在生命之中,永远无法忘怀。
随着时代发展,年画渐渐离开了年的舞台,逐渐被一些名人字画、挂历、十字绣、工艺品等取代,但年画曾带给我们的美好岁月依旧清晰。其实,年画不仅是“年”的附属和点缀,更是一项民族文化的瑰宝,因为它包罗万象,记载了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以及创新的民族精神。2006年,国家公布了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就包括杨柳青木版年画,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等十二项木版年画。衷心祝愿我们的传统年画在非遗的庇护下,能继续在历史文化进程里发扬光大,落地开花,于我们也是一种慰藉,熨帖而温暖。
无论岁月怎样变迁,那时的年画以及和年画有关的岁月,朴素而生动,亲切而美好,在我们这一代心中是永远的念想。
3、舌尖上的东北之酸菜
时光荏苒,转眼又是深秋。城市将乡间的声音阻挡在高楼大厦之外,唯有林间飘飞的落叶和远处连天的衰草暗示着季节的信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两场霜冻过后,小区里的大白菜却晶莹碧透,虎虎有生气,不由得想起老家又到了渍(ji)酸菜的时节了。酸菜,古称菹,《诗经.小雅.信南山》中说“中田有庐,疆场有瓜,是剥是菹,献之皇祖”,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菹菜者,酸菜也。《齐民要术》更是详尽记载了我们的祖先用白菜(古时叫菘)等原料渍(ji)酸菜的多种方法,可见其历史悠久。
渍酸菜在东北乡下是家家户户每年秋收之后、上冻之前必修的功课。渍酸菜首先需要一口大缸,人口多的人家一口缸哪够用啊,漫长的冬天就指着酸菜活着呢,渍少了,吃得舔嘴巴舌的多没劲啊。不管是富贵人家还是普通百姓,酸菜都是冬季首选。相传,张作霖的大帅府当年就有七八口大酸菜缸,可还是不够吃。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恩曾经高官厚禄,在文革时期惨遭迫害,弥留之际,最想吃的就是家乡酸爽可口的酸菜,那浓浓的味道已融入他的生命之中,让他在生命的尽头依然念念不忘。
男人们把闲置了一春零八夏的大缸转着圈地挪进屋,用热水洗刷干净,铺上塑料备用。女人们扎着围巾,穿着旧棉袄在菜地里忙得不亦乐乎。把放倒晒了多日的大白菜,挑那些菜帮多,菜叶少,棵大实心的,掰掉老帮,剁去根和老叶,收拾得干干净净,立立整整,像新嫁娘一样神清气爽。白白胖胖的大白菜用热水烫过,放入凉水激一下,再一层一层码在缸里,码一层白菜,洒一层盐。盐不能多,多了酸菜会苦,也不能少,少了味道就淡。码好后,注满清水,封好塑料,最后压上大石头,放在适宜的地方。温度不能太热,否则酸菜易烂,也不能太冷,温度不够,一时半会还渍不透。大白菜在神奇的大自然的发酵中,脱胎换骨,完美蜕变成酸香味醇,韧性十足的酸菜。然后再腌一小缸芥菜、萝卜、芥菜樱子等,一家人靠这些度过漫长枯燥的冬天,将那些清贫而简单的岁月过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每年的冬天,从冰冷的泛着冰碴的缸里捞出酸菜,搭在缸沿控去酸汁,个儿大、味儿足的酸菜往菜板上一躺,如翡翠般晶莹剔透。一层层扒下来,用片刀片成薄片,切成细细的丝,这可是检验刀功的时候。酸菜切好,用温水泡一会,攥干水分,放点五花肉,小火大锅咕嘟嘟多炖上一会功夫,鲜溜溜,酸爽爽,香喷喷的味道冲撞鼻腔,沁入心肺。酸菜和五花肉实乃天作之合,相得益彰,堪称绝配。酸菜吸油,将五花肉的油脂吸收后,不柴不哏,五花肉则去腻增香。如果再来点血肠,辅以韭菜花、蒜泥那更是锦上添花了。喝一碗热乎乎的酸菜汤,开胃爽口,美得不要不要的了,是东北人无论走到哪都心心念念的美味。在飘着大雪的冬夜,炖上一锅酸菜再蒸上一锅粘豆包,父辈们烫一壶老酒,将人世的苦辣酸甜一一倾诉,收拾起疲惫的情绪,怀揣着对生活的一往情深,奔向更加美好的人生。
酸菜有很多做法,比如开胃爽口的“吉菜粉”,香而不腻的酸菜馅饺子、包子、馅饼,味美汤鲜的酸菜火锅、麻辣鲜香的酸菜鱼等等。印象最深的要数妈做的“酸菜篓儿”了。“酸菜篓儿”做法其实很简单,先和玉米面,再捞出一棵酸菜剁碎,用温水投净,挤去水分,然后用盐,味精和匀,一般时候是吃不起肉的,在馅里放两勺荤油,加一些海米就很不错了。最后玉米面包上馅料,由于玉米面没有白面的粘性,不能随心所欲做成各种形状,只能团成半圆形,装馅像往背篓里使劲塞东西一样,最后上锅蒸,十几分钟后,满屋子便氤氲出酸菜的清香,让人馋涎欲滴。虽然粗糙的玉米面和没有肉的酸菜简单组合在一起,对于那个年代的我们来说也能吃出饕餮大餐的味道来。
酸菜生吃也是不同凡响。那些年在外打工,最怀念酸菜心的味道。小时候,妈切酸菜的时候,我和弟弟总是围在她左右,眼巴巴地等着,看妈一层层把酸菜帮掰下来,最后剩下酸菜心赏赐给我们,那酸爽脆甜的味道足以让我们欢天喜地一整天。如今在腻歪了鸡鸭鱼肉之后,来份酸菜心,那清淡爽口的味道经过喉咙,一路下滑至肠胃,岂是舒服二字可以形容?
东北人对酸菜情有独钟,酸菜是东北人血脉里越发酵越脆爽的天性,是东北人舌尖上越咀嚼越有味道的乡愁,是东北人难以割舍的情结。每个冬季,酸菜是餐桌上的主打菜,多年来霸主地位始终不曾动摇,即使在反季蔬菜当道的今天,酸香味醇,脆性十足的酸菜依旧是东北人的最爱,无可替代。
天天的顽强生命力更值得我们赞颂!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