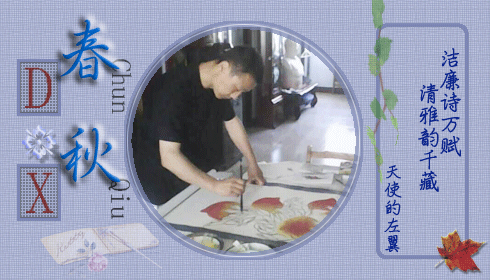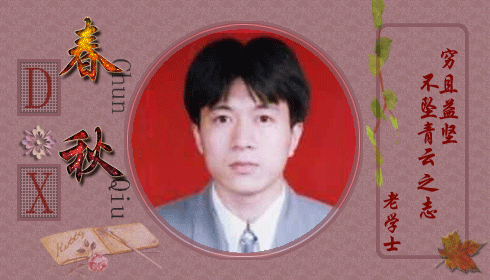【丁香收获】村西那面坡(散文)
【丁香收获】村西那面坡(散文)
![]() 一头是鳞次栉比的房舍升腾起缕缕炊烟,男耕女织,鸡犬相闻;一头是荒凹秃岭间,随处可见馒头似的坟茔。阴阳两界竟被一条土坡分隔得这样清清楚楚。
一头是鳞次栉比的房舍升腾起缕缕炊烟,男耕女织,鸡犬相闻;一头是荒凹秃岭间,随处可见馒头似的坟茔。阴阳两界竟被一条土坡分隔得这样清清楚楚。
这样安置实在是老辈人的智慧。原因大概是村东有汾河水的浇灌便利和“官道”通过,是人们“安身”的“宝地”,而村西则沟沟岔岔,土地贫瘠干旱,种庄稼困难,埋死人到十分相宜。
自我记事起,村里谁殁了,不说他(她)死了,而是就说他(她)“上西坡啦”。是不是这“西”字既指范围又暗含西天的意思?不得而知。
既然是个“分界线”,村里人就不马虎。
出殡这日,子孙身着孝服,一手擎着柳木番,一手撒着纸钱,趿拉着白鞋,由人搀扶着哀哀地走在十几号抬着的棺材的前面;棺材后面跟着嚎啕大哭的男女子孙。这支队伍在村巷的主要街道上缓缓而行。人们手头的活儿很多,起早贪黑干,也未必忙得过来,但他们仍然认为“缓”是应该的。一个人一辈子不论活得风光还是卑微,就要永久辞别这个村庄了,有什么理由不让他(她)多瞅几眼这里的留有他(她)层层叠叠脚印的道路,多瞅几眼这里他(她)闭上眼睛都能详细道出子丑寅卯的一草一木呢?人们在哭天抢地的哀嚎声里追忆着躺在棺材里的这个人的一生,也许会联想到自身的过往和未来吧?总之,他们就在这种氛围里将逝者抬到西坡上了。
爬上这条足有半里长的土坡,逝者的子孙后辈就将哭丧棍横放到地上,跪在了道路的两旁;这时,执事总管高喊“孝子谢哩”,送殡队伍闻声,齐呼“起”,而后就抬着棺材呼啸而去。
从此,坡下的人便将逝者留在了记忆里,也许偶尔提及,也许仿佛这个村里就没有生活过这么个人;而逝者呢,他(她)的灵魂只能以“坡”为界,在“坡”以西飘荡。我在想,有一天,我的灵魂也上了“坡”,当我飘到“坡”沿上,正好瞄见我的子孙掉进了河里,或者他们的房子里冒出了浓烟,我该怎么办?我刚进村,人们就惊呼着抡起桃木剑便当心刺来,我逃还是不逃?这真是难办的事情!
上个世纪,有那么一个时段,隔不上三二年,我就有一位亲人被抬上“西坡”。
我琢磨了一下,上了“西坡”的人的“住所”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由风水先生拿罗盘择定。这类主家有“雄心壮志”,指望借祖宗的阴德成件“事”;二是入祖坟。这是祖规。后辈一代代地跟着祖坟的“线法”,依次扎“穴”;三是选在自家地里。这既麻烦少又便于日后的照看。
我父母的坟就选在我家的责任田里。
那半亩来地,属于绵土,适合种植花生。我上大学的学费全赖于此。那时,目不识丁的父亲锄草展腰的当儿,常常眺望远处的山峦沉思着喃喃自语:“人吃土一辈子,土吃人一口。”说罢,往手心里吐口唾沫,又埋头锄地。十几年后,他埋在了他洒满汗水的这块地里,我才掂量出那话的分量。
父母安葬在这里,除清明上坟,随着年龄的增高,我来这里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是领着一家来,大多数情况是独自一人来。
烧几炷香,磕四个头,然后盘腿坐在坟头的松树下发呆。坟头的荒草迎风嗦嗦。我听不懂它们的语言,我只能听见自己的心声。逃离喧嚣的闹市,在这种寂静的旷野,紧偎父母的坟茔,我逐渐明白了不少道理,似乎也禅透一些古人做事的玄机。我忽然也想效仿古人,给父母坟头竖立一块大大的石碑,那上面不镌刻父母的简历之类的文字,只刻当儿子的我自己的愧疚和忏悔;也想栽植几株大树,给父母遮挡风雨;还荒唐地设想,在父母坟旁不远处建造几间茅屋,住在里面,听听父母夜里是否还咳嗽喘息?
我的目光投向远处。逡巡四周,我们的老邻居刘玉柱、刘子康、崔黑大、崔百川,还有与父亲吵过架的腊娃、海有,他们的音容笑貌就会洇印出他们的坟头。我能感觉到,他们手搭凉棚正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良久,他们认出了我,他们说:“娃,你几时回来的?就你一个人,孩子们呢?这些年,你过得可好?粮食够吃吗?”我依次回答他们的询问。我也问他们可好?这下可热闹了,他们说什么的都有。但最趋向一致的意思是,对后辈的关心和关爱。
我感到了为难。我若将这些土底下发出的声音传达给他们的儿孙,他们不把我送进疯人院才怪呢?但我又不能违拗这帮看着我长大的老人的心意。就在这当口,我瞥见一只不知名字的黑鸟栖息在一蓬酸枣树上鸣叫。我想,好啦,我就叫我的灵魂化作一只鸟吧!那样,好多问题就解决了。我可以展翅飞到“西坡”下边去,把老人们一些重要的事——诸如他们的坟头上被田鼠钻了个洞啦,他们缺东少西啦等等,用长长的啄,喳喳地告诉他们的后辈。当然啦,后辈们有什么吃不准的事,我也乐于飞到“西坡”上讨教老人们。这费不了多少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