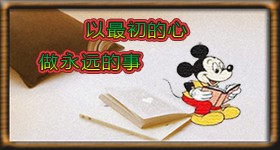【流年】魔镜(中篇小说)
【流年】魔镜(中篇小说)
![]() 一
一
正午时分,天色阴沉,风雨欲来。
房间里闷热得让人呼吸困难,杨冬藏坐在书房的窗前抽烟,眼神聚焦在对面那栋楼一户人家晒着的格子被单上。被单在风中飘摇,沿着晒衣杆自我缠绕,发出他听不见的嘶喊声,像是在给他表演一场独幕戏。
妻子冯君的唠叨声还是势不可挡地穿门而入,但好在他的耳朵还有一扇门,将其隔绝在外。
他拿出钥匙开了抽屉,拿出一个长方形木盒,木盒里黄色软布包裹着的是一枚褐绿色的铜镜。铜镜背面沿着镜边一周有水波纹,正中心一处凸起的银元般大小的柳条镂空纹,围绕着它的是四只类似麒麟的浮雕神兽。镜子正面还算光洁,但却无法映照出清晰的镜像,边缘处有一个黄豆般大小的腐蚀斑块。
他将烟蒂在烟灰缸里狠狠地碾灭,再将铜镜连同木盒装进一个黑色的塑料袋中,在心中狠下了决心,并开始思忖待会要怎么说。
客厅里,冯君正在摆碗筷,嘴里却还在念叨,说是在银行工作,也就听着好听,一个小职员,没钱没人脉,古怪脾气,遇事情只能干着急。说完用眼尾扫了一下杨冬藏。
我出去一下。他说。一边换鞋。
不吃饭?
不吃了,去迟了李主任就午睡了。
冯君停顿了一下,看了一眼那个黑色的塑料袋,问他是不是真的下定决心送了?杨冬藏没有回应,算是默认。
下楼的时候,读初三的女儿刚从辅导班补习回来,蹲在那锁自行车。杨冬藏的目光刚触及到女儿时就自动弹了回来,并下意识地将黑色塑料袋往身后藏了藏。
对于女儿杨冬藏有愧于心。因为那时候有机会让她就读更好的初中,他没有花钱,现在却为了自己所谓的前途,要把铜镜送出去。
李主任叫李中华,比杨冬藏小一岁,他之所以能担当木兰县农村信用社联社主任的这个职务,源于他在省行的叔父这个后台支撑。李中华是个收藏爱好者,他有个二百多平米的别墅,整个二楼专门存放古董字画,数百件藏品都是他在全国各地四处淘来的,这句话有多少水分外人不得而知。据杨冬藏所知,早前一位女同事,才35岁就办了内退,跟随丈夫一起去外面做大生意去了。按照工龄,她根本不符合内退相关规定,但她投其所好,送了李中华一个时大彬紫砂壶,而那个款正是李中华觊觎已久的,价值自然无需明说。
杨冬藏的同事,不是高升就是调到各种待遇都要高于乡镇分社的县联社去了,只有他十二年来一直待在乡下,每天坐二十分钟的大巴车早出晚归。这次联社又有一个人事股股长的空缺,有消息说,这次是要从各乡镇分社选调一位上去。冯君一直催促他去疏通疏通关系,把握这次机会,被她念叨得烦了,也是对自己当下的处境感到厌倦了,不然杨冬藏是不屑去找李中华的,毕竟他和李中华是有宿仇的,他甚至猜想,这些年自己一直被压制,都是李中华在公报私仇。
那是十二年前的事情,杨冬藏参加信用社公开招聘考试,六十多人参加考试,按分值高低,录取五个人。他排名第三,但公布录取结果的时候却没有他。后来经过父母的无数次上访、找人,才得知其中缘由,因为他是普通市井小民,家里无权无势,他的名额被有背景有后台的李中华顶替了。也许是他们自知理亏,也为了息事宁人,最后杨冬藏还是进入了信用社工作,只是被分配在了偏远的二泉分社。李中华进入了县联社,那次考试对于他而言,只不过是一个过场形式的陪考而已。但这利用强权冒名顶替的屎盆子扣在了他的头上,所以杨冬藏第一次见李中华的时候,就从他的眼里看到了锋利的寒光,这寒光十二年来都未曾消失,虽然他们不常见,但杨冬藏确定,寒光无处不在。
等红灯的时候遇见了一个熟人,寒暄的时候他下意识地捏紧了黑色方便袋的袋口。那人走后,他发现自己的手心满是汗,这时候他才意识到,他是没有勇气站在李中华面前,将这个铜镜双手供上的,更没有勇气向这个他厌恶的人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
算了,不送了,送了他也不一定将那个位置给我。杨冬藏在心中这样告诫自己。
这个铜镜是他们家的传家宝,据说是他当赤脚医生的爷爷年轻的时候救过一位大户人家的孙子,铜镜是他们为了感谢他赠的。杨冬藏的父亲前些年将这个铜镜拿给专业人士鉴定过,说是明朝的,价值大概在五万元左右。铜镜本来一直在父母身边,一次家里遭了贼,老爷子才交给他保管。
杨冬藏没有回家,他坐上公交车,去了西郊杨庄老家,父母住的地方。
小院子的门是虚掩着的,开了门,没见父母人影,他往卧室寻去。轻推门,父母正在午睡,睡得很香,收音机里正小声播放着庐剧,唱得凄凄切切的,风扇悠悠地转着。父亲与母亲十指紧扣,搭放在父亲的肚子上,看着恩爱了一辈子的父母那苍老但安详的姿容,杨冬藏的鼻子突然有点发酸。
他不忍心叫醒母亲,即使他还没有吃午饭。轻轻关上门,走到院内,他发现那一垄菜地上青椒茄子韭菜黄瓜长势甚好。这些都是母亲种的,与田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母亲是闲不下来的,随着县城的发展扩张,前些年家里的田地都被征收了,这垄菜上生长着母亲的念想。他走过去摘了一根黄瓜,用手摩擦了几圈大口大口嚼起来,很脆,有一股自然的清香。
大哥杨春生发来一条信息,老三,我工地上出了事,一个工人重伤,家属闹得不可开交,治疗费与赔偿款是个无底洞,帮我弄点钱。
杨家本来有弟兄三个,老大春生,老二夏长,老三冬藏。本来杨母在怀第三个孩子时,杨父给他取名秋收,但那个孩子与这个世界无缘,三个月的时候夭折,于是秋收这个名字也留给了他(她)。夏长是在20岁那年的夏天,在鱼塘里捕鱼的时候滑入深水区溺亡的。夏长去世的第二年,春生去了上海做了粉刷匠,后来竟五个年头渺无音讯,家人都以为他已客死他乡。五年后回来时,他已经拖家带口了,妻子是个上海郊区姑娘,独生女,他做了入赘女婿,一岁的儿子也随了母姓。又过了些年他从小工变成了小包工头,腰包鼓了起来,但他却很少回木兰来看父母,他说在大城市生存不容易,做倒插门女婿也身不由己,轻轻松松的一句话,就把赡养父母的责任推到了杨冬藏的身上。杨冬藏也能理解他,他那个耿直甚至有些暴躁的脾气,做了倒插门,说明大嫂是个比他更厉害的角色。也因为这事,冯君没少和他吵架。
杨冬藏没有回复杨春生,他带着那枚铜镜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气压低得让他喘不过气来,已经湿透的劣质衬衫紧紧地贴在后背上,就像一直如影随形的低迷命运,你刚把它牵开,它却似生了眉眼一样,锲而不舍地再次贴过来。
二
办公室里,两个年轻人在聊着一些八卦,身体随之话题的深入而笑得前俯后仰,杨冬藏看着他们那不谙世事的脸,感叹青春真是一个好东西,就是太不经用了。
后来有同事小声告诉杨冬藏,谁要能拉到三百万的存款任务,那个人事股长的位置就归谁。他在脑中迅速将认识的亲戚朋友搜索了一遍,但一会儿就泄了气,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是没道理,如果他真有个能拿出三百万闲钱存银行的亲戚或好友,他这些年也不至于过得这么憋屈。
临近下班的时候,杨冬藏接到了老爷子的电话,叫他回家一趟。他问是不是哪不舒服。老爷子说不是,说具体事情到家再说。放下电话后杨冬藏猜想大概是因为大哥的事情,躲是躲不掉的,该来的总会来,时间不会因为你不想就停滞不前。
三儿,老大的事情你也知道了吧?老爷子见了杨冬藏寒暄了几句后开门见山。
爸,我是知道,但是我到哪搞钱给他?您老也不是不知道我的情况。是呀,他一个月那一千来块的工资,扣去公积金和养老保险,所剩无几,冯君在超市上班也只有八百块的工资,家里的收入维持生计还行,却没有多少存余。
我知道,这些年你也不容易,老大的意思是你给他拿点贷款,利息他付,等他周转过来了,他立马还贷,不让你为难。
杨冬藏抽着烟没说话,太阳刚下山,暑气难消,母亲在院子里泼了几盆水,周遭的空气里立刻升腾弥散起一股泥土的味道,杨冬藏贪恋地深吸了一口气。
老爷子静静地等着杨冬藏开口,佝偻的他坐在小木凳上,像极了一张绷紧的弓弦。对于这两个儿子,老爷子内心里还是更偏向老三的,且不说老三这些年一直承担着照顾二老的责任,仅老三是他们家唯一一个靠读书走出农门吃上国家饭这一点就够了。老爷子是熟读四书五经崇尚孔孟之道的人,早年在乡村小学当过近三十年的民办教师,一直到退休都没能转正,这是他活了一辈子最为痛心的事情,仅次于失去杨夏长。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的他认为老三的处境和自己不同,现在的默默无闻都是为来日的崛起做功课。老大和他不一样,即使在外当了多大的老板,都是居无定所动荡不安的浮萍,难成大器,现在遇到这样的事,作为兄弟,他希望老三能够伸出援手,体现兄弟俩的团结友爱和他教育子女的方式是值得考验的。
好吧。杨冬藏突然想到小时候一次也这样热的夏天,大哥背着他走了好几里路去邻村看电影的情况。我尽量,能筹多少筹多少。
老爷子正了正身子,欣慰地点了点头。
爸,咱家那个铜镜……
杨冬藏话还没说完,老爷子立即打断,再怎么缺钱也不许打那个铜镜的主意!
我不是这个意思,算了,不说了,我也该走了。说完起身欲走。
在给菜地润水的母亲喊,三儿,吃了晚饭再走吧!
杨冬藏回了母亲,说改天和冯君以及女儿一起来吃饭。老爷子起身拍了拍他的肩,掌心里饱含着哪些意思,杨冬藏领略到了。母亲又摘了一袋子新鲜的瓜果蔬菜让他带回去,后来目送他走出小院子,眼神里布满疼惜。
杨冬藏回家后,冯君已经在洗碗了。到哪晃荡去了,回来吃饭也不打电话说一声。她嘀咕。
杨冬藏懒得解释,将一袋子瓜果蔬菜提进厨房,瓜果无言,但却替他作了解释。他不想也不准备将替大哥拿贷款的事告诉她,结婚多年,窘迫的生活现状将当年那个善解人意温柔大方的女孩变成爱计较爱唠叨甚至有些势利的女人。
女儿在开了空调的房间学习,灯光从虚掩的门缝里透出来,他走过去,轻轻地将门关严实,将外泄的灯光与冷气逼退,将一个舒适的不受外界侵染的空间留给女儿。
冯君给他端上面条时,杨冬藏收到了刘国庆的信息:冯老六在秀婷棋牌室。他顾不上吃饭,匆匆出了门,将冯君的怨言丢在身后。刘国庆与杨冬藏一样,也是二泉分社一名小小的信贷员,分管不同的村。他说的冯老六是个跑长途运输的司机,他欠的一万元贷款即将到期,别说本金,一年的利息他也是分文未交,每次打电话催要时都说在外地,又或者说在开车不方便接电话,最后干脆直接不接杨冬藏的电话。杨冬藏其实为了完成收息任务,一直在给他垫付。
棋牌室里烟雾缭绕,打牌的看牌的钓鱼的将几张桌子围了个水泄不通,汗水在空调房里被冷却之后的馊味混杂着烟味,散发出让人作呕的味道。刘国庆侧着脸抬了抬下巴,顺着那个方位,杨冬藏发现了叼着烟正在摸牌的冯老六。他站到他的身后,什么话也不说。一牌结束,冯老六对着穿梭在各牌桌之间给客人端茶递水的秀婷说,老板娘,没见杨会计在这呢?也不知道招呼一声。老板娘立马赔笑,什么风把杨会计吹来了,要不要给您安排一桌。
不了,我不会。杨冬藏从未在外上过牌桌,逢年过节偶尔在家陪亲戚打。旋即对冯老六说,冯师傅,见你一面真难,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把贷款利息结算一下了。
冯老六听了这话如同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杨冬藏扇了一巴掌,他虽然混得不怎么样,但好面子,而杨冬藏也正是了解他这一点,才说出这样的话。
他压制住怒火,皮笑肉不笑地说,杨会计,今天如果你能破个戒,陪我打几圈,贷款我连本带利一次性结清。说完从包里拿出一沓百元大钞,然后洗牌似地将钱翻得唰唰响,挑衅的目光分明在说:老子有的是钱,真的不给你你又能怎样?
杨冬藏是凌晨三点的时候走出秀婷棋牌室的,他拿到了冯老六一万元的贷款及2000元利息,但同时也输掉了456元。喧闹了一天的小城正在沉睡中,路灯昏黄,夜晚的风吹拂在脸上,有点腥甜的味道,一只红色塑料袋跟随着风来到脚下,他踩踏了一下,继续往前走,塑料袋在身后追着风忽上忽下,慢慢飘远,带着他的某些心绪,此情此景,他突然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空虚。
三
人事股长的位置是一颗悬挂在夜空中遥不可及的星星,就在杨冬藏忍痛准备转身离去,不再关注它的时候,突然有人拍着胸脯来告诉他,要带他去找这颗星星,这个人是他们分社的方田主任。
方田五十来岁,生得慈眉善目,秃顶严重,有点儿像弥勒佛,平时就算是发起火来,也没有什么震慑力,下属们也都不怕他。杨冬藏对他也没有太多好感,总觉得他是个笑里藏刀的人。那天下午,他将杨冬藏喊到办公室,还给他泡了一杯茶,告诉他一个叫杨三和的老板在隔壁永和县做钢材和房地产开发生意,身家不菲,他认识杨三和的新老婆小可,通过小可的牵线,争取到了杨三和的一笔存款,让杨冬藏准备一下,明天和他一起去永和县。
无欲则刚。当一个人看淡名利,世界会突然安静下来,就像你身处大山里的湖泊,坐在荡悠悠的小船上,天高云淡,绿水青山,虫鸣鸟啼。
小说冷静地叙述,抽丝剥离般刻画着人物,人性在故事进行中得到淋漓尽致地表现,极为深刻!
小说没有塑造高大上的人物,有的人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有的人初心积累,杀人不见血,有的人缺乏主见,胆小懦弱,被人当枪使……
故事之外的东西,让读者思考。
小说叙事沉稳,语言凝练,构架镜子,巧妙地使用道具“铜镜”,铜镜最终成为魔镜,就如贪念起,人性就成了兽性!
佳作,向怜幽学习!
你一直是写小说的高手,佩服!

迢迢会兮月下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