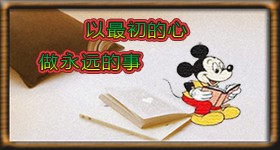【流年】箱子锁得很严实(小说)
【流年】箱子锁得很严实(小说)
![]()
确切地说,我和谢意的友谊是从父辈那里继承过来的,只是到了我们这一代更深了一层。我们都有一个刚愎自用、脾气暴躁、令人畏惧的父亲。谢意的父亲曾经在黄埔军校有过短暂的培训,在杜聿明警卫团干过八个月,官至上校,蛋镇的人都称他谢上校。1948年春夏秋冬,分别被解放军俘虏了四次。每一次都给他两个选择:一是调转枪口;二是领取路费回家。但他每次都没作选择,而是以过人的机灵成功逃脱,重新回到自己的阵营。1949年春天,他又一次被俘获了。我父亲认出了这个狡诈和宁死不降的国军上校,因为这是第三次落到了我父亲的手里。我父亲说,这一次你依然有两个选择。这一次,谢上校作出了选择,回家。但他没有领取路费。他靠步行和乞讨,从山东一直回到广西。我父亲和谢上校再次见面是在1983年,他们在蛋镇相遇了。我父亲犯了错误,从市自行车厂下放到蛋镇农械厂,实际上就是一个生产铁铲和锄头的手工作坊。母亲在偏僻而穷困的横水镇乡下,带着三个弟弟。谢上校是只有三个人的蛋镇玻璃厂厂长。我不能想象他们的不期而遇是怎样的情景。总之,他们成了最能促膝长谈的朋友,也成了最旗鼓相当的敌人——争吵的对手。他们相见恨晚,有说不完的话题,但又常常针锋相对,互不妥协。谢上校一直为他的宁死不降而自豪,至今仍坚持当初的理想信念,而我父亲永远为己方赢得了最终的胜利而沾沾自喜。有一次,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孩急匆匆地跑到我家——一间黑瓦房,问我是不是陈梭。我说是。他说你父亲被我父亲打破了头,快送去医院。我随着他去了玻璃厂。两个醉熏熏的男人仍然有气无力地扭打在一起,我好不容易才从一颗鲜血淋漓的头颅中辨认出了父亲。我试图将他背起来,但我力气不够。谢上校的儿子,是的,他叫谢意,瘦瘦的,腰杆不直,看上去营养不良,远没有发育,且生性懦弱,说话像鸡吱吱叫。他机灵而熟练地卸下一门板,我们将我父亲抬到卫生院。当然,兵家胜负难测,有时候是我们合力将谢上校抬进卫生院。在这过程中,我和谢意成了团结合作的好朋友、好兄弟,一起进了蛋镇高中,一起高考。只是我们都落榜了。这一年,我父亲心肌梗塞,突然倒在农械厂,再也没有爬起来。我和谢意将我父亲抬上一辆牛车,一起赶着牛车回到横水镇,将我父亲草草埋了。然后,谢意不顾谢上校的强烈反对和阻挠,毅然应征入伍。我到了县中学补习,第二年考上了一所破落的师范学院。四年后,我大学毕业回到县城,分配在县志办公室工作,将微薄薪水寄给正在读书的弟弟们之后,我再揭不开锅。更艰难的是,单位分房迟迟无法落实,睡办公室的日子难以为继,我如丧家之犬居无定所。谢意说,到我家里住吧。
彼时的谢意已经退伍。看上去比过去壮实了一些,性格也开朗阳光了许多,还蓄起了小胡子,戴一副度数很低的黑框眼镜,形象和气质跟过去有了很大的变化。当然,我跟在蛋镇的时候相比,也很不一样了。尽管如此,尽管四年没见,我俩的友谊毫无减弱,而且还要更成熟,像亲情。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通过不少的信,互相通报情况、彼此鼓励。谢意在部队里混得并不好,因为身体太瘦,训练跟不上,被安排到后勤部,欲当厨师而不得,养了三年猪,每年出栏二十八头,头头壮实而白净,获得战友们的一致好评。除此之外,平淡无奇,默默无闻,眼看就要退伍了。退伍前一个月,邕城78路公交车上,一个上了年纪的流氓公然调戏妇女。他犹豫和纠结了三个站的时间,才挺身而出,结果被捅了一刀肚皮,肠子都快流出来了。虽然流氓没有抓住,却因此立了三等功。退伍后,又因为他当兵时曾经在养猪之余学习过水彩画,在文化馆谋得了一份合同制差事,简称合同工,三年军旅生涯总算有了一个马马虎虎的结局。在县城有了一份稳当体面的工作,本应心满意足,但谢意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应该继续留在部队,上军校,当军官,建功立业,哪怕在部队养一辈子的猪,而不应该像绝大多数士兵一样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从部队回来的第一个月,他写了一本近三万字的养猪心得,寄给接他班的战友。文化馆的人都知道,谢意并不甘心情愿离开部队。他的父亲谢上校却十分欣慰,因为他一直担心和焦虑的中美大战没有发生,解放台湾的战斗也没有打响,他的儿子平平安安完完整整地回来了,而且迅速讨上了女人。谢意说到与其父亲的关系时,没有多余的言辞,只有一句:国民党的士兵永远无法理解人民解放军。
谢意住在文化馆狭长昏暗的四合院里,只有一间平房。中间隔了半堵墙,把房间一分为二。谢意说,你睡外头,他和姚芳睡里面。中间还有一扇门呢。关了门,谁也干扰不了谁。只是没有卫生间,公共卫生间要走到院子的尽头,解手还常常要排长长的队。老鼠肆无忌惮地穿行,半夜跳上你的床头也不要惊慌,也不必泼口大骂。它们才是四合院真正的主人。我搬了过来,照他说的办。
谢意和姚芳已经结婚一年多。姚芳相貌平凡,甚至过于普通,肥胖,矮,精力旺盛,脸上布满了雀斑。如果再观察细致一些,会发现她的左脸比右脸阔些许。但她通情达理,古道热肠,乐观开朗,耿直好客,对亲戚朋友耐心周到体贴入微。对我和谢意源远流长且无可挑剔的友谊赞不绝口,当然愿意接受我暂时寄宿,而且热情地为我张罗一切,把我当成了家庭成员,坚决不收我的伙食费,每天把我和谢意的衣服一起洗了,还紧锣密鼓地为我海选媳妇。开始的时候,我们三人都很客气,后来熟悉了,就不见外了,可以同坐在一张床上聊天,互相肆无忌惮地开玩笑、说荤话,她在里面更衣时也不忌讳我就在外面抬头即见,甚至习以为常地谈论性事。在文化馆四合院里公开谈论性事算不了什么,小孩也毫无顾忌地说。似乎是,男女之事跟一日三餐一样平常。半夜三更哪家女人控制不住自己发出猫一样的呻吟声,第二天会成为四合院茶余饭后的笑柄。大多数夫妇都曾经因为动静太大干扰过别人,被别人取笑过,但姚芳似乎是个例外。她向来悄无声息,连近在咫尺的我也几乎不知道他们的性事何时开始,何处结束。
姚芳是县第二国有瓷厂的职工,性格刚强,办事干练,说话气势如虹,家里家外全是她一人扛起来了。她八面玲珑,对四合院里复杂的人际关系应付自如。谢意喜欢认死理,有点小脾气,还喜欢跟人拌嘴。有一次,因为一言不合,谢意被院子里的一个送煤气的男人打了一记耳光,姚芳来不及脱掉高跟鞋便扑上去与那男的厮打,硬是从对方的手臂上啃下一块血淋淋的肉。谢意在姚芳面前向来唯唯诺诺,逆来顺受,还常常无缘无故招来她的一顿斥骂。只有我在的时候,姚芳才对他委婉些。谢意离不开她,不仅仅是这个家必须由她来支撑,更重要的是他患上了性瘾。
“这是职业病。”谢意说。
他说的并非扯谈。文化馆早已经跟文化毫无瓜葛,仅有的两间书画展厅被改装成录像厅。谢意是录像厅管理员,买票,验票,每天与涌进录像厅看毛片的男男女女打交道,清理满地的避孕套和粘乎乎的纸巾以及瓜子皮。他坐在门口,转身便能看到影幕上下流龌龊的镜头。即使不转身看,那些淫荡的声音也会一直撞击他的耳朵,抓咬他的心扉,跟随他回到家里,出现在乱七八糟的梦中,那些呻吟声像中了刀子的猪发出的尖叫和悲鸣,让他无法自控。一到夜里,他都要和姚芳交合。
然而,姚芳有性洁癖,乃至性冷淡,每次把身子给谢意,总像是施舍。而且是不定期的,有时候三天一次,有时候半个月一次。施舍与否,全看姚芳的心情。而影响姚芳心情的因素很多,煤气价格的波动,街坊邻里的流言蜚语,天气的变化,公厕的卫生程度等等,甚至因为突然被一只老鼠惊吓,都会直接让谢意来之不易的交合权得而复失。一旦丧失,当夜再也不可能失而复得,而需要新的等待。这一等,也许是三天,也许是五天,又也许,要等下个月。对谢意来说,这是世界上最漫长、最煎熬的等待,犹如等待彗星光顾地球。
这不能全怪姚芳。有时候我甚至认为这是谢意咎由自取。
谢意承认在部队的时候,跟一个给部队送菜的丧偶的女人谈过短暂的恋爱。短到只有三天。这本来没有什么,但他承认曾发生过一次关系。在一个猪圈里。那时候他除了喂猪,还管称。第一天,在送菜女人弯腰放下菜担子过称的时候,谢意看到了她的乳房,洁白而丰满。当她重新挑起担子要去厨房时,他伸手去扶她的胳膊,一直扶着她走出十米之外。她说,不用扶了,我能成。但谢意的手一直不愿意放开。她停下来说,你能帮我把菜挑到厨房去吗?谢意说,能。他侧着身子,弯腰贴到送菜女的面前,让她把担子送到他的肩上。在交接担子的时候,他的背结结实实地碰到了她的胸部。他转身,抱了一下她的腰。她犹豫了一下,轻轻推开他:这是部队,注意影响。他放开了手,把菜挑到了厨房。第二天,几乎是如发炮制,但他抱住她不肯松手,直到炊事班的人嚷叫了,他才把手松开。第三天,一见面,他直接把她抱进了猪圈,在猪乱哄哄的喊叫声中完成了他的第一次……如果在结婚前知道真相,姚芳肯定不会跟谢意结婚。姚芳曾经埋怨我知情不报。我发誓,我对谢意在猪圈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此事原本只有当事人知道,如果那个送菜女人不说出去,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谢意不应该听取姚芳的诱供,把此事如实说出来。其实有什么可说的?自从发生关系后,那个送菜女人再也不给部队送菜了,销声匿迹,好像她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世界上每天都发生无数的事情,有些事为人所知,有些事无声无息,随着时间消逝,一切都烟消云散,了无痕迹。人生中很多秘密就像粪便一样,经不起回味的。我们何必主动去化粪池里将自己的粪便取回来品味一番呢?
坦诚未必就是美德。
自从知道真相,避孕套像政治课一样开始强硬地介入他们的生活。姚芳必须见到避孕套稳稳当当地戴上了才能同意谢意爬到她的肚皮上去。原则问题,不容商量,威严如圣旨。为了换取交合的机会,谢意宁愿奉旨同时戴上三只避孕套。
谢上校几次从乡下来,质问谢意:为什么姚芳的肚子没有鼓起来。谢意支走父亲,恳求姚芳看在繁衍后代的份上,免戴一次避孕套。但姚芳坚决不允。她内心里无法磨灭送菜女人的形象。她跟我描述过,送菜女人,有时候像住在对门的保洁员,脸上有巨型黑疤,头发永远脏得像一坨屎。有时候,像老馆长的老婆,屁股比化粪池还大。有时候,像录像海报上的浪荡女,胸大无朋,人尽可夫。送菜女人无端被姚芳一次又一次地糟蹋、贬损,让谢意忍无可忍。有一次,谢意不知道从哪借来的胆子,对姚芳说,送菜女人长得像山口百惠。
因言获罪,谢意换来一次长达一个月零六天不得与姚芳同床的严厉制裁。他只能和我睡在一张床上。他的性幻想超出了我能忍受的程度,我宁愿在躺椅上过下半夜。我劝导姚芳,对男人的惩罚有一千种方法,但最坏的一条就是不让他过生活。姚芳说,难道不是他罪有应得吗?如果他的身体像你一样干净,我才舍不得惩罚他。我说不服姚芳,转而对谢意说,你可以嫖娼,近水楼台,找录象厅的暗娼,或多走几步找发廊的明娼,再不济,也可以去荔枝公园按摩室找野鸡解决问题——我给你钱,就当给你房租费。我不是开玩笑,县城的性开放程度已经赶上东莞,既不笑嫖,更不笑娼。如果不是因为手头拮据,我也考虑去试试。然而,谢意用蔑视和怀疑的眼神看着我,有些生气地说,你学坏了?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呀?你把我当什么人了?看样子他是认真的,他不会和别的女人发生关系,如果我再动员他嫖娼,他会跟我恩断义绝,反目成仇。
他努力讨好姚芳。
“他说的是牲口百惠——百惠是一头母猪的名字。”面对四合院此起彼落的哄笑,姚芳反复更正谢意的言辞。谢意早已经认错,也附和着姚芳:“我说的本来就是一头牲口。”
姚芳还不能容忍家里备有避孕套。
“即使将它们埋在床底,我也能闻到它们的味道,淫乱,恶心,让我想到公猪与母猪交配。”姚芳说,“但是,我知道自己是女人,有时候也不得不像她们那样张开双腿。”每次前,她都让谢意在夜色中跑到大成殿门口右侧,找到墙上免费发放避孕套的箱子,按下取套键,取回一只新鲜的避孕套。只取一只。取多了,姚芳不高兴,倒不是她担心其他人没套可取,而是她不允许家里藏着多余的避孕套。谢意嫌免费发放的避孕套不好用,产地桂林,厚硬,干涩,像隔着厚厚的包装纸吸吮冰棍。有一次,他擅自从药店买了一盒超薄型,试图偷天换日,暗渡陈仓,但刚接触便被姚芳察觉了。气味不对,感觉不对。性事嘎然而止。
“我们的日子远没有富裕到花钱买避孕套的程度。凡是需要花钱的夫妻生活,都是铺张浪费,都属于败家行为。”姚芳严厉斥责谢意,并要求他把花钱买来的避孕套退回去。
第二天,谢意拿着拆封了的避孕套垂头丧气地回来。姚芳拿着它向四合院的人推销,哪怕挽回一半的损失也是值得的。但他们都拒绝了她。因为他们也舍不得把钱花在一项本不该花钱的事情上。最后,老馆长替谢意出了一个主意:把避孕套卖给看毛片的人。此主意甚好,谢意以三张票的价钱卖掉了避孕套。但此举启发了他,为他带来了麻烦,先暂且按下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