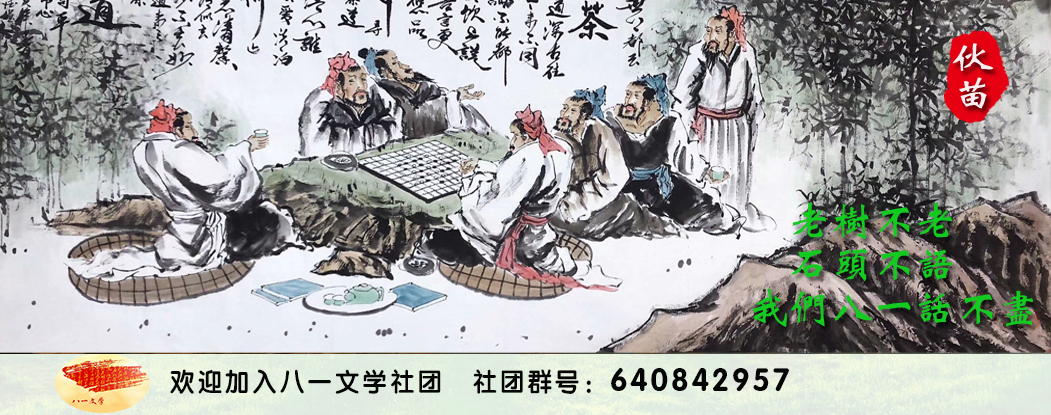【八一】山腰里的村庄(小说·旗帜)
【八一】山腰里的村庄(小说·旗帜)
![]()
一
山,如墨染的屏,一幅接一幅,万种娇情千姿态;山,如江河的浪,一坎又一坎,此时起来彼时伏;山,如护城的墙,一堵挨一堵,露岀了锋利的齿;山,如盘踞的龙,一条并一条,扭着腾飞的身躯;山,如泥捏的畜,像牛也像马,供奉先祖和天地。
村庄筑在山里的山腰上,围着渗和茅草夯出的黄泥墙,打着自家土窑里烧出的青砖和黑瓦。那房屋,东一间,西一栋,头顶的,是祖宗传下来自从盘古开天地开出的天,脚下的基础,也是自从盘古开天地开出的地,间间都是汉唐的风,栋栋都有宋明的俗。如果说,大山是山民的魂,那么,他们就是山魂繁衍的灵。
山里的坡陡谷也斜,缺少蓄水和平地,挨着泉眼处,抠出一方水田种大米。那稻田,像木槌,像镰刀,像弯月,大块只有几米长,小块也就是插上十几株秧,一顶斗笠盖住了,不留神,叫人点数准忘记它。从春到秋收两季,打下的谷子,若是家中人口多,养家糊口还困难,一桶米饭蒸下来,地瓜丝、木薯片、山药块,还得搭配七分半。
山里人平日向大山讨生活,砍伐大树放下山,卖给山下做生意的木材商。商人把木头编成排,连接起来如长龙阵,捎排工号子在群山里荡,那木伐,顺着金山江,放到山里人没有去过的它乡。山里人换来的银元,除了油盐酱醋和买米,还得省下压箱子,急用时,才好把柜底翻一翻。盖房子、迎婚嫁女、过年全家大大小小添件新衣裳,或是有个头痛脑门热,遇到这些烦人的事,没有钱,会让人的脸色很难看。
山里人,怕下雨。山里头都是黑黑的地皮黄黄的土,下雨时,那些泥巴像被老天爷翻揽拌,一脚陷下去,粘腻腻,半晌才得拨岀个窝。这天气,什么活计也做不了,只好懒懒散散呆屋里,有时一泡就是二、三旬,守着一扇门,盯着一口窗,看山,看雨,看着那天黑了亮,看着那天亮了黑,看得人们腰酸背痛浑身不自在。
二
香菇客来到大山中,和山里人一样靠山吃山讨生活。夏季里,专找那些会长香菇的倒木,一根一根扛到山的背阳处,锯成一截一截的木段,齐整整,一堆堆,架成方方正正井字型。入了冬,他还是把那些不能长香菇,山里人当劈柴也看不上眼的倒木往山下搬,送到打好的土窑烧木碳,等待来年春天派用场。
香菇客,跟山里人唱反调,雨水足,那些码好的段木堆里,那些漫山遍野捡不完的倒木上,香菇才会猛劲冒。这时节,只有他穿件盔甲似的棕衣,头顶锅盖般的竹笠,一根扁担穿着两只大篓筐,出没在青山绿色的林子里,采摘那些仗着雨水天,在断木、倒木、枯木树皮上争相抛头露面的香菇,非得待到天色暗,才肯回到草棚来。
香菇客的草棚搭在半山脊,向阳、干燥又透风。柱子、横梁用的是大毛竹,棚上架着一层厚厚的茅草,棚顶尖又陡,叫苍蝇飞上去也站不住脚,更别说是那滑溜溜的雨滴。草棚有两间,一间是焙房,正中挖出长方形的浅坑,上面架子上摆着几层竹片打编的筛子。这坑是火塘,烧木碳,焙香菇不能用柴火,若是串上烟熏味,香菇的卖价就要打折扣。挨焙坑不远,垒砌的三块石头上安放一口大铁锅,下面可以塞柴枝,焖饭、煮菜、烧水,全凭它。另一间,怕返潮,离地一尺高,平平整整地铺着一节节锯好的小杂木,焙好的香菇拿麻布袋装好后,一口一口地码上方。还挤出一块小角落,打着的草蓆底下垫着干稻草,算是香菇客睡觉的床。
在山里做活计的山里人,晌午时分歇脚时,都会找个附近人家讨碗粗茶解个渴,或借人家灶台热一热棕叶包裹着的冷饭团。香菇客的草棚,经常有人来,有时就像约了伙、结了伴,一来就是好几拨。他们图的是放肆,不拘束,说说闹闹玩得开,香菇客是外乡人,本地人的讲究在他面前没忌讳。
香菇客是外乡人,翻过好几座大山才是他家乡,拿手比划不很远,行走起来也是几天几夜的路程。刚开始,还有人知道他姓名,后来,不知谁叫了第一声“香菇客”,大家都跟着喊开了,再也没人问他姓啥或名啥。
香菇客吃透一个理,岀门在外,远近大小也管叫走江湖,一双眼睛还得学会放得亮。他在家,人来了,客客气气地招呼,烧锅喷香喷香的香菇汤,让他们用好饭团后洗洗肠。走时候,也是笑脸相送到门外,会吸烟的,往你口袋里塞上一撮土烟丝。若不在,焙房门也从来不上锁,屋内,三块石头立起的灶坑旁,放碗香菇干,摆盒洋火柴。门口的木桩上,还置着土瓷壶,壸嘴上套着一节竹筒子,壶里盛满冲泡好的茶水。
山里人,奇怪那摆着茶壶的木桩,在户外立着好几根,不喂牛不养羊,谁也不知道香菇客打在地里做啥用。当座墩,半个屁股也挨不着边,那么高,更没人愿意爬上去没事找事耍。
山里人,朴实憨厚性子直,谁敬我一尺,我敬谁一丈。这些年来,香菇客与山里人没有拌过嘴,更没动过粗,山里人把他当作客人待,谁家遇到有个红喜丧白事,座上宾上还少不了他。
转眼雨季又要到,今春香菇客倒是犯了愁。山里人都长成一个倔脾气,宁愿饿着肚子也不肯看着别人的脸色来下饭。谁家有事,大伙你帮我来我帮你,不拿人家一毫一厘的工钱,谁也忘不了欠了谁家的情。山里人还是家乡宝,更见不得有人下山到大户人家做长工来打短工。
前几年,香菇客是找兔歪子来帮忙。兔歪子,一人饱,全家饱,一人饿,全家饿,山里头名付其实的光棍汉,才不管什么脸皮和面子。一到雨季他就没地方浪,那栋破烂屋顶上的灶囱头,三天两头难得见到冒青烟。若是人家把自家菜园子盯得紧,这年偷挖不到地里的地瓜,只能背贴床板,肚皮贴着背,睁着眼,数着眼睛里冒岀的金星。听说香菇客要他来帮工,只要盯着焙坑里的木碳,不要熄火也别太旺,管酒又管饭,季节过了还给几块银元花。这等好事,他心里还来不及想,脑袋已经鸡啄食般忙点头。去年冬,山下的山货客上山收香菇,香菇客忘了收好他们丢下的十几块大银元,兔歪子抽个空档摸走了。到现在,整座大山还看不到他的影。
山里人看到香菇客急着要找人,帮他介绍李婶来帮工。李婶上山来,实话实说对香菇客讲,她家两个媳妇一前一后都生了娃,早上还得忙着家里的活,只有下午才有时间来帮他。李婶见香菇客皱起眉头又犯愁,拿嘴努了一把不远一户人家岀主意,要不找她来帮上午的忙,这两年都没见她添过新衣裳。
李婶家里大大小小有一窝,她不想和银元过不去,能得一块是一块,人穷时,苍蝇的爪爪也是肉。
三
李婶说的她,住在香菇客草棚山脊脚跟头,挑高往下探,房子、院子都被放小了。这户人家,进了大门,正对着两层高的木楼,院子两侧,两排平房相对着,耸起烟囱那边,做厨房和饭堂,另一边,是堆劈柴农具和杂物。围墙四周菜地里,稀蔬地种着的果树像风景林,有柿子,桔子,板栗和石榴。二楼还挑岀了走廊,阴天时,可以摊凉衣服和被套。前几年,入冬后,还看得到屋檐下挂着些需要风干之类的食物,如一条条的腊肉,一串串柿饼和红红火火的问天椒。
其实,这户人家,现在已经没落了,若大院子里,只居住着一位小寡妇,小寡妇名字叫山兰。人们都说嫁过的女人就是花儿也会褪了色,如果山兰没把漆黑的头发绾到后脑勺,标志着是有过男人的妇女,那丝毫不走形的身段,那如羊脂般泛光的肤肌,叫人看去,准以为还是没出过阁的黄花女。
山里人都晓得,山兰嫁过两个郎,而且两个男人都死了,都是死在她过门后没几天。
山兰娘家在大山更山里,上面有个哥哥是天生的哑巴,快三十了还没讨成亲。经媒人撮合,她一咬牙,为了哥哥的婚事,和第一个男人家里换了亲,男人的妹妹过门到她家。凭良心,这门亲,委屈的是她小姑子,山兰倒不亏。男人虽然穷,人老实,也本份,不缺胳膊不缺腿,只是家中劳力少,起早摸黑也挣不来钱。成亲那晚,挑去红头巾,见到男人的模样,山兰的心还如小兔般,“砰、砰”地跳了好一阵,庆幸自己命好嫁个如意郎。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小俩口日子还没嚼出味,一个深夜里,男人半夜起更,在茅厕旁,摔个大跟斗,无病无灾地走了。凑巧的是,男人的妹妹嫁给哑巴哥哥没大半年,也是半夜起更碰到鬼,无缘无故地小产,身下摊着一大堆血水,这可是一尸两命的横祸。
山里男人说话粗,只要女人不在场,口中无遮挡,什么事儿也敢掰。都说山兰属白虎,隐私之处是块大白板,硬把她男人克死了。这些话,都是从兔歪子嘴里溜出来,他说得是有凭又有据,不能不让人相信他。
兔歪子鼻沟豁开一条长口口,整个嘴巴如被人拧过般,扭向左边斜着放。人人都说五观不全的人心事歪,这话按在兔歪子身上一点也不委屈他。他见到女人就像中了风,抖着手脚晃着身,一双兔子般红红小眼珠冒出的邪火,专捡女人身上不该留目的地方瞅,盯得人家浑身上下不自在。平日里,山里姑娘媳妇见了他,都要绕着走。他也不敢太放肆,只是沾些眼睛和嘴巴的光,他知道,山里人见不得调戏女人这等下三滥的事,惹人恼了,打断胳膊腿儿也白搭,那冤那屈无处喊。
在山里,谁家娶媳妇,兔歪子准是不请自来到,那心情,比捡到金元宝还高兴,如一只馋嘴的猫,吃不到鱼,还能嗅嗅鱼腥味。闹洞房那一夜,就算对人家小媳妇有些出格的举止,主人家咬牙切齿也不能拿他来翻脸。山里人,新婚夫妇三天无大小。闹洞房,只要不把人家媳妇拐跑,动手动脚,讲些酸话疯话,主人家还生不得气,否则,夫妻俩往后日子不和睦,闹个鸡飞狗跳悔青肠子都无处怨。
山兰闹洞房那夜,突然刮起一阵好大的风,愣是把插在土墙上挂着的洋铁皮筒子里的松明火把吹熄了。本来怀着一肚子坏水的兔歪子,借着几分水酒劲,挤到新人旁,冷不丁伸岀鸡爪似的手,朝山兰身子摸过去。这一次,他可没有讨到好,黑暗中,不知从哪起一腿,朝他裤档飞过来,把他踢翻在地下。他扶着墙根回家后,整整是躺了十天半个月,胯下的命根子都险些被废了。
山里人,嫁出去的女儿泼岀的水,无论在婆家受了什么委屈,或有什么大变故,别指望娘家人出头当靠山。嫁鸡趴鸡窝,嫁狗守狗洞。命苦的,男人死了,若有一儿半女,还得为婆家传宗接代守寡一辈子。要是男人没留下种,二年后,婆家会把媳妇当作女儿来相待,待到找到合适的人家,收了聘礼,再把她嫁出门,娶媳妇这笔份子钱还得捞回来。
男人死后,山兰整整守了两年寡,经媒人撮合后,又说给现在的人家。这户戚姓人家花钱娶回这门亲,更多心事是拿它来冲喜。他儿子比山兰整整大十岁,虽不傻,却犯下浑浑浊浊的痴呆病。听说以前不是这个样,还在山下私塾里上过几年学。就是因为读了书,识了字,才不把山里的女孩放眼眶,喜欢上山下的姑娘,但人家姑娘却瞅不上他。回到山里后,自家的门坎再也没有迈出过,整天介日里,有如丢了魂来失了魄。
山兰这回更命苦,结婚那晚,吃完宴席,要送新人入洞房,新郎倌却不见了。好几天后,人们才在山头的林子里找到他,死在一块岩石边,身上不见任何伤和痕。山里人有规矩,男人死了女人在,都由自己女人为他擦净身子换衣裳。山兰这回可是留了心,就算自己再晦气,同样的事儿也不可能莫名其妙来两回,这回她可仔细了,果然在死去的男人身上发现了奚巧。
祸不单行,不到二年的时间,公婆也撒手走了。公公临终前,拉着山兰的手,叮嘱道,这若大的宅子就传给她,求她招个男人上门来,生下第一个男孩随他戚家姓,别断了戚家一代接一代传下来的香火。
自从公婆过世后,山兰是上没大来下无小,就算偷个男人养个汉,山里人除了茶余饭后多份聊天的料,这闲事不会有人出头管。山兰不是那号人,偷鸡摸狗被人指着着脊梁骨骂破鞋的事儿做不出。但孤苦零丁的日子熬得苦,哪个女子心甘情愿辜负青春好风光,她也想正儿八经找个规规矩矩的男人成个家,偏偏是,再也没有媒人上门来招惹她。
哪个地方都不缺骚公鸡和馋嘴的猫,盯着山兰看的不少,想去碰她的人也只能在心里想,因为她是白虎星,山里头的一枚刺梨儿。男人虽然嘴巴硬,说什么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真的要去送性命,十有八九还是不乐意。
四
山里头,杏花开了,梨花开了,桃花开了,还有那些叫不出名儿的野花儿也开了,粉粉红红,雪雪白白,一丛丛;紫紫蓝蓝,浓浓淡淡,一点点。叠缀在葱茏的山坡和山头,一座座大山都添换了新衣裳。
山里头,雨水也来了,一茬接一茬,把整座大山浇个透,山上的断木上,香菇客伐下的段木里,树皮开始腐烂,香茹钉钉一点一点地往外冒,黑褐褐,毛茸茸,宛如一把渐渐撑开的小油伞。
前阵子,香菇客听了李婶的主意,思来想后也只有这么办,他让李婶跟山兰去说说,看看她是否愿意来帮忙。香菇客在山里呆了好些年,偶尔和山兰也打照面,两人仅仅只是端起眼角瞟一瞟,算是招呼过去了,几年来,谁也没跟谁搭过腔。香菇客不想去招惹那份腥和臊,让山里人没事编排起事儿来,谁也知,寡妇门前是非多。
村民放下个人恩怨,一致抗日,很有政治意义!小说描写细腻,脉络清晰,人物生动鲜明,很有文学意义!
祝阿泥老师生活愉快!佳作不断!o(* ̄︶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