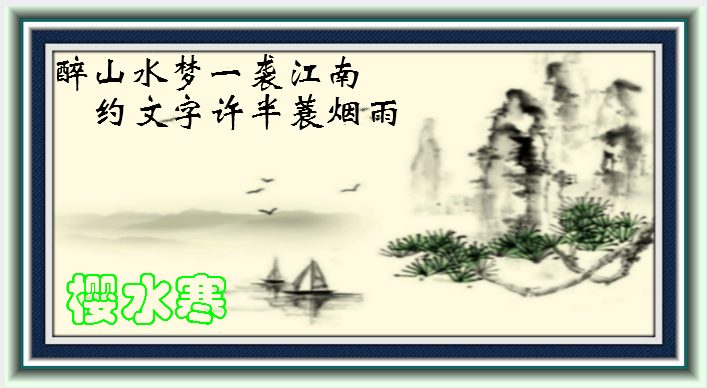【暗香】此心安处是吾乡(散文)
【暗香】此心安处是吾乡(散文)
儿子快开学了,趁着假期,我们携两宝回到了查干台。这个时节是查干台最舒服的季节,天气不热不凉,地里的麦子还未黄,不用忙农活,父母也闲在家里。我们赶到时,父母亲已做了一桌子的家常菜,炉火烧的通红,母亲说,怕孩子们受冻。
次日清晨,老公带儿子去爬山,他和我一样,都是山沟沟里长大的孩子,自然对一草一木都充满着感激与怀念。我起床时,母亲已揉好一大团面,说要给我们烙油饼,说今年新摘的香豆昨天已晒好,父亲抱着我的小儿在院子里转。
父母亲是去年搬到县城里的,但他俩并不习惯待在楼上,过了一个冬天,又“跑”到这里了。这里舒服,他俩待了一辈子了,说哪里都没有这里好。年初的时候,政府拆除危旧房,父母亲担心了好一阵子,怕老屋会被拆除。我们仨异常淡定,安慰母亲,拆就拆吧,你俩又不是没地住。母亲嘴上附和我们,但那神色却明显暗淡了。
儿子爬山回来,一脸不悦。他害怕各种虫子,莫名害怕,我亦无法理解。对于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我来说,一切都是熟悉而美好的。
母亲的院落荒废了,多年以后,再次回到这里时,我们都有了自己的小家。老屋的土坯墙早已被岁月腐蚀的不成样子,屋前父亲的磨坊已拆掉了,但是屋后的老树还在,草木依旧,鸟鸣声依旧。儿时我种的那棵杏树还在,倚着老屋的土墙,树上零星挂着些果子。母亲的大理花去年冻坏了,石竹花开得正艳。母亲说,人是最不耐用的物件,人不在了,草木依旧在,所以我们说草木有情。
饭后带儿子去摘酸刺果果,去田间地头转转,去村东头的杏树上“偷”杏子,给儿子讲述我的童年趣事。那些熟悉的草木都在。指哪些山头上我曾留下过脚印,给他指那些年读书时常走的捷路,讲那些年读书的不易、生活的不易,他倒听得津津有味。
挨着老屋的是查干村文化广场。多年以前,这里还是查干的村级小学,朗朗的读书声,能传遍整个村子。如今,只有闲叙的老人和玩耍的孩子们。老人都是看着我长大的,都能喊出我的小名,玩耍的孩童,好奇的眼神,大有“儿童相见不相识”的味道。
家乡的变化很大,我也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查干台”变的生分了。或者,是从我离开这里上高中起,又或者,是十年前,从我出嫁的那天起。每每回来,都是匆匆一别,顾不上到处转转。光阴真的是特别奇妙的东西,也特别可怕。它会让一些美好的事情沉淀在岁月深处,成为过去;也会让一个天真的孩童变成一个世俗之人。
走到“牙豁”里的时候,看到新搬的住户,二妈家旧房子的墙还在,门口的花椒树和杏树已不在了。
我记忆里去二妈家的那个坡特别陡,或许是我已不在年少,又或者是坡真的变了。小时候,胆子特别大,冬日的夜里拿着书本去问二爹问题的情景,依然在目。记得尕姐姐戴着的厚厚的“通袖”,记得教二妈写字的情景……而今,他们都在遥远的新疆。于是,把随手拍来的美景图片发给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大妈家的房屋已没有任何痕迹,取代它的是崭新的养老院,白墙红瓦。记忆里大妈院落里有一株“棉豆儿”,结白色的果、黑籽,似棉花糖般的柔软,个不大,和野樱桃一般大。据说是大姐姐从山里移植来的,如今已不见踪迹。
家家户户的院落都有了新面貌,但有些记忆深处的东西,是岁月无法抹去的。路边的、山头上的花花草草,都是我熟悉的,连草的味道都是我小时候的那个味道。一一都能叫出名来,记得第一次吃“猪耳朵—车前草”的情景;记得挖野蒜的场景……我以为有些被我忘记的东西,其实,只是被我珍藏了。那些深埋在记忆深处的琐碎,关于草木、关于亲人,都与这个地方息息相关。
特别奇怪,回到这里,吃饭也香,睡觉也安。突然想起苏轼的一句话“此心安处是吾乡”。多年前以为有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如今又有了新的理解。一所房子,没有父母,就没有家的温度;一个地方,如果没有成长的记忆,也不是故乡。
所有的人都去午睡了,父母亲也睡了。他俩真的老了,操劳了一辈子了,就在睡前母亲还在为早上烙油饼忘记放碱面而自责。我一个人在院里兜兜转转,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许多回忆涌出,变成眼角的星星点点。就是这个地方,我从小无数次想长大、想逃离的一个地方。如今回到这里,全是怀念与感激,感谢父母,感谢父老乡亲,感谢这里的一草一木,带给我的温度。让我长大,让我成为现在的自己。
夜晚,查干台安静下来了,只一两声狗叫声。睡觉的时候未拉窗帘,一轮明月高挂在窗前,静谧而美好,都说“月是故乡明”多年以来,仅没有这样好好赏过月色。没有比较,窃以为这便是世间最美的月色了。
感谢老师分享美文,祝您写作愉快!
遥握、敬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