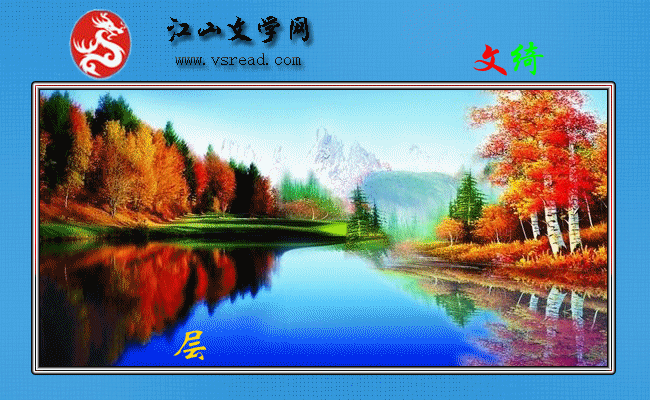【轻舞.秋韵】碗中道离欢,盘里有春秋(散文)
【轻舞.秋韵】碗中道离欢,盘里有春秋(散文)
说到碗,自然会联想到可口的菜。脑海遐想秋色,习习秋风、落叶、硕果都随即浮现眼前。这些都是人的思维意识形态下本能的条件反射。
记不得某天何故去了一家规格较高的食府。服务员满脸春风热情洋溢地将十几道菜端上旋转的餐桌,豪华的包厢已是满屋生香。在被美味佳肴诱惑了我的味蕾前,那些形状不一的菜盘倒先吸住了我的眼球。肚大腰圆是盛汤用的,叫汤钵,或叫陶罐。酒精炉上一口扁平的锅被淡蓝色的火苗炙烤着,嗤嗤地冒着香气。菜盘有方形、棱形、荷叶形、鱼形、月牙形,林林总总。依据各式的菜盘配上相宜的各种色调,菜盘倒也增添了不少生动的质感。佩服制瓷艺人竟有如此心境;折服厨师依据不同的菜谱,而选择什么样的菜盘盛菜。荷叶粉蒸肉摊开放在荷叶形状的盘里,盘子四周摆上几片薄薄的生藕片,加上盘子上浅绿色的底,这道菜有荷塘蓬莲逸清香的雅致。一尾西湖糖醋活鱼正在鱼形的盘里张嘴翘尾,让我莫名地难以动筷食之。“人靠衣裳马靠鞍”,这句老话在他们的经营理念中,运作得如此玄妙。这些生意人捕捉到了客人的心,通过视觉就让人有了食欲。当然,最终要靠“作品”说话,必竟众口难调。
每年的春节前夕,母亲都会给家里添置些新的碗盘。图个人丁兴旺,家合万事大吉。这句话,母亲唠叨了一辈子。在母亲心里,添置新碗盘是件大事。新年新开端,新年新起色。这是母亲的愿望。
母亲不会去价格偏贵的瓷器专卖店里购买碗盘。用她的话说,碗盘是用的,不是去看的。那些手感光滑、图案精美、釉质讲究的碗盘入不了母亲的眼。相反,母亲专挑些光泽一般,没有花俏图案,手感厚重的碗盘带回家,即便这祥,还时常叹息,怎么现在的碗盘都这么花俏,拿在手上没有啥重量,和早前的是没法比喽。母亲的想法和做法怎么这么土气?都什么年代了,哪还能寻见过去她说的那种样式简单厚实的碗盘。我很疑惑。
某天,父亲对我说了一席话,我这才幡然彻悟,方知母亲为什么对碗盘有这种情结。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婆家和其他庄户上的人家一样,贫困的家庭没有啥好物件,除了耕地所必须的农具,大到耕牛、打谷机、风车、犁耙、晒谷垫,小到镰刀、土箕、箩筐、锄头,这是农户人家的命根子。每户家庭按照人口添置碗盘,几乎没有多余。说来说去都因为穷。碗没有什么大小之分,大人和小孩都用同一规格的碗。喝酒、喝茶、装饭、盛汤,都用碗取代。碗和盘子的焙烧及制作工艺较为简单粗糙,碗盘都很厚实,清一色的白颜色,然而白色却又泛着黄。碗和盘子的表皮麻麻点点,疙疙瘩瘩,摸上去硌手。这些碗盘是烧制过程中的次品,在市场上的销售价格相对正品便宜许多,为了剩两钱,这些次品成了庄上人家的抢手货。这样一来,家家户户的碗盘几乎都一样,难以区分。
日子再怎么苦,过年之时,外婆都会去集市买上几个碗盘回家,又把新碗盘浸泡在热水中煮上一阵子,这一做法的目的是除去碗盘体内含有的有毒的化学成份。而后,舅舅会拿着尖錾在碗盘底部轻轻凿出一个个圆点,凿上名字中的最后一字。外婆所在的庄上大多姓张、赵、邓、李的姓氏,只能凿上名字中最后一字区分。外婆的丈夫离世很早,她的五个孩子只有舅舅一个男丁。舅舅小心翼翼地在碗底凿上一个又一个“平”字。
每年庄上遇上谁家红白喜事摆桌设宴,显然家中碗盘是不够用的。这些人家就会挑着箩筐挨家挨户去借碗盘、桌凳,谁也不用担心归还之时会还错这些东西。借东西的人家客客气气地给借出东西的人家散着香烟,请他们前去喝酒。借出东西的人家客气地答应下来。饭桌上的碗盘底五花八门的字,让大家瞧见倍感亲切。这种借碗盘的习俗至今保留着。在碗盘凿字的习俗已不多见,现在农村各自家中的碗盘样式都不一样了。
庄上的人家很珍爱家中的任何东西。碗边缺了口,换个地方吃饭,喝酒。盘身裂了缝,只要不漏,继续用。
舅舅是家中唯一男劳力。采石、挖山、伐木、砌墙……所有的重体力劳动都是他干。每次疲惫回家,外婆都会给舅舅倒好酒,给他盛饭。外婆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舅舅身上。
舅舅用的碗很容易认出,碗边缺了两口子。一个口子是三十多年前,他结婚给大家伙敬酒,高兴时与客人们碰碗碰缺的;一个口子是他婚后几年,他的小儿意外溺水身亡,喝闷酒磕缺的。小儿的意外离故,给舅舅带来极大地打击和悲痛。很长一段时间,舅母不怎么理睬外婆,更多的是怨恨。
事发那年是盛夏,舅舅夫妻俩外出揽活,外婆一人在家中忙家务。因为天热,两个年龄尚小的孙子背着外婆,偷偷摸摸地去河里玩水。孩子们哪知水火无情啊,稍小的胆子大些,先下了水,最终因不会游泳而被淹死。事发的几年里,外婆没有去辩解,全身心地照顾舅舅的大儿子,仔细打理家中所有的家务,生怕再有什么闪失,疏漏。外婆仍然如初地给舅舅倒酒,盛饭。看似平静地生活,没人知道年迈的外婆心里的苦。
又是一年盛夏日,农村的生活好了许多。
舅舅晌午回家,不见外婆在家中。寻思,外婆去喂猪,去菜园子浇水摘菜。正想着,舅舅闻到家中刺鼻的农药味,这才发现外婆喝农药自杀。外婆选择了决绝的方式离开了大家,常期的压抑,她的心理彻底崩溃。当时,外婆的床上放着一个碗,那碗边缺了两口。
出殡送外婆上山下葬那天,舅舅在坟头啜泣:娘啊!其实我知道您给我换了新碗,我都知道……坟前,那个缺了两口子的碗盛满了白花花的米饭,三柱香插在上面,燃烧的香灰默默地低下了头,一段段,无声无息地掉进碗里。
九四年,我结婚那天,母亲送了一套碗盘。盘子的边沿有蓝色的花边,碗的四周有菊花。这些用了二十多年的碗盘所剩不多,不小心摔碎,磕裂的,留下的至今也存放在家中。
我喜欢看碗盘里绘制的彩釉图案。一尾鱼、一荷花、一蔬绿……飘逸出自然古朴;我更爱过去粗陋简约的碗盘,有回忆的味道,有情感的凝结。
一个碗,承载着母亲的挚爱,道尽人间离欢;一个盘,种有春秋,希望生生不息。我深深地理解母亲,更会去深深地怀念外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