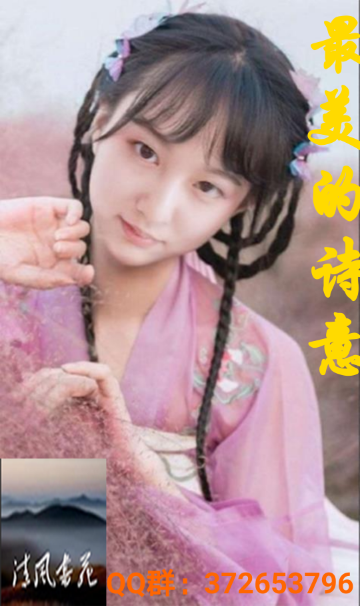【宁静•守】父亲的城堡(散文)
【宁静•守】父亲的城堡(散文)
![]() 一、黄土堡子里的童年
一、黄土堡子里的童年
我的父亲出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的西北农村,他坎坷而跌宕的七十多年岁月里,目睹过旧中国的破败,感受过新中国变革中的阵痛,经历过土改文革的凌乱,见证过家庭兴衰起伏的波澜。在食不果腹的日子里度过了他所有的童年、少年、乃至大半个中年。在日新月异的新中国里,成就了他“一生戎马”的天下。
在上世纪早期的西北农村,因社会治安的败落而导致民间整日匪患猖獗。村民们在夜间担惊受怕自不必说,即使是白天里,也是在提心吊胆,战战兢兢中想方设法地护佑着家人的同时,在山野之间寻找可以果腹的东西。因此一些村里有点家底的农户,会自建“堡子”,以挡“外敌入侵”。
“堡子”一词的称呼,属于西北方言,其实就是民间的具有防御性质的城堡。堡子的四周,用黄土夯起高约三丈,厚约三米的城墙,然后在城墙内建房箍窑,设栏为圈,一家老小,以及所有的牲畜、家当,都在堡内居住安置,待夜幕降临,便卡上堡门,如此一来,一般的小盗小匪,即便打到堡下,也只能望堡兴叹,无可奈何。在那个风雨飘摇,匪盗猖獗,饥不择食的年代,这样一座纯粹用黄土夯筑起来的堡子,往往会是一个家庭,甚至一整个村子的村民与牲畜,在面临外来威胁,甚至生死关头时的唯一避难所。
我的父亲就出生在这样一座我们村里唯一的堡子里。
父亲在兄妹五人中排行老四,上有一位哥哥两位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幼年时的父亲因家境尚可,也算过了几年难得的好日子,这点单从拥有村里唯一一座堡子这点便可了解一二了。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座多年来庇佑全家乃至全村人的黄土堡子,在随后的土地改革和打倒地富右的政治浪潮中,让全家人吃尽了苦头。家里仅有的一点家底儿都被洗劫一空,土地全部充公,牛羊牲畜全部上交,同时全家被戴上了富农的“高帽子”,一家老小从此低人一等,矮人半截。
进入少年的父亲,因家庭成分的牵连,仅仅上了三年完小,就被大队领导从学校拉了出来,成了当年生产队里最年轻的劳动力。从此,父亲用一双稚嫩的手,开始了他整整七十年的农民生涯。那座黄土夯打起来的、经历了数十年时代的洗刷,庇佑过全家乃至全村几代人的城堡,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让全家老小,乃至已经嫁出去的女儿在内所有亲人都抬不起头的土城,父亲也从此结束了他被那座堡子庇佑的少年时代,结束了他短暂的童年。
二、苦难岁月里的“城堡”
我的大伯因赶在了那个“运动”的前面幸而完成了学业,到父亲被辍学的时候,他已经顺利端上了令全村人都羡慕不已的铁饭碗,有了可以坐在办公室就能拿到钱,并领到高过父亲好多倍工分的工作。但是因为爷爷奶奶依然担心大伯一人在外吃不好穿不暖,所以父亲遵循爷爷奶奶的心思,在大伯初始工作的那些年里,也是家庭最穷困的几年中,每周都笈着草鞋,翻山越岭步行几十公里,将家里仅有的那点细粮送给城里工作的大伯。
年迈的爷爷奶奶自从被戴上了“帽子”开始,便过上了牛马不如的日子。白天空着肚子被赶着下地干活,劳累到天黑后,再空着肚子被捆在树桩上接受“人民大众的批评教育”。劳累、饥饿、加上精神上的无限打压,使他们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彻底垮掉了,面对如此灾难般的境况,父亲成了家里唯一的顶梁柱,将十几口人的家庭扛在了自己十几岁的肩膀上踽踽而行。
父亲如此清贫艰苦,低人一等的生活,开始于血气方刚的少年时代,直到包产到户的曙光正式照进西北大地为止,才算有了历史性的改变。彼时,父亲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早已脱去了少年时代的稚气和锐气,成为了一名恰如路遥先生笔下那位勤恳善良,忠孝厚道的孙少安一样的纯纯粹粹的农民。不过这里所说的结束,仅仅是精神上的结束而已,但即使只是精神的解脱也足以让遭难的人们如释重负。摘掉了戴在头上整整压了二十多年的“富农子女”的大帽子,就这一点,对于当时的父亲来讲,已经好比卸下了顶在头上的巨大的石头,终于可以抬起头做人了。此后的生活虽然依旧清贫艰难,但也不至于忍饥挨饿、受打挨骂。精神上的解放,算是父亲人生中第一次挺起了胸膛,这对于和父亲那一代有同样经历的人来讲,绝对算得上是一种里程碑式的变革。而在过去这三十多年艰难的人生里,除了家人的扶持之外,还有一个人,用她矮小而稚嫩的肩膀,自始至终陪着父亲一同扛着这个家庭走过了她整个青春年华,这个人,就是我的母亲。
母亲,是父亲失去了童年那座黄土夯起的城堡后,在青春年华伊始的时候,便住进去的又一座无比温厚而踏实的“城堡”,这座始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爱情城堡,庇佑了母亲和父亲斑驳平凡而温情款款的一生。
三、携手共建的城堡
母亲年长父亲一岁,和父亲的出身一样,母亲也出生于一个富农家庭,这在当时“成分”和“出身”至上的年代,同样的出身,戴着同样的“帽子”,受着同样的苦难,如此“门当户对”的结合,我想也算是一种必然,更是一种天作之合。
其实我的父母亲在幼年时开始,就因两方长辈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就时常一起玩耍、相互串门,所以这也称得上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母亲是姥姥姥爷唯一的女儿,因此自幼颇受家人宠爱,七八岁的时候,姥爷送母亲去了县城的完小上学,希望能认识些字,将来不至于像他们一样做睁眼瞎。但因为实在无法忍受离开姥姥的那一片温暖的大衣襟而需要夜晚独自一人在学堂睡觉,母亲在三日后的晌午,便抱着步行三十多里地、特意前来看望她的姥爷的大腿,在一场歇斯底里的哭喊声中,被姥爷背着带回家里,从此结束了仅仅三天的学生生涯。
母亲自从上完了她的三天完小之后,便整日在家帮助姥姥做饭浆洗,侍奉长辈,直到十六岁那年,以一个枕头般大小的包袱做嫁妆,骑着接亲的人牵着的毛驴,嫁给了六十多里外,年方十五岁,已是家庭顶梁柱的父亲,从此便开始了早晚侍奉老人、餐饭浆洗,白天刨地挖土,干着同男人一样的,永远干不完的粗活重活。赚取工分有母亲的份儿,侍奉老人更是母亲的义务,但不论里外,都无疑为父亲分担了太多原来父亲一人承担了多年的重任。父亲和母亲的结合,以一种最简陋的仪式作证,然后以同甘苦的方式拉开了他们六十多年荣辱与共的人生序幕。
父母生我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了,我是他们的老儿子,对于父亲年轻时候的苦难经历,实际上我知之甚少,仅有的一点“历史资料”,也是长大后从父亲的口中断断续续得知的,比如父亲被派往百里之外用架子车拉石头而彻夜独自赶路于荒郊野岭;比如面对奶奶重病急需送医,父亲在半夜里试图向他的晚辈借一把自行车而被对方堵在门外;比如为了完成大队的任务而抹黑赶路而掉下悬崖,比如得知年方十九岁的儿子被塌方压碎了脊椎……
父亲的生活里,经不起一点细细地盘算,否则唏嘘和泪水会让人彻夜难眠。我不知道,更不确定父亲在那些煎熬的日月里是否有过丝毫想要放弃的念头,我仅仅能确定的是,我的父亲在那些阴晦茫茫的年代里,经历了晚辈们所无法想象的苦难岁月,而这些仅仅靠着口口相传,或者我的这半截烂笔头,所能表达的何止沧海一粟,更何况,父亲压根就不想让他的孩子们了解太多关于他和母亲的那段过往。从父亲与母亲结合之后二十年中,在属于他们的所有的青春岁月里,他们执子之手,一同侍奉三位长辈,使他们在岌岌可危的环境中得以安度晚年并酣然离开;他们并肩携手,养育出了使他们值得自豪的儿女,并托举着使之一个个振翅翱翔于蓝天白云之下;他们憨厚善良于所有的亲邻廊下,馈以微薄之力,然后无所欲求。也许这是很多很多平凡的父母所共有的历史,相似的特点,所以才有了父爱如山,母爱似海的说法吧。
我是兄弟姐妹中最后一个被父母用他们粗糙的双手抛出去的“雀儿”,然而我恰恰又是他们最晚熟的一个孩子。可能是从小被父母宠爱有加,加之上有兄长姐姐们呵护,所以时至今日虽然我已经年近不惑,但对于家庭责任,对于父母孝道,我承担的和做到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实际上我是从近两年才开始慢慢反思,反思我对于父母,对于家庭而言,自己的存在感在哪里,我应该去做什么或者应该如何去做一个儿子本该做到的事情,至今,我得到的答案是模糊不定的。而今想想,我之前的三十多年,过得都浑浑噩噩,过得稀里糊涂。走进大学之前的那些年,以幼稚为借口,很少与父母谈心,从上了大学到后来工作,和父母的聊天都局限在电话中。
二零一五年的十一月初,是妻子的预产期,在那之前父母已经多次在电话里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他们一定会在妻子分娩之前赶来。事实证明父母给儿子许下的诺言的兑现率远远超出了儿子对父母的许诺兑现率。父母在他们的小孙女儿呱呱坠地前三周,便已风尘仆仆地从三千里之外赶来。自从到了我的小家后,从来不善煽情,不善表达的父亲,曾经不止两三回地重复着一句话:“孩子,爸妈穷了一辈子,现在也老了,所以不管是钱还是精力上,我们俩都帮不了你什么大忙了,但是有我们俩在,生孩子这么大的事,你的心里总归会踏实点”。每每听之,我总会笑笑回复父母:“你们不用帮什么,你俩在我们身边,就是我最大的安心”。实际上我心里明白,父亲的这句话里面,充满了无奈,充满了束手无策,充满了对儿子儿媳的愧疚之心。父亲无奈于他们的年纪,无奈于他们的身体;无策于他们对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的迷茫,无策于想帮儿子做点事却不知道如下下手,以及从何处下手才算是帮上了儿子,由此而生愧疚,然又不能言,我想这是许许多多质朴,憨厚的农村父亲所共有过的心情,后来我试着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我似乎感受到了父亲说这句话时的那种心情和那种言语里的万般难言之痛。
父亲在我家里住的几个月里,每天早上都会揣着钥匙,蹑手蹑脚地早早出门,待我起床准备上班时,往往已经拎着一塑料袋蔬菜从农贸市场走回来了。我也曾劝说父亲,来往市场需要过红绿灯,走斑马线,他又有腿疾,不要再去了,小区门口的大超市里啥菜都能买得到。但是父亲每每听之,都只是憨笑一下道:“我看着红灯呢,而且市场热闹,又能和人拉呱,菜也新鲜,我早上走走,就当锻炼身体了……”实际上我心里明白,此时的父亲行为,像极了小时候的我总想抢在他们之前抱着扫把打扫屋里的卫生的做法,所谓力所能及,此,恰似也。
二零一六年四月中旬,寿光蔬菜博览会盛大开启了,考虑到父母从寒冬时节到我的小家后,至今基本没有怎么出去玩过,便趁着周末,开车带他们去了寿光。博览会盛况空前,人声鼎沸,四个大展馆中各种长势惊艳的蔬菜瓜果让人眼花缭乱。也许是因为父母和庄稼打了一辈子交道,也许是久违了他们耕种了一辈子的土地的缘故,在看到那些瓜果蔬菜被培植地格外喜人后,他们的脸上似乎露出了恰似见到了久违的亲人一般的激动和亲热。父亲总是走在我和母亲的前面,带着他的茶色石头眼镜,左右观看,赞叹不已,我扶着母亲走在人群里,生怕跟丢了父亲。直到午后三点左右才从人群里挤出来,三人面对面席地而坐在树下的草坪上,香喷喷地吃了从会场边买来的小笼包子和米皮,那日,父亲吃地很香,母亲一直很开心,谈笑中看着远处草坪上嬉戏的小孩,感受着北方四月里的清风,一切都是那么柔情,温厚,惬意,心安。虽然看得出父母依旧有些意犹未尽的样子,但是考虑到他们的身体,也就只能尽快赶着返程了。
那一次算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全身心地陪他们游玩,而父亲今年的突然离世,让这种陪伴成了我一生的唯一一次。那天过马路时,父亲见母亲腿脚不好,怕是担心摔倒,便及其自然,甚至有点强硬地牵住了母亲的手,一直扶到马路对面。父亲这个对我来说有点突如其来,又异常陌生的举动,让我异常惊讶,万分意外。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父母拉手。跟在他们身后的我在惊讶和莫名的感动中,看着两位华发老人手牵手蹒跚于人流之中,那一刻,我似乎品感受了些许所谓“陪伴”的分量,亲眼目睹了所谓“执子之手”的真实与具体。这个画面,我至今没有给任何人讲过,一来我担心别人会笑话我拿着一种“司空见惯”和“理所当然”当谈资,二来,我不认为任何一个人都能理解那个牵手的背影的分量所带给我的触动。父母爱情看不到任何的粉饰,更找不到丝毫的浮夸,一切都在这种默契中,这种及时而自然的呵护中,平淡而温润地走过了近七十年的岁月。
四、城堡里的小城
二零一九年的春节,是我陪父亲度过的最后一个节日,更是我此生最后一次有父亲陪伴的春节。过年那些日子,兄弟们齐聚一堂,欢声笑语,孩子们三两成堆,嬉戏打闹。父亲则基本都是偶尔走进屋子,满面含笑,满脸慈祥地看着我们,然后围着沙发踱一圈,再背着双手再回到他的堂屋,一个人静静地端坐在靠近火炉的椅子上,一言不发,偶尔点根烟头,吸两口,再捏掉,小心地放在炉子边,聆听隔壁小屋里孙子孙女们嬉戏打闹的嘈杂声,时而抬头望着窗外,似乎再仔细听哪个孩子的话语,时而低头看着炉子里的火苗,若有所思,眉目之间看不出任何的遗憾或者欲求。每每看到父亲的这个样子,我都忍不住想,我们而今这个二十多口人的大家庭,多么酷似家门前的那颗大榆树啊,儿女子孙们都是父亲用七十年的沧桑岁月所延申出来的枝叶,而今蓬勃繁茂,翠绿欲滴,而父亲则像极了这遮天蔽日的枝叶下那根粗壮斑驳的根,在父亲仰头之间,树荫之上全是他用一生打下的天下。而今独自端坐于炉边的父亲的这种安详神情中,应该饱含着只有他和母亲才能理解的含义吧。
父爱如山,如城堡~
感人的文字,动人的真情,欣赏美文,问候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