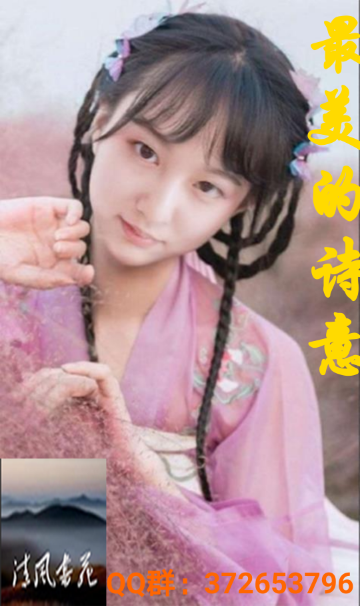【看点】惊蛰,叫醒了土地(散文)
【看点】惊蛰,叫醒了土地(散文)
![]()
一
惊蛰,是来叫醒土地的,就像晨鸡是叫醒沉睡的人。
每年,春与我有约,我去踏春,踩踩松软的土地。但今春与往年不一样了。春说,我还没有化妆好;土地说,真正唤醒我的是踏春的人,可今春的人们似乎冷落了我。珍视春色,不能放过每一春,我不能做爽约的人。我读唐诗人刘方平的《春怨》诗,总不解春会有“怨”,看来今春正怨我疏离。当下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稍趋好转,听了院士钟南山的话,只要不扎堆,踏春是可以的,我要亲近春天的土地,尽管迟到了,可怎么也要给春天一个如约。
时间,仿佛被无数灰色的云朵包裹住而不动,但还是抵不住期许和信念的光。直到有一天,那安静的时光终于被一场乍暖还寒的春雨濡湿,春雨湿润了惊蛰的雷,声音沙哑了。这是2020年春的惊蛰。
惊蛰了,我想起汉景帝为避名讳将“启蛰”,改为“惊蛰”,一字之别,修改得太妙,在路上,我琢磨着这个字的妙处,“启”,微开,似乎春病无力;而“惊”字,颇具气势,且有“我邀惊雷炸春响”之意。我以为二十四节令里最令人感动的一页就是惊蛰时节,宛若一首铿锵的诗。这首诗,都承载在醒了的土地上。
我始终觉得惊蛰的意思是,大地之下还是一个沉睡的世界,它属于百虫,其实,更属于爱春的人。
“一候桃始华;二候仓庚鸣;三候鹰化为鸠。”这是古人所描述的惊蛰三候。实在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桃花盛开的春天,实在不能缺少一个鸟鸣的春色,实在不能少了百鸟翔集的景观。那不只是不完整,简直就是失去了春之魂。今春,我心中装着这些灵魂,期待着春在土地上挥洒出锦绣。即使春没有来,我也喜欢在诗意里想着春,是妖冶桃花点亮了春,是百鸟唤醒了土地。
鹰化为鸠,也正是紫薇花开诗,那是报春的花,我耐不住这个征候,我要看春土醒来的样子。
我早就生出诗意,踏春,最好就是趁着惊蛰去倾听土地醒了的声音,看睡意朦胧的样子。和妻驱车到往年常去的虎础寺西的绕山梯田,一边挖荠菜,一边看看春来土地苏醒。
温善的春风,就像舞台上撩起的彩带,只是看不见舞女摇动春风的玉手。沟涧里聚集了一股调皮的春风,将枯黄的芦苇摇响,哦,我明白了,那就是在叫醒沉睡一冬的土地啊。弯下腰,仔细看地表,微尘已经被吹走,沙粒嵌在泥土里。春天啊,让我生出无尽的联想,这是春天土地的青春痘,年轻的土地,正要焕发出蓬勃的激情。我不能错过抚慰青春脸蛋的机会,附身捧起一抔泥土,橘黄色的土,似乎是从金矿淘出的金粒,美妙的感觉往往来自自然与朴实,人在土地上马上就有了富足的感觉,可能这是人世代无法告别土地的唯一原因啊。
正如诗人所言,我的泪水总是流给土地,因为我爱得深沉。
二
春土的味儿,似乎被春风唤出,我凑近鼻息之下,深嗅一口,就像我在医院的病榻上贪婪地吸氧。阳光晒透了泥土的萌动基因,我相信泥土是有味道的,不能以是否招蜂引蝶来衡量。泛绿的春草,返绿的麦苗,贪恋依恋着土地,一股股轻微的清香,就像点燃细细的檀香首发出袅袅的烟,我想,所谓信仰宗教的人,在神佛像下跪拜,或许就是受了这样的启迪。从春土升腾着春气,在阳光的折射下,变得缭绕扭曲,就像仙女舞动着诗一般的身段,似乎是在告诉人们,春天的泥土熟了……
我恣肆地在耕田里散步,跋涉是很艰难的,脚下踩着的土地如面包一样,春天啊,春风岂止又绿江南岸,每一寸泥土都开始承载绿色了。“数声微雨风惊晓”,难怪春土迎春苏醒。“暖着田衣饱青藜”,光照充沛的太阳走了,皎洁的月光来清照,“沐日光华还浴月”(纳兰性德句),春风,春雨,春阳,春天的月光都来唤醒沉睡的土地。我想到一个词“热土”的别解,热土,不单单指的是故乡,土地在冰冻之下,依然是热的,一旦春来,泥土就发酵,催醒了身上的每一个细胞。
我想起父亲活着的时候,几乎每日都拄着拐杖坐在自家自留地的地堰上,吸完烟,便在地上放一个蒲团,用他的小镢头一寸一寸地刨着泥土,每一寸土地上都淌过他的汗水,我想到土地上至今还浸染着世代耕田人的汗水,用汗水浇灌的泥土,不就是“热土”吗?地下涌动着热泉,并发酵着,这就是春土,所以,春土恰似面包,养活了一代代人,抚育了无数的动植物,可这又是什么样的面包房可以比拟的啊!
是啊,农人膜拜土地,即使遇到旱灾洪灾,也还为土地叹息着。我不是农人了,我用踏春,来表达对复苏的土地的宠爱,春,喜欢我爱的方式。
三
有人说,经冬的土地就会裂出口子。一点诗意也没有啊。我仿佛听到从这些口子发出了声音,饥渴而唇干,祈雨的岂止是抬着贡品跪拜“行雨神”的农人。土地裂开的口子,又仿佛是在笑,笑纳春种一粒,然后将微启的小嘴闭上。原来是土地因春而热起来,舒张了封闭的毛孔,要将金黄的黍米和艳丽的花朵插满全身,哦,人们总说春天最美好,原来春天的土地从来都是不误节令,土地上,写着生动而丰满的梦,土地至善,在于她从不厚此薄彼,无论是在土地上索取,还是在土地上耕耘,土地不计较,我想,所谓诗意的栖居,是否就是这样的境界,可以相伴而从不分离的,应该就是土地的品性,于是,我们才有了诗意栖居的体验。同时,能够从土地上刨出诗,坐下来和土地絮语,那才是真的懂得了土地,所谓“生于斯故于斯”,这才是最痴情的诗意栖居。
春风厉而不烈。我站在土地上,风吹着欢快的口哨,掠过无物的土地,仿佛是一把最原始的伏羲琴,将春在土地上醉了的声音送到天空,我眼前出现的是绿色的音符,和畅的旋律,萦绕于耳畔。我问站在地堰割灌木条子的77岁老汉,他说,只有“厉”才可以把土地的脸吹出笑意,而“烈”只是莽撞,唤不醒春土。我想到了许慎的《说文解字》,都失色了,太呆板,老汉的“解字”是用不老的春心揣摩的。
春风攒足了力气,却又不乏绵绵之情,正如狂风不能让人脱去棉衣,而和煦的日光会让人着急脱下御寒的衣装。我真无法描摹这惊蛰炸响的春风,到底是怎样一种魔力。
春土溢出的土香,也沁人心脾。老汉没有戴口罩,我距他五米开外,他说,呼一口泥土散发出的香,润润肺,窝在坑头,喘气都不匀了。土地的香,凝在野菜的根上。弯着腰,从黄土和草窠处,寻找微弱的绿光,野菜冲动地顶起了酥润的泥土,不屈的绿色寻觅着日光。我发现,土地承载的不是一枯一荣的简单法则,而是新老更替的生动。野菜的香原来是去年的枯草做了香料,原来是土地将香寄托在根上。春风拨开草窠,抚摸一把地皮,绿色就禁不住诱惑而萌芽,诗人说“天街小雨润如酥”,是喜雨之作,而我所见的是“风来问草何故绿”的逗趣,我喜欢这种明知故问的春情爱意。怪不得那么多名义上踏春的人,却胳膊上拎着篮子,想带走春土里的绿。放眼望去,几个裹着头巾的女人在地堰上挖野菜,几个城市人带着口罩,对准了挖菜的人,录制着最生动的抖音。我想起卞之琳的《断章》:“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不必去周庄找那座外婆桥,也不必去西子湖,觅那座断桥,春天的土地上哪里都有朴素的诗,这也是我最喜欢看西北黄土高原画展的一个原因,在苍茫之下,我们最容易发现诗意,最容易闻到土地的香。凡是家乡,每一处热土,都不适宜用“贫瘠”来形容,这也是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到处都有人居的原因。
我相信我读懂了卞之琳的《断章》,凡是有人经过的地方,都有风景,如果披着春风和土地一起醒来,那风景就不是“断章”那样的剪纸式的风景了。
四
老汉将砍伐下来的灌木条子绑上电动车,他说,门前有片园子,每年要换一茬篱笆,就是想闻到春野的味儿,牵牛花快要窜出来了,不能不把篱笆插好。他还有四亩地,给总承包人,每年得四千块,加上村集体给60岁以上老人的养老钱,国家给的补贴,每年也有七八千,日子无忧无虑了,可还是想来地里看看,说说话。
说说话?说什么?他和土地谈心吧,默契是无需语言的。我想起了少年时看见村上的农人深爱土地的画面。每当孟春,队上还未出工,太叔早就蹲在自家自留地头,默默吸几支纸烟,太婶嘲弄他在家一个屁不放,有话都跟土地去说。从初春,到秋收,很多农人都喜欢趁着收工后坐在自家地头,炊烟送来饭香,也没有土地上的香有吸引力,总是要家里人大声吆喝着吃饭哦,才不舍地离开。
其实,在土地里深藏着的是幸福的味道。我毕业那年,成了吃国家粮的人。之前一段不长时间,父母相继去世,正赶上土地承包制开始推行,我是没资格均分土地的人,我跟在获得土地的人后面,看着他们的兴奋,我忘不了一个镜头:德仁哥捧起地里的泥土,深嗅着,说,这样的土质,不能耽搁,明日就播下大豆……
他说第一次可以说算土地上种什么,何时下种。是春风吹醒来土地,唤醒了农人。这样的话不是无忌,是释放。
我想,德仁哥的诗早就写出来了:土地的味道,是金灿灿的稻穗诉说的汗水的咸腥,是快要炸开的豆荚响彻着丰收的喜悦。
是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的春土一直醒着,那声惊蛰的霹雳,始终响彻在天空。每年初春,我总是回村看看老屋老街,还有一些曾经认识的而已经变老的人,之后,我一定要去当年我高中毕业承包的那几亩地看看,席地坐在地头,无语地看着土地,土地早就易主了,但那份无法舍弃的亲切仍在。人们常言说,爱上一个人,才爱上一座城。这是一种追随的爱。我说,因为爱上一片土地,才爱上一个屯一个村一个庄。户籍的概念,只在那个毫无生机的本本上,装不进我的心中。
春来草自青。我想起2008年山东高考语文作文题。这是一种朴素的自然观,当年黄庭坚“兀然无事坐”,突然获得这样的禅悟。我想,我们与土地,从来不必刻意,没有签订一个与惊蛰的协议,却俗成了一个规矩,惊蛰,叫醒了土地,不管是春寒料峭,还是防控病毒,我们都要踏春,看看土地醒来的样子。明媚的春天年年来,在循环往复里,我们最容易失去对春的激情,我很怕,土地醒了,我还在睡。
什么时候会觉得浪费了时间和生命?春来而无动于衷。我想,春来了,惊蛰的雷响了,我们赶快迈开追赶春的脚步吧。
2020年3月9日原创首发江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