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风】我的女神节(散文)
【西风】我的女神节(散文)
非洲没有四季,只有雨季和旱季,雨季最热,步入三月,雨季正浓,我忽然想起2017年在重庆过的女神节,那个女神节与今年的女神节不仅是地域、国别、温度的区别,还有心情,那时候心情宛如重庆此季的天空,浓云密布,阴雨连绵,现在想起来还是记忆犹新,很特别,值得回味。
2017年的女神节过的是空前的,我不敢说绝后,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过这么特别的节日,首先打破常规,破得一塌糊涂。
以前过节,不管什么节日,最基本的过法是隆重的吃一顿肉。而后找一些娱乐活动的场子,或是亲朋好友聚聚,或是去哪儿逛逛。
今天,我在一个风土人情、地域气候与塞北大相径庭的地方过节就得入乡随俗,我本身喜欢原始古老的民俗民风,不喜欢千篇一律人工斧凿的建筑、马路、旅游景点。比如:西安的乾陵、北京的南海公园等等。再说饮食文化,现在是信息时代,交通方便,人口流动,地方风俗潜移默化,大江南北的城市生活、城市建筑基本趋于一体化,特色的东西逐渐淡出年轻人的生活。
我曾经多次去过秦岭,看山里人家的住房,尝他们的饭菜,跟他们聊天,也拍了很多照片。到重庆,气候、地形、饮食、语言与家乡天壤之别。正是这种巨大差异调起了我的兴趣。
项目部给我们几个女职工放了半天假,我们没吃中午饭急急往县城赶,县城很小,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山城,群山环抱,街道狭窄且起伏很大,山腰山脚的楼房栉比鳞次。
也许是过节,街道人头攒动,我们扒开人群挤入服装店,店里的衣服款式和西安七八年前的一样,质地也差,我对衣服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这地方的特色小吃,我特意关注农夫模样的人卖的小吃,很特别,很新鲜,他们用一个破盆,里边放几块木碳,上面架个锅,里边烤着杂粮馍,有荞麦面、玉米面、带麸皮的麦面。还有用一个平底锅烙糯米豆馅饼,另我大开眼界。
重庆的太阳和贵阳一样,很珍贵,偶尔露个脸,如同流星即刻消失。南方的湿和冷非常含蓄,非常执着,湿悄悄渗透人的骨缝,冷从早到晚从黑到明24小时没有温差,一冷到底,满大街的人都穿着棉衣、棉鞋。
我穿了一件妮子衣服,在北方有点厚,在这却冻得手脚没了知觉。我的确饿了,也的确冷,迫切想吃一点高热量的东西御寒。饥寒交迫,我买了一个糯米大豆面馅的饼,一是充饥补充热量,二是品尝,饼是素的,吃完还是冷,肚里还是空空得像没吃似的。
我们又逛了几家店,各自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后找饭店,我坚持品尝地方特色,所以,我选了一家当地风味饭店,要了一碗荞麦面,一碗菜豆腐,老板一口方言,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尽最大努力说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他全懂,我说:面里不要放辣椒,给我倒口热水喝。
老板咕噜咕噜不知道说了些啥,然后呼另一位端来一碗面汤不像面汤,泔水不像泔水,有点红还泛黄的热汤,我端起就喝,还真没喝过这种汤,味道很难描述,一会端来一碗菜豆腐,我吃了一口没有一点味道。
老板笑了,指着桌上放的调料咕噜咕噜说,意思让我自己调。我想吃当地的味道,就说:你给我调,我不会调,不要辣椒。
老板拿个小碗,麻利的给我调了一小碗汁端来,边比划边咕噜咕噜说,我猜是蘸汁吃,因为周围的人就是这样吃的。我蘸的吃了一口,妈呀,好腥气!再不想吃第二口,我把菜豆腐里的汤喝了,等着荞麦面,我想荞麦面咋都得给浇点肉臊子吧?
我不挑食,但吃饭必须得有点荤腥,否则吃了就像没吃似的,肚里老是空落落的。荞麦面端上来,还和菜豆腐一样,什么调料都没有,我等老板舀臊子,老板到一边跟人拉话,我呼老板,老板过来还是咕噜咕噜的比划。老天,还是蘸这汁吃吗?
老板笑着点头。
这汁太腥气,我吃不惯,你放的啥啊?
老板:咕噜咕噜。
我的天,你能听懂我这半吊子的普通话就不能说吗?
一股无名的火冲上头顶,跟我作对是吧?不就说方言吗?我也说:麻烦你给我放滴卜思(蒙语盐)撒不斯(蒜)醋我想不起蒙语咋说,就用日语やきもち说的。
老板摇摇头,说:听不懂你说啥子。
你能听懂就怪了,让你也尝尝听不懂的滋味,原来你能说普通话啊!不逼你你还真因为我是软柿子呢。
我赶紧问:你的汁子腥气很,我吃不成,你放的啥?
老板:折儿根。
又是方言?你能不能说普通话?老板眉头皱了皱,用普通话说:鱼腥草。
鱼腥草是一种药,你怎么能随便给顾客吃药呢?我想质问,忽然觉得,这就是我要找的异域特色。
她说:再给你调一份吧。又调了一份,汁里没放一滴油,清汤寡水的,这不是洗肠子吗?我一口面也没吃,只把面里的汤喝了,付了钱,走出饭店,虽然冷得直打哆嗦,但是开了眼界,不虚此行。
二○二○,三月八日,在南半球,在西非,在大西洋畔的热带雨林,有阳光、涌浪、沙滩、渔船、不同肤色的女神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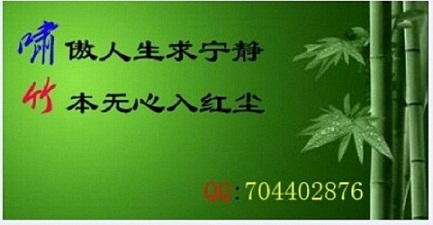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