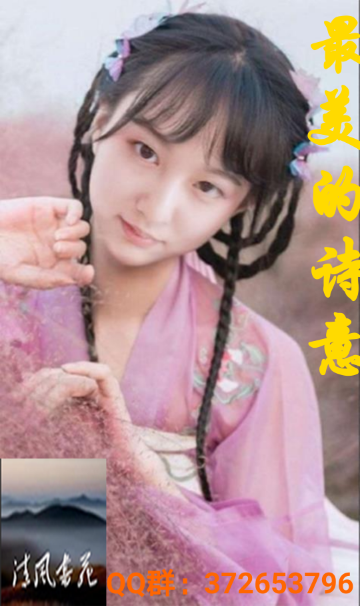【宁静•正】清明的夜色(散文)
【宁静•正】清明的夜色(散文)
![]() 从前的清明是模糊的,如摘掉了眼镜眺望远方的风景;从前的清明仅限于一种概念,与中秋有些雷同。唯独今年的清明,如一面凸透镜,将我置于阳光下的焦点里,紧逼着炙烤;更如一弯猎人腰间的匕首,扎得人无处躲藏。
从前的清明是模糊的,如摘掉了眼镜眺望远方的风景;从前的清明仅限于一种概念,与中秋有些雷同。唯独今年的清明,如一面凸透镜,将我置于阳光下的焦点里,紧逼着炙烤;更如一弯猎人腰间的匕首,扎得人无处躲藏。
岁月总是会在不经意间留给我们一些可触及到的痕迹,也会“明目张胆”地掠去我们原本以为是永恒的真爱,直到理性逐渐代替了感性之后才明白,原来这就是所谓的滚滚红尘,这就是常言说的“后浪推前浪”。当一切都变得真实的时候,也是开始有了痛觉的时候。
过去的三十多个清明节,在我心里仅仅是一个纯粹的节日,这个节日和中秋节、元宵节没有什么区别。除此之外,我也仅仅将之理解为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普通节气,与芒种类似,与霜降一样。在这一天里,会有家人亲戚相聚在一起,这是令人无比开心的;过了这一天,北方漫长而严酷的寒冬将逐渐结束,温暖的春天即将到来,这更是令人无限期待的。因此,一直以来,清明的到来,总会让人神清气爽,精神抖擞。不过这样的清明节在今年却变了味道,变得阴沉,变得孤单,变得让人坐立不安,总觉有点事我得去做做,但到底是什么事情,却又理也理不清,直到前天晚上看到楼下那堆燃烧的火,以及火堆前立着的那位单薄的妇女,我才恍然大悟。是的,清明就我而言,从此不再是一个节日、一个节气了,我的清明变了。
清明节的祭祖和踏青,是中华民族沿袭了千年的习俗了,祭祖是为节,踏青则是为节气。不过也许是因为北方高原的寒冬总是会持续到来年端午前后才渐渐而去的缘故,抑或是因为清苦的农人们整日里匍匐在田间地头,双脚早已沾满了泥土的味道,踏青对他们而言,是小资的行为,更是多余的行为。所以,黄土高原山上的清明,仅仅是一个祭祖的日子,从来没有过踏青一说。在这片距离蓝天很近的土地上,清明节和农历十月一的寒衣节有着酷似的样子,相似在大人们佝偻的腰杆下;相似在孩子门嬉戏打闹的笑声中;更相似在荒草凄凄的坟头前。
我的祖父是他们同辈人中的大哥,所以族里的大小祭祀活动,总是要找祖父来安排,到了那一日,也都要他来召集。祖父走后,族人们的这一多年形成的习惯,顺理成章地传到了父亲的身上。于是父亲成为了族人里新一代的领头者。因着这个原因,在我幼年直至少年时代的十几年岁月里,每到清明节到来,家里总会来许多族人,从晌午开始,三三两两的老人,一手牵着自家的孩子,一手捏着打狗的树梢,吆喝着一路小跑来到我们家。我最是喜欢这个时候的到来,平日里和我光着屁股打打闹闹的伙伴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聚在一起,或是甩起胳膊打纸片,或是席地而围坐,捏着一把石子下谜棋。清明对孩子们而言,首先是一场聚会,然后才是上坟祭祖。但不论是“聚会”还是上坟祭祖,在孩子们的周围,只有笑声和打闹,这种情景似乎和清明的祭祖有点不太相配。但老人们总是会在凝重的气氛中偶尔回头看看周围满身黄土的孩子,露出一种“由他去吧”的微笑。原本我以为老人们是因这场“聚会”而欢愉才面露笑容,如今想来,我是错的,这种微笑是一种欣慰,更是一种担当。当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没有了父亲。
父亲的在清明刚过没几天,就悄然而去了。
父亲的离开是让我措手不及的噩耗,虽然在那之前的二十多天中,已经给了自己足够的心理铺垫,但当呼啸而北去的飞机将我送到弥留之际的父亲身边时,父亲的样子,让我近乎晕厥。我没法接受一直以来身材高大,满脸红光的父亲,在阔别仅仅一个月后,变得骨瘦如柴,面如黄蜡。那一日的夜里,我趴在父亲的炕头,一手捏着父亲肿胀的手,一手扶着自己的眼镜框,就那样盯着艰难而坚强的父亲直至凌晨四点。突然醒来的父亲,摸着我的手,用他最大的声音,近乎于命令的口气说:“娃,去睡去,别再蹲着,爸我没事……”
这一夜的陪伴,是我此生仅有的一次如此细致地看父亲的脸,看父亲睡着的样子,第二天,我就没有了父亲。
父亲的突然“消失”改变了我原本对家、对生死别离,对故土亲情的固有理解;带走了我原本对家,对家乡,以及对那座山村一直以来浓烈而单纯的归属感;同时带走的,还有拥有过三十多个、却已然过往了的那些概念中的春节,清明。准确讲,是父亲的离开,改变了我对传统节日,特别是关系到焚香祭祖类的所有节日的固有观念和认识。原来,清明是一个沉重的日子,只是一直以来这种沉重被父亲年复一年地“过滤”了,挑出来的那些快乐给了我和我的伙伴们。至此,我方才明白,为什么清明时候不论我们多么闹腾,父亲以及父亲那辈儿人往往只是回头微笑一下,不再言语。
父亲,以及所有的父亲们,都是挡在孩子面前的一面盾,抵挡着岁月的风沙,抵挡着红尘里的酸涩。而今,父亲走了,我没了这面盾,岁月在我的面前变成了刀子,总是时不时谋划在我的胸口做个刺青;清明变得真实,变得凄凉,变得单一而灰暗,使人无所适从。
原本我早该意识到这一点的,至少在自己面前没了父亲的阻挡后,就该第一时间清楚这个事实,想到这个,我就会时不时责怪自己的不成熟。不过扪心自问,我实际上是一直逃避,或者是一直在做梦一般试图回到过往的一切中去,然后,在每一个节日来临之前醒过来的瞬间,顿然间怅然无措。
记得去年的寒衣节那天的傍晚,我独自一个人站在小区的楼下面,望着西北的方向,将一根香烟烧到了嘴唇边,那一夜的西北天空,黑得吓人,纵然有斑斑霓虹灯的闪烁,然正是这些霓虹灯,让那一夜显得格外清冷。我在想象就在我站在那里的那时,族人们以及家里的亲人应该正跪在雪地里,将一件件精心“缝制的衣服被褥”送出。烟火缭绕依旧,却唯独没有听到昔日里孩童们打闹嬉戏的欢快声,那时,我明白了我的节日真的已经变了。
前日晚上那位独自立于楼下的那个角落里烧纸的妇人,让我再一次对中年人的节日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顿时,我对那位孤独的妇人投去了最柔情的目光。回头想想,清明纷纷雨下的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孤单,又有谁会给我投来一丝柔情。
成年人的生活中,都偷偷地私藏着许多经不起揭开的痂,用心呵护着,遮掩着,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到了双鬓花发,然而,所谓成人,这就是必然要承受和接受的,所以才有了天真烂漫的孩子得已欢声笑语,得已无忧无虑。
今年的清明节,是我没有了父亲的第一个清明节。过去的年岁中,都是父亲带着家人亲朋给故去的先人祭拜,然而今年的清明,父亲不在了,他可知这个清明风清月朗,他可知这个离家三千里的孩子,又会盯着西边天上的星星,念着无人能懂的“经文”。
城市的夜空总是很亮,这一点也不像高原山村里的夜,少了神秘,少了深邃,更少了夜色本该有的深沉;城市里的清明总是带着不同的味道,诸如车流而过的味道,诸如灯红酒绿的味道,诸如踏青的味道,唯独看不到的,是我记忆中的香火味。
再一次乘着夜色,盯着西方的夜空,在心里,将几页薄薄的纸,和着微风,送了过去……
作者笔法流畅,叙述自然,故事性强。推荐欣赏阅读!问候作者!

是啊,只能走好自己的岁月,以求慰藉故去的亲人!
问候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