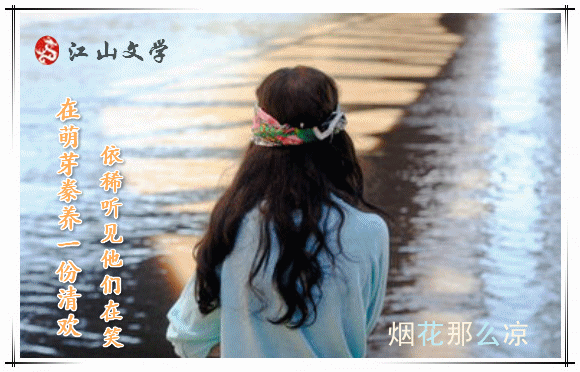【菊韵】七十七年的婚姻 (散文)
【菊韵】七十七年的婚姻 (散文)
![]()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正月十九,这一天父母结婚了,母亲离16周岁还差20天,父亲刚过完15周岁生日。那一天,拜过天地,拜过高堂,入洞房的时候父亲失踪了……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正月十九,这一天父母结婚了,母亲离16周岁还差20天,父亲刚过完15周岁生日。那一天,拜过天地,拜过高堂,入洞房的时候父亲失踪了……
找不到新郎官,爷爷急得捶胸顿足,像热锅上的蚂蚁片刻不得安宁,一个劲地说,都怪我,都怪我,我不该……
奶奶很淡定,一言不发,抱起被子,去陪着母亲睡觉了。
母亲不见父亲来洞房,喜出望外。正想睡觉,见奶奶抱着被子来了,忙接过被子说:“妈,你咋来了。”边说边帮着奶奶把床铺好,母亲明白了,这一夜父亲是不会来了。
奶奶去陪着母亲睡觉,爷爷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思前想后,觉得这门亲事有些仓促和草率,父亲一直不接受这门亲事,但用这种方式抗婚,让爷爷始料不及,无可奈何。这要是让亲家公知道了如何得了,愧对亲家,愧对人家女儿,没法交代呀!他想起了那个夜晚,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
村东头一片茂密的树林,成了坟场,那里安葬着各家各户去世的人,树林深处有条路,是通往县城和其他村庄的必经之路。有人说坟地里夜间经常闹鬼,让过往的行人可怕至极,毛骨悚然。爷爷是有名的飞毛腿,胆子又大。他决定去树林探个究竟,看看鬼长得什么样子,顺便抓一个来给大家看看。
一直等了几个夜晚,都未见一个鬼影子。这一晚,爷爷等得不耐烦了,决定回家。正在这时,突然发现一个亮光闪过,一闪就不见了,然后听见唰唰的声音。爷爷闻声而去,发现一鬼影,穿过树林,向着村庄方向晃来晃去跳着行走。爷爷高兴极了,心想,终于等到你了,也不作声,撒腿就追。
鬼影发现了有人在追,越行越快。一个铆足力气追赶,一个拼命奔逃。最后,爷爷终究还是没有追上鬼影,让他逃掉了。跑得太急了,累得爷爷回到家里倒头大睡。
快到中午了,奶奶叫醒了爷爷,说他惹了大祸。听说邻村的老张(后来的外公)昨夜做生意回来晚了,路过树林,被一鬼穷追不舍,回到家里就病倒了。奶奶让爷爷赶紧起来去看看老张,告诉人家真相。
爷爷和老张认识,知道那是个老实厚道的买卖人。拿着奶奶绑好的一只老母鸡,去老张家负荆请罪。
爷爷见了老张,说明了昨晚的行踪,一个劲地道歉。老张明白了是爷爷不是鬼也就释怀了,不再后怕。爷爷不解问老张开始进树林有亮光,怎么突然没了呢?
老张告诉爷爷是他自行车前面绑着手电筒,可不知道为何,走到树林子里手电筒就没电了,只好摸着黑前行。他也是闻听了坟场有鬼的传闻,把爷爷当成鬼了。坟地都是沙土地,车轱辘陷进沙子里,越着急害怕越骑不快,着急得出了一身冷汗。好不容易骑出树林,路况好了,飞快骑回家。
俩人说明白了,唠了半天。老张杀了那只鸡留爷爷吃了午饭,几杯酒下肚,俩人高兴至极,席间就把父亲母亲的亲事定了。那年父母都是10虚岁。
对这门亲事,母亲一百个反对,“父母之命不可违”,她依然极力抗婚,用那微不足道的力量和各种方式争取着自己的权利。我外公是生意人,最注重诚实守信,让他退婚言而无信,这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
母亲抗婚未果,只好听之任之……
结婚那天,母亲的二舅(我二舅姥爷)知道我奶奶家抠门,怕不舍得租轿子,就派人捎口信,不要吝啬钱,轿子钱他花,这样母亲也安心了许多,开始梳洗打扮换衣服。
那一日,母亲装扮完毕,左等右等,眼看拜堂的时间就要到了,父亲才赶着老牛车慢悠悠地来接新娘。二舅姥爷急眼了,勒令父亲回去,非要亲自去找花轿。父亲说来不及了,时间都快到了。就这样,母亲坐着老牛车嫁到了父亲家。她不知道,这是父亲抗婚故意刁难,好让家长难堪。
母亲身材修长,亭亭玉立,大红的旗袍垂到脚面,更显窈窕多姿,一下车和父亲站在一起,比父亲高出半头(当时父亲正处在生长发育期),左邻右舍、乡亲父老对母亲赞不绝口。母亲说,结婚那天是她一生中唯一化妆的一次,此后连润肤霜都没有用过。
入夜,亲戚们都走了,洞房里只剩下母亲一人,始终不见父亲的踪影,母亲心里窃喜。心想,一辈子不来才好呢!
一个躲着不进洞房,一个看不见新郎高兴得不得了。这就是父母的新婚之夜。
爷爷脾气不好,左邻右舍都知道。第一个媳妇实在是忍无可忍,带着闺女远走他乡。父亲是爷爷老来得子,所以从小就娇惯着。父亲的脾气像极了爷爷,但更任性自私。为逃避这场父母包办的婚姻,父亲离开了家,找到了抗联,投入到滚滚的抗日洪流,并悄悄地加入了党组织……
母亲并不知道父亲干啥去了,只知道这个家里没有父亲挺好的,每天除了家务就是跟着奶奶去地里干农活。苦点累点母亲毫不在乎,对奶奶的吝啬刻薄母亲也没当回事。母亲说她心大着呢,能撑船。按现在的时髦话来说“啥都不是个事儿”。
但当父亲提出要离婚的时候,母亲毅然决然地告诉父亲,那是不可能的,婚前她抗婚五年没成功,既然嫁了绝对不离婚。母亲认为离婚是很丢人的事情,不管父亲回不回家,守住这个家就是她的本分。
母亲如此态度坚决,让父亲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逃婚。
不知道是老天捉弄人,还是命运不可违,父亲做梦也没想到,他逃婚投奔到唐山地区行政公署的人,竟然是母亲的表姐夫。被一顿训斥,乖乖地回家了。从此和母亲过上了安稳的生活,再无二心。用父亲的话说,该是你的就是你的,逃是逃不掉的。
一场戏剧性的婚姻经过了前后长达十年的抗争,终于回归宁静。
这一守就是77年,一守就跨过了两个世纪。
我问父亲,母亲的家庭、外表、人品条件样样好,你为何逃婚呢?父亲说,那个时候不是对你母亲有意见,除了对你爷爷的安排逆反外,也是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反对。父亲也算是进步青年,受新思想的影响,想争取婚姻自由。只不过像孙悟空一样,始终没逃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母亲说,从她过门以来,也没见过父亲顺从过爷爷,都是爷爷说啥父亲就反对啥,爷俩冤家一般,很难相处。母亲庆幸的是五个儿子谁也不敢顶撞父亲,都特别惧怕父亲,尤其是二哥三哥,相差两岁,爱打斗,母亲无奈的时候说一句“你爸爸来了”,哥俩不由分说条件反射似的撒丫子就跑,一会儿就没影了。
现在想想,一个15周岁的青少年,连个子都没有长成,正处在家庭的叛逆期,所以对爷爷安排的婚姻任性反对,也在情理中。这不是父亲的错,是那个时代对青少年的摧残。如果是现在,逼着一个15岁的孩子结婚,会有百分之百的人逃婚。
我很赞同母亲的婚姻观,既然嫁了,就是一辈子相守。家里只要有好女人守着,就不愁男人不回家。
父亲在供销社工作,是老革命,工作大于一切,很少回家,母亲一人操持家务,带大了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小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回家和母亲生气,父亲咆哮着,吼叫着,气急败坏。母亲则沉默着一语不发,从不和父亲争辩,嘴里会唠叨句“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两个人说啥事情都说不到一块去,最后肯定是母亲无条件依了父亲才结束。母亲和父亲生气的时候,都是委屈自己,不吵不闹,不吃不喝,蜷曲着身子靠在被摞上暗自垂泪,那样子另我们心疼。父亲就是一个严厉的家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父亲回家的时候,母亲总要做点好吃的,我们也跟着改善下生活。诸如包饺子之类,平时都是吃玉米面菜馍馍。吃不完剩下的饺子,母亲也要给父亲留着,往往是我们看着父亲吃饺子,个个馋得咽口水。父亲闭着眼睛吃,从来不顾及孩子们的感受。母亲说,细粮是父亲的粮本领的,父亲身体不好,需要营养。
父亲在家养病期间,整天愁眉不展闷闷不乐。母亲看出了父亲的心思,是怕被供销社辞退。母亲变着花样地给父亲改善生活开小灶,劝说父亲要想得开病才好得快,辞退了也不怕,母亲给五联村人家经布(把线放在织布机的过程),最多的时候一天的收入就是父亲一个月的收入。家里从来不愁没钱花,不是父亲挣得工资多,是母亲经布的收入高。
外表上父亲是当家的,其实大事小情都是母亲张罗着。父亲爱面子,干啥都不好意思,需要出头露面的时候,母亲挺身而出义不容辞,不管多难的事情,到了母亲那里都迎刃而解了。
孩子们陆续长大,父亲因病提前退休了,回到农村和母亲一起过起了田园生活。院子前后成了瓜果蔬菜的乐园,两口子一起干活,父亲的身体也逐渐强壮起来。干活的时候也是你说这样,他说那样,总是拧着。母亲总是说,你爸爸各色(方言,意思是古怪和一般人不一样)得很;父亲总是说你母亲任性不听话。我也总是笑笑说,你俩呀一辈子没一句共同语言。
上次回家,母亲和我诉苦,说和父亲生气了,问其原因才明白是因为前院的三婶来找她打牌,没吃午饭就走了,玩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也没回家。父亲去找她,可能是态度不好,惹得大家不欢而散。回家就和父亲怄气,父亲解释说,毕竟是90多岁的人了,饿着肚子坐半天,是心疼她,才去找她的,没有态度不好。但母亲不理解,说父亲搅了牌局,不给她面子。三婶说,再也不来找母亲了,嫌父亲事儿多脸子难看。类似这样的小事,在我看来根本不是个事儿,但他们却很在意。每次回家,母亲便有各种委屈向我诉说,我一边安慰母亲,一边说父亲,别总管着我妈,她爱干啥就干啥。父亲苦笑说,没管她,只是关心她,她不领情而已。
母亲因缺钙腰腿不好,父亲还总是让她活动活动。母亲很不理解,回家就和我唠叨,父亲不疼她,总让她干活。可父亲却说,你不干活了就等着死了,能干就干点,对身体有利。父亲讲究生活质量,母亲则是过一天少一天。夫妻俩没有一句共同语言,性格脾气也大相径庭,就这么磕磕绊绊一起走过了77个春秋。
儿子的裤子兜坏了,拿来让我缝补。母亲接过裤子对儿子说:“我来缝补,你妈妈做不好这针线活的。”母亲接过裤子,拿着我找出来的布头比划比划就知道怎么做了。父亲找来针线,帮母亲穿好线,递给母亲。母亲戴上老花镜,一针一针地缝补;父亲在一边抻着,缝补完了,父亲拿起剪刀把线剪断,收拾好针线放到针线盒里。我在一旁看着他们夫妻那默契协调的动作,就明白这是生活几十年配合的结果。父母是典型的互补型,所以找不出他们的共同点,但能配合默契和谐相处,这得需要怎样的磨合和磨炼才可以做到的啊。
这次回家,看到母亲端着一杯水,在和父亲怄气。父亲患前列腺增生严重,影响到了解手。医生嘱咐多喝水,一天要喝两壶水。这样防止尿储留引起的炎症。
母亲和我说:“你爸任性着呢,喝水比喝药难,每次都是逼着他喝水才喝一点。”
我说:“妈你不用生气,他不喝水就住院去,看看哪个受罪。”
父亲对我说:“快不行了,老了,浑身疼。原来总是出去走走,现在一点精神没有了。懒了!这一懒就坏了,不活动吃啥啥不香,浑身难受。”
我说:“要不去医院吧,好歹有医生呢,放心。”
父亲说:“不去住院了,剩下的钱给你妈留着,她没劳保,得给她攒点钱,都给医院花了,没意义了。94岁了,走了也到寿了。”父亲的话,让我眼睛湿润了,别看俩人总是掐,说不到一起,到了最后还是惦着老伴,让我感动。
一辈子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岁月艰难便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父母付出的艰辛是无法估量的。夫妻能做到同甘共苦、风雨同舟就是难能可贵的。
父母的婚姻生活是典型的封建家长制,夫唱妇随,一言九鼎。母亲的妥协、宽容、忍让和吃苦耐劳,体现了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