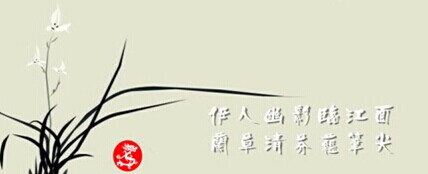【神舟】为难称呼(散文)
【神舟】为难称呼(散文)
![]() 普通人普通事,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招呼或者两句闲聊,涉及到称谓,我流畅的语速瞬间堵塞,有几分迟疑,甚至有些难以启齿。
普通人普通事,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招呼或者两句闲聊,涉及到称谓,我流畅的语速瞬间堵塞,有几分迟疑,甚至有些难以启齿。
年少时我们姐妹因称呼挨过父亲的训斥,主要是在部队习惯了,称呼别人一律在前面加一个小字:比如小李叔叔、小张阿姨。后来回到地方,依旧积习难改,结果邻居不乐意了,他们和我父亲平级,年龄也不比我父母小哪儿去,玩笑似地找上门来。为此父亲大发雷霆,狠狠地教训了我们一顿。此后我叫人便有一份紧张一份犹豫,生怕祸从口出。
长大后进单位工作,由于习惯更由于羞涩,不好意思称异性男人,一律还是说男孩。有女同事问我谁把订书机拿走了,我说可能是刚才那位大男孩拿的,同事便出去找人,一会儿又过来问我是不是看错了,根本没有什么男孩来过啊。我上前指着不远处三十出头的男人说,他不就是吗?同事哭笑不得,点了点我的额头说,傻丫头,他比你大多了,你怎么能喊人家男孩?
这一笑话让同事当面背后笑了许久,从此凡异性我一概称男的,不再添加亲切活泼的修辞。
后来让我困惑的是“丈夫”这个称谓,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没有结婚前我是不好意思问及同事的另一半,似乎说一句你“丈夫”,都有偷窥了人家夫妻亲密的嫌疑,我结婚后也没有达成女孩到女人语言上的质变,说话特别注意分寸,没有同事敢随意跟我开玩笑,但“丈夫”这两个字却是必须面对的,介绍自是少不了,可还是有些羞于出口。翻查字典,夫多被称为“丈夫”,有两种说法,其一母系社会女尊男卑,男女结为夫妻后,男担心女被其他男人抢走,便尾随女身后,又恐其反感于是保持一丈的距离。小心伺候,久而久之落下“丈夫”之称。其二则是古有抢婚的习俗。女子选择夫婿,男子身高首当其冲,通常以一丈为标准。这样高大强壮的夫婿,方可抵御强人的抢婚,据此,女子便称所嫁之人为“丈夫”。
现在不是母系社会,也非抢婚时代,难怪我怎么也不习惯喊出“丈夫”这个称谓。细想“丈夫”之所以沿用至今,也自有道理,热恋时期可不就是母系社会吗?热恋中的女人说一不二,热恋中的男子哪一个不是跟随女子左右嘘寒问暖,哪敢擅自远离恋人一丈开外。尽管现在没有抢婚旧习,但婚后男子依然坚守保护妻子的责任,是为妻儿拼尽全力,为家庭遮风挡雨的大丈夫。“丈夫”这一词体现了夫婿的责任,也贯穿了千百年来妻子对婚姻的期许,
我赞同“丈夫”的内涵,只是不习惯张口提及。父亲曾是军人,他和母亲多是以爱人互称,偶尔也说家属。我很认同爱人这一说法,毕竟家属也可以包括我们姐妹,但爱人只能是父母彼此。“爱人”多么美好,比“丈夫”少了一分孔武有力的粗糙,多了一分浪漫气息。看一眼都是含情脉脉的甜蜜,叫一声无异于向全世界宣告我爱你。想当初提出这个称谓的人必定是深爱着自己的另一半,由己及人,恨不得让大家天天挂在嘴边,铭记于心,切莫辜负了另一半的情义。
离开部队,我只听过父亲对外介绍母亲使用这样的称呼。我们这个小城那时都是喊媳妇,男的则称之为“丈夫”或“当家的”。
“媳妇”全国流通,我听着也顺耳。“当家的”则新鲜,有走入影视之感,是男权统治封建社会的家族,但不是家规森严的权贵阶级,那是老爷太太们的专属。喊“当家的”女人们应该是衣食无忧但所剩无多的小家碧玉,住在一所青砖小院,空间不大却无一例外地种上几盆花草于风中摇摆。喊孩他爹的多半就是劳苦大众了,场景自然是一片茅草房,于昏暗的灯光中缝缝补补相守到老。虽然清贫,却也有点点温暖的光照。
如此推想,我们小县城这个叫法还真是再贴切不过,如今的女人们哪一个不是衣食无忧呢,但是想再上一级也绝无可能。大家平等,相互你当家的我当家的喊个不亦乐乎,看到对方就像看到自己一样的亲切。
我还是喊不出口,通常以一个“他”划过,或者直呼其名,不管人家究竟知不知道这个名字的主人和我是什么关系。
名子,本身就是一个称呼。“爱人”这么情深义重的呼唤,又能如何?我父亲声声不已,可我从来没见过有一点能落到实处,刚滑出温热的口腔早已被风儿吹得无影无踪。
据我过世的母亲说生我后她去上海做心脏手术,胸前划了那么大的刀口,父亲都不知道怎么照顾她,后来想起买补品,还买的是油炸麻雀,那是刚手术的人能吃的吗?不过母亲吃不下去没关系,父亲爱吃。我们小的时候母亲都是一个人自己去医院住院,我们大些了便是我们陪母亲住院。母亲从不抱怨父亲,她一个病弱的人似乎总觉得高大强健的父亲更需要别人照顾。我无法理解母亲,唯一的解释就是母亲太坚强,太有同情心,父亲只要稍微委屈,她就觉得自己应该护他周全。像她这样医生勒令卧床养病,甚至医院常常要下病危通知的人,却比正常人付出还要多。小到家庭琐事,大到我们的工作住房,以及亲戚们难以解决的问题都要她跑前跑后找人办理。而我的父亲品着茶看她跑前跑后,看心脏不好有着气管炎的她站到凳子上去换电灯泡,高大的他没有一点自己要上去的意思。
“爱人”这个称谓在母亲一阵急似一阵的喘息声中再也无法轻盈,于风中跌落,碎了一地。
喊什么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人做了什么。后来我也开始入乡随俗,聊天时一口一个“当家的”。比较而言,我的丈夫是名副其实的当家人。当初我就是冲他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与心疼才嫁的他,婚后他也是这么做的,尽管有段时间玩野了经常不归家,但也不算食言。我现在还能这般没有俗事烦忧,不食人间烟火。我儿子说全是他爸的功劳,换成他坚决不要我这样的人当媳妇,都这么大人了出个门都找不到回家的路,事事要人操心,真是太不省事了!
我心中一惊,我对我老爸也有类似的嫌弃。比较来比较去,觉得我比我老爸要顾家多了,至少儿子是我自己一个人带大的,当年可全是我妈和外公带我,我老爸抱一下都恨不得将哭闹的我摔到大门外冻死算了。可我却无法和儿子理论,黯然伤心了许久。
每个人总是看到自己的优点看不到别人的长处,那就无须苦苦寻觅,尽力做好自己。不管儿子对我这个妈啥态度,我首先要求我自己做好女儿这个角色,纵然父亲有千般错也无法抵消他生养了我这个事实不是吗?
这么一想心胸豁然开朗,觉得父亲也是有情的,只是我看不到而已,不然母亲临终也不会拉着父亲不忍放手。每个人的爱情都不一样,才有了“爱人”“当家的”“孩他爸”诸多昵称。
“老公”这个称谓纯粹是看港剧看过来的,那时港剧风靡全国,一个称谓在小城犹如一夜东风,开得满城香艳。几乎是一觉醒来,耳朵里充斥着“老公”的声浪,此起彼伏。以至于我从排斥到接受,搞得小城四处流窜着一股土土的港腔。
“老公”大家欣然接受,但“老婆”却迟迟未能替代媳妇。可能是两者同样历史悠久,没了新旧之说,所以也不存在替代与否。在小城喊老婆就如同喊媳妇一样顺口,只是喊媳妇的更多些。想是“媳妇”虽然乡土味十足,却足够年轻俊俏,“老婆”一看就是城里人,但四平八稳不够轻盈吧。
时间久了,我也习以为常,开口闭口再不为难,喊得再顺口不过。可写作上又开始犯难。我发现无论书面还是口语,配偶女方都好开口,尤其是书写,“妻子”柔而雅,“媳妇”通俗“老婆”大气。唯独“丈夫”“当家的”“老公”看字面好像都有些拿不出手。于是文学作品里出现了一些替代,比如“夫君”“先生”,这些称谓看着是雅致很多,可我偏偏不好意思使用,总觉得“先生”有点高度,“夫君”有些风度,这两者我老公似乎都有些达不到,就像我不够格称夫人一个道理。于是写一篇文,改了八回,最后还是觉得我只能用前三种。
称谓和生活习俗有关,和性格也有很大的关系。如今的我已到不拘小节的年纪,别人喊出口的我也可以说。只是文学上还是有些拘谨,想是资历不够吧,每每提笔又想起有关称谓的往事,嘴角溢出一抹笑意,青春不再,年轻时的闹剧竟也有几分可爱。就像看别人书写那些“丈夫”的雅称不觉眉眼含笑,想着看久了自己或许也可以大模大样地借用一下。人总是向往美好的事物,哪怕只是一个美好的称呼,也是生活的一个小小的点缀,不管生活如何,都要尽最大的努力,将人生妆扮得越来越接近自己想象中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