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年·时光】“那年那事”之螬密涌心(征文·散文)
【流年·时光】“那年那事”之螬密涌心(征文·散文)
一
我与妻子走到一起实属不容易。按照她当时的情况,应该比我更胜一筹。她年龄小我五岁,白皙的皮肤,亭亭玉立,戴着的金丝眼镜更显文静。在脱掉农皮很难的那个年代,初中毕业就考入了人人羡慕的中专——四川卫校。毕业后又分在了市里的铁路医院从事统计工作。而我呢,自然考学无望,只得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本打算从此认命,像父辈们那样,去做一个与土地打一辈子交道的地道农民,命运却意外安排我成了一名军人。那时,中越自卫反击战才刚刚结束,边境线上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去,作为独子的我,当兵自然是有风险的,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军营。
好在五年后,凭我的表现,留下来当了一名改变我命运的志愿兵。从表面上看,我与她都站到了靠工资吃饭的同一起跑线上,其实不然。我们存在的悬殊,依然在她家人那里被视作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爱情这东西一旦发作,就有如野马般狂奔。那时,她仍坚持与我秘密书信交往,在我们接上头的第二年,她突然来到了我所在的军营,我被惊得目瞪口呆。事后我问她,你家人终于可以放你一马了?
她莞尔一笑,很开心地告诉我,我给她们说,如果那次我螬密涌心死了人,你们到哪儿管我去?
什么,螬密涌心?我惊讶地问。
是啊!这是戳中她们软肋的秘密武器,她们不得不松口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凭这四个字,就能让她们退缩了?我狐疑地摇了摇头。
以后再告诉你,反正她们不得不这样做。
后来,当得知了螬密涌心的真相后,我在她面前竖起大拇指说,高,高,高家庄实在是高啊!
不过,从她的表情上看,可没多少快乐的影子。要是我真死了,我们还结个鬼的婚啦,脑壳昏……她说。
二
妻子左手的腕骨那里,有块拇指大的疤痕,有次我问她是怎么回事,她并不乐意告诉,在我刨根问底的追问下,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与螬密涌心有关。
在她七八岁的时候,总感觉到天天都没力气。上学的路上没力气走,坐在课堂上没力气做作业。连有些男生故意欺负她,都没力气还手。回到家,父母根本没时间管她,仍要安排她去做这做那,其中割猪草、砍猪草、煮猪食、喂猪食,是她每天必做的事。但她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在冬天下着雨的屋檐下睡着了。这一睡,就睡出了个大问题,她竟然长时间没被弄醒过来。
家里的人,以为是叫天气寒冷给冷着了,就一个劲儿地给她发汗,用稀缺的红糖熬了姜汤水喂她,却把她鼻子、嘴里的虫给喂出来了。
那个虫啊,有筷头子那么粗,有的已经老红了。它们一出来就活蹦乱跳地撒着欢,一下子就把她的母亲吓坏了。
像这种“怪”事,村里的老人们从前倒是听说过,可还没人见到过呢。难道这就叫螬密涌心了?她母亲赶紧去请了邻居家的老人来看,那老人说得更吓人,你看她都昏迷了,螬虫一定是进了心脏,肚子里已经装不下了,不然不会从鼻子口里往外钻……她不忍心再看下去了,嘴里一连好几声说着可怜啊可怜啊地走开了。
六神无主的她妈,在场地上嚎啕大哭了一阵,想到的不是“没救了没救了”之类的事,也来不及告诉其他人,就赶快背起她往公社卫生院跑。
四五公里的山路,她妈也晓不得累,背上的女儿完全昏迷不醒了,她想歇口气,一怕耽误时间,二怕坐不稳的女儿会滚过去,硬着头皮、疲惫地把她背到了卫生院。到了医院,她母亲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用手指着她的女儿说,救……救……快……救救她……
多年之后,当年救过我妻子的那个老医生,只要见了我妻子便开玩笑说,变狗的娃儿活过来……
据老医生回忆,我妻子被她母亲背到公社卫生院后太阳落山了。那天他值班,心想没病人了,可以端碗吃饭了。哪知这个不死不活的小病人一来,把整个卫生院都搅得不安了。她母亲坐在那儿哭天喊地、捶胸顿足地数落说,可怜她的这二女儿啊,生在她们那个贫穷的家里,没吃过一顿好吃的饭菜,没穿一件好的衣服,这么小就这样走了。她也不想活了……
大妹子,你不能光这样哭啊,咋治你得说个话呀,哭又不能把她哭醒……那个老医生也急了,看了看我妻子惨白的脸,摸了摸我妻子冰冷的小手——那小手啊,黑得像个挖煤的。而且那黑呵,也深深地渗透进指甲缝里了。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治,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不治,连这一线生机都没有了。就死马当个活马医吧!救不活,不能怪我喽,她本来就不行了……
她母亲又想哭,被那老中医制止住了。
一连输了几天的液,我妻子昏迷的程度好像都没减轻多少。但几天下来,她的左手戳满了针眼,换到右手来输时就漏了针,又被感染了。
这下,医生不但要治她昏迷不醒的病,还得为肿胀的右手消肿。这不,手腕那里才落下了这块疤痕。
三
我们结婚以后,奶奶很是喜欢她这个孙媳妇。我妻子呢,则表现出特别懂事、特别孝顺的那种“好”来,常常逗得奶奶开心不已。
没想到,奶奶却把她存放在心底多年的秘密,第一次拿出来讲给我妻子听——是妻子问我时,我才知道这事的。而我这个从小由奶奶带大的身边人,居然被隐瞒了没告诉。
有天,我故意噘着嘴问她,奶奶您怎么那么偏心啊?我居然还有个大伯,你也不告诉我……
又不是什么好事,告诉你干啥?你又没得过螬密涌心,听说我孙媳妇小时候得过了,我才向她摆起了这件事……她先是一愣,继而才说出了后面我能理解的那些话。毕竟是遇到了同病相怜的人,她才像觅到了知音似的管不住自己的嘴了。
是的,那的确不是件什么好事,甚至可以说,是奶奶心头一直的疼痛。她之所以很坦然地告诉我妻子,说明她在几十年风霜雪雨的磨砺之后,早已释怀了。
有天,当我与父亲在一起的时候,我好事者似的问父亲知不知道他有个哥哥这件事?父亲一脸镇定地回答我说,知道啊,哥哥大概是三四岁就死了,得的是螬密涌心……
如果不是妻子小时候差点被螬密涌心夺去了生命,我也不会这么上心的。当再一次听说有人得了这种病,而且事关我的家人,而且还死了人,觉得这病太可怕了,便很是讨厌起它来。仿佛在弄清真相后,要把它给消灭了似的,我便从父亲那儿去“查找”真相。还真有了结果呢。
那时,我还没出生。听妈说大哥还没取名字就夭折了,他是闰月生的,小名叫润生。
他们天天只晓得去租来的地里做农活,只说在交了人家的租子后,还能多些剩余。爹的心思只在田地上,妈那时也才生了场病,身体虚弱得很,都没时间在家里闲着。六月炙热的阳光下,她还带着哥哥去地里除草,穿着“岔岔裤”的哥哥,就在田边地头自个儿玩耍。他们早上出去了,晚上月亮升起来才回家,中午就吃进些生冷硬剩的东西。
爹妈丝毫就没想过哥哥会得那种病。能不得病吗?在当时那种周围环境又差,只图填饱个肚子,什么都往里装。何况哥哥还那么小,什么时候吃的什么东西,又没人看得见、更没人去制止。到得了病时,就开始傻眼了,肯定就晚了。
傻眼又如何呢?也没钱去及时治啊!
听妈说,哥哥几次捂着肚子说肚肚疼肚肚疼,他们就在他小肚儿上像安抚样地摸几下,算是把他给哄过去了。
他吐螬虫的头天,瞌睡很多,妈就在地边的一块石头上,给他垫了件衣服,叫他睡会儿。怕太阳晒着,就在他小脸上摘了几片桐麻叶盖上。
晚上背他回家的路上,他把头耷拉在背上,就有些不行了。进屋的时候,不等把他放下来,从他鼻子嘴里涌出来的螬虫,吐了一背,眼睛都不晓得睁开,人迷沉着……
虽然爹妈无计可施,但是也没想到要送去医治,只说天亮就好些了。哪晓得半夜去摸他,瘦得只剩下皮包骨的身体,早已冰凉了……
四
听了父亲的讲述,我忽然想起一些事。尽管在我小时候,还没有听到过螬密涌心这恐怖字眼的,大人们所做的事,却又与它有关。
有天,我放学回来捂着肚子,向奶奶说,我肚子疼。她先摸摸我的肚子,有点放心地说,没起硬梁,没起硬梁……又把我拉到亮处,看我肚子上长没长出“羊毛疔”来。有次,我的肚子上还真起了几颗羊毛疔呢。
幺女子,来给我孙子挑挑,我眼睛不行,怕伤着肉了,她赶忙叫来母亲,自己则站在旁边,给母亲打着下手。还给我说着宽心的话,不疼不疼,我这孙子还搂得起,挑了肚肚就不疼了……
洗手是我们最不愿做的事,大人们却在时时提醒着。他们拿来肥皂毛巾,还亲自舀来水,倒在洗脸盆里。而我们对手的维护,犹如婴儿对第一次理发那般的不情愿。
就连大年三十吃了年午饭的下午,都要勒令我们必须洗了脸、洗了手脚,干干净净去迎接这第一次所穿的新衣服。
我们并不明白大人们的这些要求里,就藏着病从手入的担心。
就我所知,我们那贫穷偏僻的小山村里,是没人得过螬密涌心这种怪病的。还真没有呢!
是不是与我们小时候常常吃到的“宝塔糖”有关呢?抑或还与我们家屋后的那棵苦楝树有关呢?用那树上的苦楝果,熬出来的水又苦又涩,我们可没少喝哟!
这问题,我一直都在思考着。
“螬密涌心”虽然我在网上也没有查出具体是什么病,但感觉还挺严重和可怕的:妻子、伯父、哥哥都曾患上,而且伯父和哥哥还因此早夭。文章中一个情节让我印象深刻,“哥哥罹患疾病,爸妈虽然无计可施,但也没想着去医院,只希望天亮就会好些”……不是他们不想而是缺少能力,在那个贫瘠的年代,有多少事情都显得那么的无能为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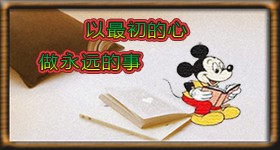
足行老师讲的这个螬密涌心,在我们老家讲的是蛔虫返位。我小时候也会经常听大人说起过,大人总是对我们这些小孩子说,如果不讲卫生乱吃东西,就会得这个蛔虫返位的病,大人们也会把蛔虫返位时的那个恐怖样子,说给我们这些小孩子听,他们当时的目的,就是想让小孩子在讲卫生方面有点自觉性。
足行老师在这讲的螬密涌心故事,居然还可以牵扯出你和你妻子的浪漫来,你的妻子,也算是有急中生智的办法,她居然会用螬密涌心的事去妥协她的父母,哈哈,你们这是不是也能叫因祸得福呢。
螬密涌心,也是缺衣少食的年代,大人们忙忙碌碌没有多少时间照顾自家的小孩子,小孩子嘴馋,会乱吃不卫生的东西所致。
如果得了螬密涌心的病,也有很多是靠老天爷保佑能及时发现和能及时治疗才活过来的,否则,就有小命不保的危险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