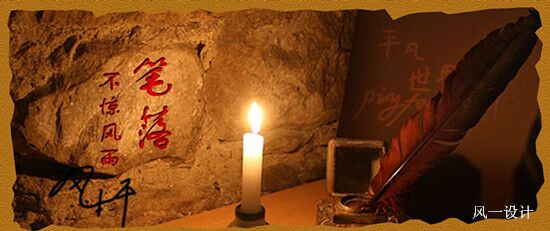【东篱】老师(小说)
【东篱】老师(小说)
![]() 一
一
赵意从小就羡慕老师,就想当一名老师。可惜,走向社会后,阴差阳错,他终于没成为一名老师,终于没能从事上“阳光下最崇高的职业”。但他没想到的是,老师这个称呼,陪伴了自己好多年,也别扭了好多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赵意大学毕业三年后,就和同学来到上海闯荡。都说上海遍地是黄金,不捡都不行,有时候都硌脚。转了几个人才市场,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岗位,在上海,自己的大学名气不够响,校名里还带个“农”字,和工业城市上海好像格格不入,每次HR(特指企业人事部门)看简历,一看到毕业院校,眉头就皱一下。同学泄气了,以上海太热,听不懂上海话为由,回家乡边境小城了,考了公务员,进了公安局。赵意不服,自己住在乡下的民租房里,继续找着工作。最后,他听了父亲的建议,先不要一步到位,找个公司先落脚,以后有机会再跳槽。果然,他放低身段,虽然他工作经验少,但“市场营销”这个专业还是让人眼前一亮。结果不久,就被一家商贸公司选中,去做销售经理。
赵意的公司是一家国企子公司,总部在北京。是中国改革开放提速时期成立最多的公司,大街小巷,这类公司比小饭馆都多。公司市场有总部打下的底子,不需赵意太伤脑筋,要他主要是做好销售管理。公司经营各种印刷纸张、印刷器材,起初,生意兴隆,开发票的小王开得手疼。渐渐地,随着更多的经营者加入这个行列,恶性竞争发生了,假冒伪劣,浑水摸鱼,有的公司还用低价、给回扣拉拢顾客。公司的业务开始萎缩,一向比较平稳的新区市场也出现动荡。有的客户以印刷业低迷为由减少进货,公司在马路对面租借的一百多平方的仓库里,积压的货物越来越多。年底盘点的时候,赵意进去了一次,在仓库里,只好左闪右躲走路,一大卷一大卷的纸张,一箱一箱的器材,不规则地堆砌着,很像枪战片的现场,每一卷每一箱都能成为不错的掩体。
老总急了,起码要保住原来的市场份额,否则,跟总部无法交代。通过熟人介绍,请来了国内某纸张生产厂家销售科两位退休人员,以加强公司的销售力量。老左和老鲍来了半个月,赵意只是象征性地跟他们说了些恭维的话,比如,两位销售经验丰富,人脉广,主要的市场维护和开发就有劳两位了。实际上,赵意都不知道怎样称呼他们二位,如果直呼其名,从年纪上讲,显然不礼貌,同样因为自己是小字辈,如果就“老左老鲍”地叫着,好像也不够尊重。这种烦恼没持续多久,赵意发现,同事都叫他们“老师”。左老师、鲍老师,他们叫得很顺口,两位老同志也爽快地应着,从他们平静的表情判断,丝毫没有违和感,倒是很享受别人这样的称谓。但赵意觉着别扭,偶尔叫声老师,声音轻轻的,两片嘴唇只是轻轻碰下,像嘴里含着大白兔奶糖在说话似的。
在赵意的吉林老家,只有在学校里叫老师,在单位里,领导之外的同事之间都张哥、李姐、王妹、朱弟般叫着,又亲切,又随意,又家常,和和气气,那才有一家亲的气氛,爱厂如家嘛。赵意最终还是没有改口,他折中了一下,从老左、老鲍这里开始,叫同事“师傅”。师傅,这个词比其他称呼都坚挺。在以前的老国企里,刚入职的工人都要“拜师(傅)”的,由师傅一点一点带领,在自己的岗位上,先入门,然后独立上岗,慢慢炼成能工巧匠。
赵意一直纠结着,毕竟身边的同事都一口一个老师叫着,而自己却师傅师傅叫着,有点另类。虽然在赵意的心目中,老师都应该是文质彬彬、才学八斗之人,老左和老鲍显然并不属于此类。老左是湖南回来的上海知青,据说退休回来前,在一家造纸厂做过多年销售科长,老鲍是宁波人,从小就在上海长大,喜欢咸蟹和臭冬瓜的他,退休前是上海一家纸业贸易公司的资深销售员。从年龄上可以断定,排除工农兵大学生的可能,他们最高的学历就是高中,想必就是那一批所谓的“老高三”吧。平时闲聊时,两个人性格外向,喜欢边说话边哈哈大笑,一点都不避讳谈自己的历史。其实,一个人的言谈举止就是他的简历,不经意间,总会给别人窥视到自己的人生历程,乃至心灵世界。没有丰富的学识,但他们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尤其在销售铜版纸方面的经验,这于他们就足够了,正是老总需要的。从这点讲,叫二位“老师”,言之有理,名副其“师”。
入乡随俗吧,赵意在公开场合,也改口叫他们老师。虽然,于赵意而言也是,提到老师,就一定想到站在讲台上挥着教鞭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人,老师一般要比较内向,不讲闲话,最好带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是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身材清癯,面容严肃,身影每每晃动在昏暗的灯光里,他们与金钱无关,与娱乐无关,与绯闻无关。
二
和同事们越来越熟悉了,除了公司的郭总,赵意一律称呼老师,每天老师老师地叫着,仿佛置身校园,自己拥有了永远有做不完的校园梦,青春因此万岁万万岁。
出乎意料的是,有人管赵意叫老师了。一次,江苏来一个催货款的人,样子看上去很小,外加一张娃娃脸,简直就是个初中生模样。在左老师的引荐下,他来见赵意,一开口就是“赵老师好”,令赵意足足惊讶三秒钟以上,才回送两个字“你好”。叫小赵的人越来越少了,有点不习惯。他喜欢人家叫自己小赵,这样有安全感,在年龄的区间里,永远有别人的年龄做上限,自己就在这区间里自由徜徉,感觉永远年轻。叫就叫吧,毕竟是个尊称。他想起自己刚毕业参加工作,进的是一家老国营工厂销售科,不久就被送了一个“老同志”的外号。当时自己很生气,但当对方这样叫自己时,人家端着一副笑嘻嘻的模样,又气不起来。这哭笑不得的滋味,真是难受!后来,听长辈讲,民间迷信说法,没有外号的人不发家(财)。姑且相信,也就自我疗伤一番后痊愈了,不再为此郁闷。自己天生长的老相,休说别的,黝黑的皮肤,加上比皮肤更黝黑的双眉,就足以夸大自己的实际年龄了。所以,今天有人叫自己老师,他们似乎手里捏着证据。
坐对面的内勤小王,业务虽然不太精,经常发票的抬头都写错,税务代码总是漏写1位。但她明事理,和赵意谈工作时,先是微微一笑,叫一声组合式“小赵老师”,软软地,糯糯地,既尊重自己又觉得亲切。自己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叫什么似乎不重要了。赵意信奉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职场哲理,自己一直风里来雨里去认认真真工作,从左老师那儿学到的口头禅,在领导表扬自己工作刻苦时,他总会迅速回馈一句“不辛苦,应该的”。
天有不测风云,也有意外甘霖,人间有高空抛物飞来横祸,也有苹果坠落枝头砸出万有引力定律。赵意没想到,在一次晨会上,郭总宣布赵意为公司销售总监,销售经理由左老师担任。销售部一共就五六个人,两个领导。赵意很快就听到了别人的议论。管它呢。难怪最近一些日子,郭总见到自己总是笑眯眯的,经常拍拍自己肩膀,说“好好干”。还以为他的老伴从京来沪陪伴他,他因此开心呢。赵意觉得惊慌失措,这简直是一次“事故”,只好连忙鞠躬致谢,说了感谢领导培养感谢同事信任之类的话。其实,这是老总变相给他加工资的借口,三十来人的小公司设置一个销售总监的职位,纯属赶潮流,其实谁都知道没必要。原来听说“总监”一词,赵意羡慕之至,以为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人物,轮到自己,才知道,许多职场上的职位,不过是一个托词,也是老板套住你的紧箍咒,要你更加卖力工作。当然,既然是光环,如雨后彩虹,迟早有消失的时候。因此,赵意只开心了一个晚上,没睡好觉,从此也就没再拿这总监太当回事。
但在这之后,人们对他的称呼变了,左一个“赵总”,右一个“赵总”,这突然令他不习惯了,怎么不叫赵老师了呢,尤其对面的小王,也叫起赵总了,神色还有些怯怯的,每次叫的时候,眼睛里都像有片云掠过。当上总监后,赵意的职称似乎被人忘记了,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营销师,却每天被赵总赵总的叫着,似乎这个总监职位替代了他的职称。赵意自己慢慢感觉到,成了总监之后,的确有些膨胀,有些飘飘然,尽管公司里同事不多,但尤其在开会的场合,有了万众瞩目的感觉。他越来越喜欢讲话,讲话还越来越长,讲话中还时常有讲解的意味,好像其他人都是学生,甚至有时还夹杂一句两句哲人的名言在其中。同事找自己审核签字时,他发现了问题,不但批评了对方,还要给人上几分钟课,这事情应该怎样怎样,那问题应该如何如何,直至对方一个劲儿的点头称是才结束。就是这么奇怪,当上了总监,可以被称为“某总”了,反倒越来越乐为人师。
赵意有些习惯了,叫顺口了,不用“三人行“,也”必有我师”。比自己年龄小的先算了,只要见到比自己年长的人就叫老师。没料到,这次碰壁了。他管烧饭的阿姨叫老师,结果被怼:“别叫我老师,你不知道吗?在单位里没有级别的人才被叫做老师。叫老师,是人家客气,没有官衔,不是帅哥,又不是美女,又不好直呼其名,实在没法叫你,才只好叫你老师。这个‘老师’,不是学校里的老师,老师有学问,这个其实是‘老实’,在公司里,一般情况下,老实的人是没有出头之日的,老师,是做到退休那天都没有得到提拔的人的‘高级职称’。你的明白?”连珠炮般说到最后,烧饭阿姨还幽了一默。赵意未置可否,但心中不以为然。岂有此理,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维修和保养灵魂的,那是天字级别的,被她这么一说,心中崇尚的一份美好竟然被涂上阴影。算了,以后见到这位和自己同姓的阿姨,他还是规规矩矩叫赵师傅吧。不,就直呼其名,赵红侠,当代“女侠客”。
三
好景不长,生活似乎故意捉弄他,刚提职不到一年,赵意所在的销售部惹了麻烦——被税务罚款120万元。鲍老师在从汕头一家公司进货时,取得的是假增值税发票。当时,大家没能力肉眼鉴别出来,鲍老师也蒙在鼓里,毫不知情。这对于规模不大的公司,可是五雷轰顶的事情。赵意作为公司销售负责人,只好咬牙承担全部责任。意料之中,他被免去总监职务。当晚,他在家里一个人喝醉了,有些委屈,但说不出口,公司只是受到了广州公司的牵连,并没有主观故意去偷税漏税,但税务局已经不听自己的解释。当然,一向偏袒自己的郭总这次也没有听他的解释,能上能下嘛,公司很快就下发了红头文件,郭总在宣布免职决定后又笑眯眯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折磨人的是,接下来在各种场合,同事还是一口一个“赵总”的叫着,这令他很感动也很尴尬,应也不是不应也不是,他和对方都觉得难受,叫“总”还是叫“老师”,好像都不是最好的选择。现代人学聪明了,谁会在对方倒霉时马上就见风使舵,跟着公司文件一起,从嘴巴上将“总”撤掉,被人说成小人、势力眼呢。叫啥还不是叫,自己又没损失。一朝为“总”,终生为“总”,这是员工的善良所致。好在赵意没有因为一点挫折灰心丧气,就算为了养家糊口,为了还每月2500元的房贷,他还在努力工作。哪里跌倒哪里爬起嘛。想不起来在哪里看到的一句话——生活才是自己真正的老师。
为了公司能在上海市场站稳脚跟,并且将公司做大做强,集团公司的侯董事长来上海的次数增加了,“以前我太忙,忽视了上海公司的工作,今后,我要多来几次,协助郭总,让咱们上海公司尽快走出低谷。当然,大家做的也很辛苦,我也是顺便来问候问候大家。”每次来沪必开会,每次开会他几乎都程序般地抛出这样的开场白。“喏,这次我给大家带点茯苓饼、北京果脯,大家尝尝,一点小意思。”见大家鼓掌,董事长停顿下,又补充一句。不是总监了,但每次开会,郭总还是钦点赵意必须参加,并仍要他来汇报销售工作。这无疑令销售经理左老师不快。当然,赵意心里也酸溜溜的,可又无法拒绝。这也让赵意又看到一线生机,自己又有了东山再起的可能。每次,赵意都将PPT(幻灯片)做得漂漂亮亮的,先从形式上给领导一点好感,自己没有因为免职附带任何消极情绪。
各部门汇报完工作,整个会议就是董事长成为麦霸了。他会先叫办公室人员去抬来一块较大的白板,多准备几支水笔。然后,他会用一块面巾纸擦擦鼻子、擦擦手,呷口茶,清清嗓子,就离开座位,像老师一样站到了白板前,开始传播他的“企业管理学”。赵意记得很多内容董事长以前都讲过N遍了,但他还是装出拥有一副强烈的求知欲聚精会神地听着,眼睛盯着董事长,用眼神和董事长交流,并不时地对着董事长的求证式的提问给予回答,“对的、是的”,不知自己重复了多少遍,每次还要点头配合,以表示内心的首肯和极度佩服。领导希望自己兜售的别人的观点得到大家的回应,回应多了,就会被当成是自己的观点,久而久之,威望会随之提高,就多了屁股指挥脑袋的资本。赵意懂得了这一点职场法则,所以,他看到,董事长每次在他点头应答时,嘴角眼角都笑意盈盈。每次董事长讲到兴奋之处,都会说自己比较喜欢做老师,如果不是进了企业,今天自己就差不多是大学教授。赵意这时会和其他同事一样,把头点得像捣蒜,以便叫董事长醉酒般继续兴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