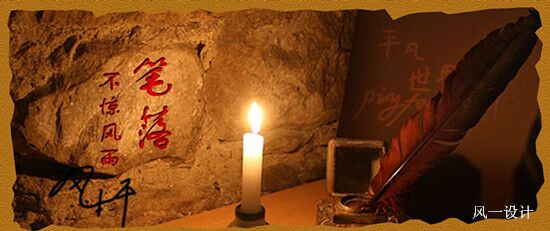【东篱】农民作家(散文)
【东篱】农民作家(散文)
引子
最近听一个作家协会的朋友讲述了一个关于农民作家的故事,听了之后感慨颇多。在感慨他的命运时,其实也在感慨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同时也感慨我自己——作为一个长期的写手,至今亦如其寂寂无名,多次想到放弃,而那个农民作家却比我在追求文学方面更加勤奋、更有勇气,于是便把这个故事写了出来。
一
那个农民作家叫曾华云。
几个月前曾华云病了,而且听说是癌症,于是相邀了作协的几个朋友大家一起凑了个份子,到医院去看望。曾华云的情况那时可能并不是那么乐观,起初他执意不收大家的钱,说他暂时还能支撑,大家在这个圈子里不过都是因为共同的文学爱好萍水相逢,能来看他已经是感激不尽,但是他不愿意大家都掏钱,这实在过意不去,但是大家哪里肯把钱再拿回去,他最后拗不过大家收了钱,并对来的人说了很多感谢的话。
曾华云是七十年代早期生人,算来也已经五十多了,不过至今还是单身。
曾华云的家族都是世代的农民,当然他到现在也还在生养他的那片土地上耕耘,只是他的祖辈、父辈都是地道的文盲,大字不识一个,但是令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阴差阳错爱上了写作这样的爱好,而且几十年笔耕不辍。
曾华云之所以走上写作这条道路,是因为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他那时候不知道怎么灵光乍现,写了一篇让老师都十分欣赏的文章,并将这篇文章在全班作为范文朗读给大家听,这让他大受鼓舞,而也坚定地爱上了语文和作文,后来他的作文时不时成为班上的好作文,这更增强了他的自信心,再后来,他尝试着向一家少年文学杂志社投稿,居然一投而中,这一下子简直让他的自信心爆棚了,不知道哪位名人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曾华云就是这句话的最好实践者,这也是他走上写作之路的最初原因。虽然他的其他课目很糟糕,但是一到语文课他便如变了一个人似的,全神贯注地学习,认认真真听讲,这也让他彻底了成了一个偏科生。
曾华云后来高中都没有考上便辍学了,但是对于写作却没有放弃,他在县城打工时,还报考了夜校,一边打工一边学习,同时还自学了汉语言文学的自考课程,虽然最终没有拿到自考大专文凭,但是文学素养却进一步得到了提升。他还办理了县图书馆的借书证,一有时间便往图书馆跑,从古代小说,到现当代小说,他都如饥似渴地阅读,只是有些外国小说读起来很费劲——人名长还容易混淆,一个场景叙述老半天,还有各种关于修辞和写作的书,他完全凭着自己的兴趣,一边读,一边写,很是写了些东西,但是后来发表的却寥寥无几。
不过此时的曾华云已经不用能不能发表来衡量自己的写作了——他已经沉陷其中,每当在写作时,他便同文章中的人物一起思想,一起快乐,一起悲伤,他说他在写作时他便找到了自我,找到了快乐,找到了价值,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二
曾华云曾对我说,他不知道爱上写作这条路究竟是成就了他,还是害了他,有时候在深纠这个问题时,他会感到十分痛苦也很迷茫。
他之所以对这个问题如此纠结,是因为他本来有发财的机会,可是就是因为不舍他的写作而至今还是个农民,一年也没有多少收入;二是因为他本来也曾经成过家,也还是因为痴迷于写作,而让自己短暂的婚姻泡了汤,如果不这样,他也许跟其他人一样,自己的小日子应该还过得不错。
曾华云对写作如此一往情深,在很多时候又很有满足感:他写了两部长篇乡土小说,写了几十篇中短篇小说,以及几百篇的散文、杂文和诗歌,每当别人吹牛的时候,他也毫不示弱,你们这算什么,老子写了两部长篇小说,几十篇短篇小说和几百篇诗歌散文,这不算成就算什么,就冲这点,大家也都不免对他刮目相看。就凭这些,当地人们对他还是不敢小瞧。
曾华云年轻的时候确实有过发财机会,同村里有个要好的朋友,一起邀他去收猪贩往南方,他跟着那个朋友跑了一段时间,确实非常赚钱,短短几个月便赚了几万块钱,但是收猪贩猪之后学习的时间少了,写作的时间也少了,而且他觉得离开了那片土地,灵感也变得没有了,而只有安身这片土地才能更好的写作,这让他觉得很受损失,他觉得不管怎样赚钱,但是自己的爱好不能丢,因为赚钱带来的快感并不能弥补写作带来的快乐,这让他很痛苦,于是他便跟朋友说,他不想干了,他的这番举动让朋友大惑不解,觉得他简直疯了,这么好的赚钱机会,居然就这样放弃,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坚持了自己的选择,朋友没办法,谁也劝不动他,他又跑回来照旧种地。
还有件让曾华云感动纠结的事是,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有人曾给他介绍过一个女人,那女人离过婚,模样也周正,当时他们没拿结婚证生活过近一年时间。
那女人看他心眼好,人也不错,也愿意跟他在一起,只是后来看他一门心思用在无用的写作上,而不想发财的路子,便几次动员他出去打工,说不管怎么样打工总比种田收益高,你看人家把日子都过得红红火火,你这样一天总窝在家里种地这日子怎么过,但是曾华云不为所动,他说他要是想发财早就发财了,而出去打工了哪还有时间和空间供自己写作,他必须要将自己的写作进行下去,女人一听觉得简直不可理喻——一个农村人总想着那些虚头巴脑的事,而不想出去赚钱,这日子哪能过得下去,于是收拾了自己的东西走了人。
对此,曾华云的父母也十分不理解,老头子气得要发病,生气地骂他不务正业,你整天写这些东西究竟有什么作用?十里八乡便是全县有几个人是靠这个发家致富的?咱们家世代农民,就不要妄想癞蛤蟆吃天鹅肉了;母亲也小心地劝说他:“华云,你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即便你不替我们着想,也要替自己的下半生着想,还是要想着多挣点钱,别再搞你那个什么写作了,啊!?”曾华云听了不反驳,也不说话,他的精神世界无人能懂,跟父母亲说写作那是他的精神家园和价值追求?他们根本理解不了,所以只有保持沉默,同时他也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期许,就是希望有一天他真的能靠写作成名,并且有很高的收益——好遥远的梦想啊!
那时候曾华云最崇敬和羡慕的作家是陈忠实,陈忠实也算是个农民作家,文化程度并不高,但是他却写出了《白鹿原》这样的巨著;陈忠实可以,那他曾华云也应该有这种可能性。
虽然当地人对曾华云还尊重,不过当地也有些跟他年龄相仿的人,对此不以为然,他们有时候在酒后也会狠狠地打击曾华云,说老曾你写的那些玩意吃不能吃,喝不喝,而且还是自己掏钱出的书,看的人又不多,有多大个屁用呢?曾华云就反驳说,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文化,知道吗?跟有钱人的财富是一样的,他们的叫物质财物,我这叫精神财富,也是值钱的东西。若干年后,那些人的财富可能消失的,但是我的精神财富却传承了下去,你们不懂,就不要乱说了。听的人都哈哈大笑。
三
曾华云后来的写作慢慢转到网上,因为他投出去的多篇小说和诗歌、散文,那些杂志社客气点地还给予回复说不便采用,更多的是连回复都不带回复的,对此他也只能一声叹息。他上网发现有榕树下、红袖添香等文学网站后,便将自己的文章投到网站上,陆陆续续写了有几百篇,他每每看到那几百篇文章,一种自豪感便油然而生。
曾华云后来还做了一件疯狂的事,那便是将他写的两部长篇小说进行自费出版。在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响水村纪事》后,他先是通过纸质打印稿和电子稿给多家出版社进行投递,但是得到的答复是他知名度不高,小说文学价值不高,没什么市场,要出版的话就得自费,对此他又只能是一声叹息。
但是曾华云是个倔强的人,这个村里自古没有人出过书,他倒是要成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于是掏了几万块钱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印了一千本,他将这些书捐给了当地的小学和中学,然后便是送人,当然他也不是见人就送,他要觉得这个人值得送,而且是读书的人,他才肯送,当然这些书至今他家里还有一大摞没有送出去。
在自费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后,曾华云最大的收获便是被县里的作家协会吸纳为会员,这让他的人生和创作仿佛又上了一个层次。也正是因为他成了县作协会员,作协的那位朋友才有机会跟他认识,进而慢慢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他在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年之后,他又写出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黄土地之上》,开始他还是想着联系一些出版社,看有没有免费出版的可能,但是最终得到的所有的答复是这种小说只能自费。
如果说第一篇小说出来后出版社的态度是这样,曾华云心底还比较好想些,一是觉得自己没有名气,即便再好的作品也不会引起反响,二是觉得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文学性、艺术性、叙事性还不够好,可能没能入编辑的法眼;可是对于第二部长篇小说,没想到从这么多出版社那里得到的还是同样答复,这让他非常受打击,同时再度怀疑自己写作的初衷和不懈坚持是否真的值得。
曾华云也读过许多当代作家的长篇小说,在他看来,除了少部分大众口碑不错的作品值得一读外,众多的作品包括一些大作家的非代表作品,甚至一些茅盾文学获奖长篇小说,质量也不过如此,可是他们的作品为什么就能被认可,而自己的作品却要自己掏钱去印刷,并请别人来看呢?
曾华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差不多搁置了近两年时间,最后他还是选择了自费出版,他想这些作品就如他的孩子一样,既然诞生了,就要让他们光明的生活下去;当然第二部小说出版后的命运跟第一部小说的命运相似。
在后来的日子里,曾华云还是沉浸自己的写作里,他有时候觉得很满足,可是有时候他又觉得自己很悲哀——自己的作品得不到认可,还遭遇到了很多人的不屑,自己的生活也因此过得很清苦,这两种情绪状态让他有时候又很痛苦不堪。
作家协会的朋友在看望曾华云从医院回家后,将曾华云追求和坚持写作的心路历程写了一篇文章发到了网上,没想到跟帖的非常之多,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有,正方的认为,做人一定要有梦,才不枉费这一生,写作不仅仅是个人情感和思想的释放,更是内在价值的自我实现,真正专业写作的人有多少呢,无非都是从业余写成了专业;反对方的认为,一个农民,写作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就当是自娱自乐;但是如果不能突破,不能写出惊世之作,而把人生大部分精力用在上面,自己掏钱出版,是不值得的;如今写作的人一大把,真正能写出好作品的凤毛麟角,而大部分人的写作都是没多大意义的。只是不知道曾华云是怎么看待那些评论的,因为他已经病到无力回天的地步了,作家协会的朋友不想再把这篇文章和跟贴转发给他,因为怕引起他更多的痛苦。
四
作家协会的朋友把这个故事讲完后,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而且作家协会的那个朋友说曾华云已经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我就更加感叹了,为这个农民作家的一生感到不可思议。
于曾华云的一生,于他的写作,于更多寂寂无名写作的人,于自己,其意义是什么?我无法说清楚。我深深叹息了一声。
农民作家,都有传奇的人生,但这种传奇,更多的是被苦难和任性填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