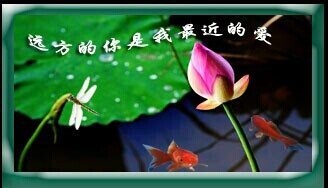【云水·忆】思想的月亮(自传体散文) ——一个人的大学系列之四
【云水·忆】思想的月亮(自传体散文) ——一个人的大学系列之四
有人说,可以放下了,你这样念念不忘活在过去,该是多么沉重啊!我说不,这份记忆不是沉重,而是让我永远住在童话里,我是童话里主人公,我的恩师孙光明导演是搭建童话世界的建筑师。不是苦涩而是欢乐,是力量,是光!他让我体悟到,肉体有生有灭,灵魂不生不死,有灵性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知。恩师生前曾有神圣约定:“艺术是我们共同的信仰,生生世世为艺术而生。”恩师如今去世10年,他的嘱托常在我耳边响起。可以说,我的每一部书,最初的构想都有恩师参与。长篇小说《碎片儿》手稿,恩师本想拍成电视剧而资金不力,鼓励我先出版书,他认为书中的语言感觉能歌善舞非常欢乐,影视难以展示,所以,他建议先展现语言才华,再考虑影视拍摄,但始终未能成行。这成了恩师最大的遗憾。那时“文化产业化”正在兴起,艺术资本化,导演已不是艺术主体,投资人的想法决定一切,这个时期成了一大批艺术家的瓶颈。《碎片儿》嫁于河南文艺出版社。我开始构思长篇小说《神灯》,最初是一个剧本,恩师看后有过如下建议:
亚珍:你好!
去北京参加第四届全国影视代表会回来接到你写来的信,最近忙了一些,复迟望谅!
看来《神灯》还会是一段时间我们要交谈的话题。剧本的立意当然是首要,但实现它全靠作品本身,视觉艺术难以加以作者的注释。这需要“意”的融入、化作人物自身的行为动作及语言,“意”是潜在的,戏剧不同于小说,小说可以加“议”的,一切动作可以停下来让作者发表意见,故此,戏剧文学似比小说更难把握一些。
任何一个人物均有“潜在文本”,即:他的私下认知感觉。戏剧文学中文本(文学性)与潜在文本(角色个人的)是交互作用的,然而难点在后者,作者要了解和把握他的整个内在,这一个就要反映作者的功力水平了。由于当代社会的浮躁,人们缺乏生活的深层重量,文学滑坡这也是这个根源。
我这样说不是指《神灯》缺少深刻的“立意”,而是讲如何把“意”变成可视可感的具象呢!也许是个技巧问题?或是“意”还未思透?这需要实践去解决。近代史西方不少“创作少于观察”(观察重于创作也不少写东西)的作家,他们强调透明的眼睛,甚至把作家自身的价值取决于他们的见闻的广博程度,我认为这是问题的一面,也是根本的一面,切勿闭上眼睛,生活是源泉。但弗洛伊德的观点也万分重要:平凡的事物有不可思议的秘密。一言之意,它们总有比我们见到的还要多的东西。我认为后者恰是文学家、艺术家们关键所在,只有眼睛是不够的,要有心眼、思想、穿透力!其实西方东方、过去与现代都有如此慧思的作家和作品。
请注意:《神灯》的“立意”在人物性格逻辑的合理可信上,在情节的合理可信上,望再思。
作为导演,我为关羽过江单刀赴会没拍好而遗憾,客观有原因,湖比不了浩浩长江、剪接也有问题,不去说它了。遗憾我没有表现出我曾有过的感觉:我多次站立长江大桥之上,目视大江东逝,内心充满浩瀚之气,这是作品要表达的根本灵魂,但作品不是这种浩然效果,最多是个狭义的“勇”字而已。我思考:长江是空阔的,除水、云之外,无具象,怎么办?怎么才能找到无中之有?虚中之实?文学想象是朦胧的,人物想到什么?——这就是要表现“心”的东西!结论:应挖掘人物心中形象!之后,我读到一篇文章谈及关汉卿的《单刀赴会》一首词,那一江满流的不是水而是血和泪。我把文章寄给了作词者,她写的词很好,再次遗憾的是曲子没有写好,太轻飘,毫无浩气,作曲没找准感觉,剪辑也剪掉些生动的镜头……就此而已!
我讲说此事是想说编导在创作过程中的相通感是何其重要!感觉不对,技巧也失灵了。
你在信中讲,感觉到我像“智慧巨人”站在你背后,这叫我吓了一跳!不敢当的,也不够格的,比之古代圣贤我算什么呢?千万不敢如此,我太平凡了,也没本事,只不过爱读点书想些问题而已,你再说此言,以后我就再不敢多言了,切切!切切!从你的作品中我不断吸取智慧,我们是心的交流,互补所短,互取所长吧。若你能从我身上取得哪怕是点滴的力量或经验,我也就感到无比欣慰了。
你说要做一个不再有任何思想,任何追求的平凡人。这是不可能的,首先,历史(个人经历)已选定了你的文化模型,客观也难以改变你、主观深处也不愿改的,你的本质是:还有更大的追求,路途艰辛而已,不要乱想。再者,平凡人就没有追求了吗?你想要的钢琴、书库还是心灵的寄托物啊!它们不会使你变成庸常的人,而使你变得更加执着地追求精神境界的人!你说得好:离开文学,又是怎样一种悲惨呢?——这也是你的心底之言,如此了解自己,置身于本我与超我之间,这应是最恰当的活法。
这月16日本想去学开车,其实我早就会开,只是想弄个执照,又一想执照在手又有何用?买不起车白搭,也就放弃了。
我也盼望与你再次合作,可我们都是被动者,现实中我真羡慕个体艺术家(画家、书法家等)不受各样外在限制,我们的行当太难了,本子、票子压得透不过气来,能开心的没几个人,那也只属暴发户……心中常不平衡,也落入苦恼,用者是虎,不用者是鼠,看来我这只虎迟早要变成鼠了。不过人生就是这么个过程,五十知天命,而今我过随心所欲之年了!这并非悲观,而是需要自我调节的年月了,我自感不足仍需充实,我是乐观的,烦恼的事存不住,除非他的价值比生命可贵。1997年来临,祝你新年快乐!万事顺心!
问候全家安好!
孙光明
1997年12月18日
这就是我的恩师,他一边排泄自己的苦闷,一边鼓励我前行。其实我和恩师同时都陷入了时代给艺术带来的困境中。钱,成了一切的主宰。当时《碎片儿》迟迟不签合约,恰好赶上出版改革“编辑责任制”,意思是编辑一年限定几个书号,书能卖出去,编辑才有工资可挣,若卖不出去呢?编辑就喝西北风。也怪难为的,编辑们要不就是求名人的书稿,卖名。要不就必须是畅销书,怎样才算畅销呢?其实也是打彩碰运气,当时言情、武打、泛娱乐、低俗性质的纷纷抬头。严肃文学趋向沉默,甚至打入冷宫,二、三、四流写者连农民工也不如,于是出现了自费出书,聊以自慰,有的为定职称一本万利。
《碎片儿》属于悲情小说,编辑是十分喜欢的,可是能否赚回钱来就未知了,如此煎熬耗去了我的耐心。我在想,假如我什么也不思不想,吃了饭弹弹钢琴,有个书库,好书看不完,也许会更轻松。可是我做了一个梦。那位已故的地委书记(把我当特殊人才调到晋中文联从事写作的人)要我写的书看,可是书就是出不来。有人说,一切苦恼,都是欲望观照下的东西。是的,那个时候太想出点儿小名儿,太想有本自己的书放在书架上自豪一下了,太想完成已故书记的愿望了。人生很多时候是一种力量的推动,你受过谁的恩赐和鼓励就是播种在心中的意念,这个意念会一着推着你奔赴那个目标,这很大程度上形成压力,就算没有这个压力,哪个作家不希望书架上有几本自己的书,哪个导演不希望拍出几部好片子?但,你的书能赚钱吗?而往往好书未必畅销,严肃的片子未必有人投资。这不都是导演与作家的困境吗?除非你当一个泛泛的匠人,别人怎么说你怎么做,拿钱走人,余下的后续与我无关(当然这也得有资格)。那和泥瓦匠有什么区别?有人设计好你按章办事即可,这是艺术的本质吗?艺术太需要自由的空气了,艺术是神性与人性之间传递的心灵活动,它必须自由放飞,他们不是命题作文的中学生,真正的作家、艺术家是不会以高价出售低廉的“艺术”,如果生存需要,卖菜卖冰棒,都不能出卖灵魂和滥用才华。宁肯独行,宁肯沉默!这就是恩师的艺术品格。现在回头看,这也是我的艺术品格。
2003年有一个影视剧“皮包公司”要我当“枪手”,说一年可挣80万。我虽不懂枪手何意,可我当然也想挣钱啊!谈判的人告诉我,比小说容易多了,市场上最畅销的书拿回来,取了它的内容结构加以组合,加点自己的想法就炮制出来了,最高明的“抢手”是可以不费劲,但不能看出是拿来的。你也不用亲自写,只把每集构架和基本内容弄出来,找个刚上路的人每集给他一千块银子他都高兴死了。条件是第一个剧本每集五至八千,如果我们觉得可用,下一部再加价。但有时间性,“抢手”就是要抢在一个思潮的前面,一过时就不值钱了。
我整个人被蒙住了,雇用别人写,设计者挣大头,劳动者挣零头先不说,艺术成了流水线,且是剽窃组合,还得窃而无痕,抢潮头,过时作废。我赶上了这样赚钱不费劲的“好”时代?我心跳,我心动!
可是,写作就是过程的欢乐,这个欢乐是创造的欢乐,是思想火花闪耀的惊喜,是一种奇思妙想出现的激动,是和笔下的人物对话的文化心理反应!一个成功的人物就是一个丰碑,这是创作唯一的享受!放弃了这个权力,你还是创作者吗?艺术变成了组件技工、缝补师、大盗无痕者?那“艺术”腕儿们岂不是每天都在作案,永不受法律制裁?难怪时代大盗辈出,文化一旦成为盗业,人文心理不就统统变了颜色?是谁的发明?
有人说,要改变观念,接受新事物。
我忐忑不安!我心神不宁!但银子却像美女在我脉管里舞动!如果接受了是可以发财的。
我和恩师说了此事,恩师说,那是出卖艺术灵魂的猪制片、猪编剧,八百万都不能干!金钱和艺术的冲突你自己选。不妨试一下,不适应就撤。我看这种做法,恐怕是骗子,写了也不一定拿到钱的。要写,先把稿费拿到手再动笔。
但我终究没有涉入这趟浑水。
恩师说,我知道你会这么做。
我说为什么?
恩师说你的文学心灵很纯粹,文学潜质这么好,走这条路子就是扼杀你的才华。创作者都不愿意放弃创作过程的欢乐,如果是赶时效,没有孕育就让分娩,只好东拼西凑,拿钱走人,如果成了流水、拼凑、缝补习惯,最终完全分食了自我,失去了灵魂的活力和生命的激情,艺术就无趣了。唉!人间到处都有黑暗,只是形式不同,非物质黑暗更可怕,它是一种无形的捆绑、剥夺、软威胁,这是最可怕的黑暗。
恩师不仅是我的文学导师,也是我的人生导师,心灵导师。我的人生正遭遇着无穷无尽的曲折、坎坷、烦恼、失意……有时候为一件小事会觉得穷途末路,恩师都及时添油点灯,照见糟粕,提取精纯。遭遇最多的是世故的陷阱,在这些问题上恩师是这么劝我的:
亚珍:你好!
首先向你慰问!太行之行万般辛苦了,病体可安好?甚念。毒性流感成灾区那确实是要命哩,至今无噩耗,言明你依然安在,可别忘了谢我一声:我遥为你祈祷了!
我更担心的是你的心情,生命中潜伏着太多的怒火,让我给你浇些冰露吧,不然烧死了,怎么得了!最近我看了一部西片《情深到未来》,男主人公从小没得到父亲的关切,直到成人他都报以怨恨,得了绝症后悟到:死亡是明白人生的最苦方法,原谅了其父为生活苦斗了一生,无暇照料他。片子写得细腻深刻,感人肺腑,也不断引我深思人生……我提的这个故事与我们无关,但人之情却相通,心灵受到震撼。我想:人生短短几十年,不应该劳累自己的心,尤其是来自那些小人的干扰,然而这终极悟性为什么总是在人们吃尽苦头才迟迟降临呢?回忆我的历程何尝不是如此?即便现在我也没有完全把人生读懂,否则遇小人就不会再痛苦自己了。
看来这冰露也是浇给我自己的。
那位“领导”的灵魂何其渺小!不足挂齿,你的对白恐怕他几辈子也不可能领悟的,如此丑态的鬼灵,白有一张人皮而已。这种无价值的躯壳从我身边也擦过不少,现在还在擦我,我也愤怒过,最近还发过大火,冷静下来顿悟:别上当了,历史总是公正的,小丑表演真的好玩,乐了我的人生!想想,人生不过荣辱一场,如果社会的奖惩制度不公,分配失衡,一切都是人情分配,暗箱操作。荣与辱还有什么意义?你不争是内在的荣!
我非常感动你说的:“我在乎的是临别前老乡们真挚的泪水,这就足够我一生享用了”!这是悟道的心声,是正直文人的崇高境界!与我的心灵融合,你讲得太好太好了。这是你最有价值的胜利!他若自愧倒有救,否则就是头猪。
写作是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处事也如此,看来这是你历时13个月“扶贫”之行最值得总结的可贵的精神财富!使我又一次看到你刚直善美的心灵。这就是人生最需求的东西!
你依然还坚持着对我的高度评价,谢谢你的真诚,但我仍觉不敢当的,倒不是你的眼力差,是“学然后知不足”,望你理解我这句话,我希望的是:我的心灵之光照亮你,它只是一盏平凡质朴的灯,不是太阳也非月亮,确实是一盏实实在在的灯啊!这样我才心安哩!
春节快到了,我们都希望转转运啊!过去一年被“西藏”一片捆住了,先后推掉六部戏,回首令我愤恼,目前有两部片约我未推,正在洽谈中,唉!也许是我要求过高,也不知是否落成。
好,先写到此,愿带去冰露灭火,你可不能烧死啊!我们还要等待机会再次合作呢!平静——看来是我们的良药!
祝你安好顺利!
孙光明
1999年1月17日
恩师的诙谐让我笑了,他看我怒不可遏,逗我一笑!这时我们是互诉衷肠的朋友。现在重阅此信,其实我与恩师同时在世故的隧道中挣扎,他给我“冰露”浇火,其实也在给自己内心浇冰露。我与恩师常常面对世故一筹莫展。但我们的心灵却是无与伦比的通透。
也许在恩师自己看来,他认为自己是一盏平凡的灯,可对我而言:他是我思想的月亮,是人生的太阳,是心灵的火把。照亮是我的感觉,恩师怎能体会到精神、知识饥渴者的惊喜和意外?培根认为:
“世上的种种快乐都能达到饱和状态,而学问却深似海洋。勤学好问者永远是谦虚的,并且如饥似渴。”
恩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会抓住我发出的每一束光亮对接,且碰出耀眼的火花,从而让我成为童话中的主人公!有的记忆会褪色,有的记忆如回荡在长空中的歌谣,随时盘旋在耳际。“来日方长”这个成语,不只是物理相见,而是灵魂的永久萦绕。对我们而言,是艺术心灵的永恒再现!
2025.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