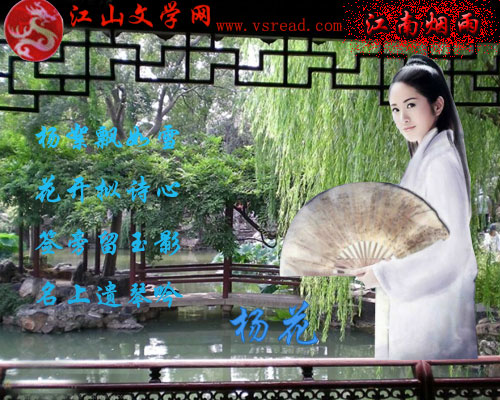【江南风骨】沉眠的爱恋,终情归陶然 (散文)
【江南风骨】沉眠的爱恋,终情归陶然 (散文)
“我由冬的残梦里惊醒,春正吻着我的睡靥低吟!晨曦照上了窗纱,望见往日令我醺醉的朝霞,我想让丹彩的云流,再认我当年的颜色。
披上那件绣着蛱蝶的衣裳,姗姗地走到尘网封锁的妆台旁。呵!明镜里照见我憔悴的枯颜,像一朵颤动在风雨中苍白凋零的梨花。
我爱,我原想追回那美丽的皎容,祭献在你碧草如茵的墓旁,谁知道青春的残蕾已和你一同殉葬”。
当大家读到上面这段文字,我想对于任何一个爱好文学的人不算是陌生了,她就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石评梅,现在,请跟我一起,走进这位民国女作家短暂而传奇的一生。她是中国现代女作家中生命最短促的一位。原名石汝壁,因喜爱梅花,后自号评梅。初次对这位山西籍作家的认识,还是在一部《情归陶然亭》的影片,影片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高君宇和石评梅的红色爱情故事。真实反映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山西党组织的创始人高君宇短暂而光辉的革命人生,艺术再现中国现代史上被誉为“当代梁祝"的一代才俊与才女冰雪圣洁、为人传颂的红色爱情故事。
民国的舞台,被尊称为先生的女子寥寥无几,先生评梅便是其中之一。她的生命虽然只有短暂的二十六年,创作生涯仅此六年,诗歌、小说、剧本、评论等体裁,她都曾驾驭过,最成功却在散文,代表作有《梦回》、《社戏》、《深夜絮语》、《墓畔哀歌》、《偶然草》、《灰烬》、《惆怅》等。小说以《红鬃马》和《匹马嘶风录》为代表,虽然她离世八十多年了,但她的文字、她高贵的灵魂依旧散发着淡淡的幽香,影响着万千读者。
她的人生值得每个女子称羡,她自幼家境殷实,其父为清末举人。自幼便得家学滋养,其父为启蒙,就读于太原师范附小、太原女子师范。她除酷爱文学外,还爱好绘画和音乐,是一位天资聪慧、不可多得的才女。她是一位独具慧眼的智者,也经历了太多的动荡与苦难,无论身处何种境地,读她的作品都给人一种清清冷冷的悲剧色彩,可谓是满纸辛酸泪。在散文《董二嫂》中她这样写道:“直到我走,我再莫有而且再不能听到那哀婉的泣声了!然而那凄哀的泣声似乎常常在我耳旁萦绕着!同时我很惭愧我和她是两个世界的人,我感觉自己的力量太渺小了,我是贵族阶级的罪人,我不应该怨恨一切无智识的狠毒妇人,我应该怨自己未曾指导救护过一个人”。她从悲观的写法,反映出了那个时代妇女悲惨命运的生活,时刻能让你感受到心灵极度的宁静和作者对现实的呐喊,读来句句震撼,从《血尸》到《痛哭珍君》中,那种凄惨的哀婉,里面又蕴藏着钢铁般意志和力量,从而争取妇女自由和民族解放的执著精神,震撼了我的心,我觉得用震撼二字来形容是再贴切不过了。
八十多年后,偶尔会与这个前世的女作家碰碰面,在她的字里行间多多少少都有了世俗的气息和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而我觉得她的文字里面所表达的情感,温和的话语,当时的那种忧郁,苦闷与欢快。也许是不同时代的人吧,明白那只是环境不同,境界各异而已。读起她的文字却依然亲切如故。她那文字绮丽、韵调铿锵的文体。小心翼翼地却让人心疼!或许是心里太珍重,又难保岁月的间隙,这个流失的时代,我总是会担心要失去了什么似的。世上最悲伤的爱情莫过于,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你的面前,你却没有珍惜,当你回过头来,决定去爱的时侯,那个人却永远离去了。
情爱原来是一件很残酷的事,在爱人高君宇离世后,她曾也想逃离,但高君宇对革命的执着与信仰让她留下来,继续打扫人生的现场,在这段孤独的岁月里,她仍然没有放弃她的信仰,两个相爱的人,心彼此在身上,以象牙做为情感的信物,所有的情感,毫无保留的付出。这从她的文字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她依旧思念高君宇,这思念化作了病魔。评梅抱病回到君宇的故乡。也陆续找到了君宇对自己的爱情信物。让我们随着她的文字回到那八十多年前,那位形单影只,孤傲自芳的梅花,在陶然亭,在爱人高君宇的墓前,触景生情,想到了远去的君宇,不免有些伤感,又有点自悲自怜用文字叙述生死离别的伤感;用文字表达刻骨铭心的悲痛;用文字记录无法停止的爱恋,为爱人写下了千古绝唱,《墓畔哀歌》就这样问世人间。
她在《墓畔哀歌》写道:“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我愿意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爱人的名字和信仰,早已深深地烙在了她的心里,是她难以割舍的烙印。喜欢文字的人都是至情至性之人,读着评梅先生的文字,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高君宇生死爱情的真情流露,她知道,她的这份浓情再也无法传递到爱人手中,寸寸相思,字字成灰,她们聚少离多,让无数美好的时光在回忆里度过,美好的爱情在爱人离世后终成了幻影。这种藏在心底的感情,也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变淡,却反而加深了我对评梅先生的那份深深的仰慕和眷恋。
这朵风雪里的梅花历经苦寒,不肯折腰,用“生不能同衾,死要同穴”的当代梁祝故事,终于情归一处,在北京城南的陶然亭迎来了她的春暖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