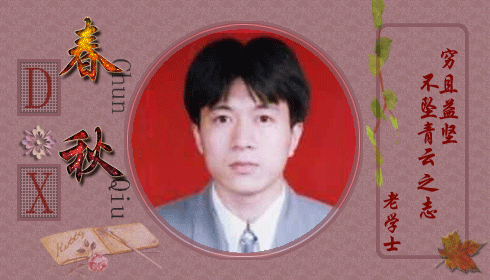【丁香杯】岳王庙,历史的沉重现实的忧思---江南行(散文)
【丁香杯】岳王庙,历史的沉重现实的忧思---江南行(散文)
一
上海外滩,一场有惊无险的偶遇
沿着南京路径直向东,尽头便是上海闻名于世界的外滩。它背倚着由罗马式、中西合壁式等52幢造型严谨、风格迥异的古典复兴大楼所组成的 “万国建筑博览群”;面对开阔的黄浦江以及对岸浦东的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等地标景观。
时值中午,烈日当空,阳光耀眼;极目远眺,瓦蓝的天幕上,大座或小座的云山醒目地移动着。黄浦江两岸古典与现代的建筑,在蓝天白云下,显得格外地壮观、华贵。此时我独断:如若想欣赏造型各异的中外建筑群,上海的外滩当属首选。
太阳愈发浓烈的热情与来来往往的人流不减的兴致,让外滩处于一种沸腾的状态。无数个花伞在外滩上组成了一条彩色的河流。不停地拍照者比比皆是。我当然是其中的一员,为了留下外滩妙美的景象,不惜汗流浃背,不时地挪动着沉重的脚步,举着手机这拍拍、那照照,很是卖力气。
新中国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元帅的铜铸塑像,立在了外滩的中部这个显著的位置,其深刻的寓意自然不必说。可是,相对于整个外滩的风光和建筑,这尊铜像无论是高度还是颜色都不是很醒目,如果换成了汉白玉,也许那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正在我边拍边想的空当,就在离陈毅元帅铜像前方不远处的江岸护栏边,聚集了一大群的人。发生了什么事儿了?我赶紧跑了过去,往人群里挤。
听旁边的游客说,有一个年近八旬的老者,不知何故,顺着护栏跳进了江里。八旬老者?那岂不危险?我着实为这老人的冒险行为捏了一把汗。这时,我看见身边几个穿着保安制服的人拿着对讲机不停地呼叫着什么,一个保安的手里还拿着拴着长绳子的救生圈,隐约听他说,投江的老者拒绝救援,抛下的救生圈,被推了出去。
正在这时,一艘快艇从黄浦江的南边疾驶过来;然后调转船头,向西边的江堤靠近,可是由于黄浦江通江接海,受到潮汐影响,平均每天两次有明显的涨潮和退潮现象。此时正处于退潮时段,快艇几次努力也无法靠近江堤处。无奈,两名警察只好将船上拴着绳子的求生圈向投江的老者扔了过去,估计是求生圈重量的原因,当然,是不是老者依然拒绝救援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扔出去的求生圈“无功而返”。
船头站着的四个警察在紧急商量后,一个头发谢顶的警察穿上救生衣、带着救生圈跳入江水中,向靠在江堤的老者游去,不一会儿,又看到一名警察也跳入水中,游了过去。
至于警察是利用什么办法把救生衣和救生圈套在老者的身上,这没法亲眼目睹了,因为江岸的护栏是呈弓形的,即使头伸出去也无法看到下面情况,况且,出事的地段已经挤满了游人。那时候,我恨不得自己是一只长颈鹿。
就在我想那老者现在是一种什么状况时,两个警察架着穿着救生衣、套着救生圈的老者出现在我的视线中。感觉体态偏胖的老者是被“绑架”的,连拖带拽地被警察架着游到了船边。之后便是水中的俩警察费劲向上推着,船上的俩警察用力向上拉着,最后将这“顽固”的老者弄上了船,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就在水中的俩警察正往船上爬的过程中,那位已经安全脱险的老者,竟然从船的窗口探出头看着俩警察怎样上船。这一细节也被我的手机“捕捉”到了。
快艇很快地驶离了,拥挤的人群逐渐散开,不少游客在长出了一口气后,不仅长吁短叹起来:“是儿女不孝顺吧。”、“是被城管欺负了吧。”、“是告状没有结果吧”……
夹在散去的人流中,听着人们这些议论,我也在想那老者跳江并且拒绝救援的原因,无数种猜测,肯定了又否定,否定了又肯定。想想,现实中的不少人因为久拖不决的问题或者由于不公正的解决问题,多采用一些极端的方式,如跳楼、挟持人质等等手段,多半是想引起公众的注意和相关部门的重视。不知道这位老者是处于什么原因,在这个闻名于世、游人如织的上海外滩,采用了投江这种方式,来引起中外游客的注意。
尽管,我并不欣赏这种极端的方式,这的确也与壮美的外滩景象极不协调;但是,我又不得不承认老者很聪明,选择了外滩这样举世瞩目的地方投江,让你不注意都不行。
外滩,在极其开阔的视野中,依然人流不断,蓝天、白云、高楼大厦构成一幅幅亮丽、壮观的画面;一次外滩之行,我的手机镜头记录下了一些极具观赏力的风光,那是些有亮度的景象;我的心中也记住了这一场有惊无险的偶遇,尽管,它让我的眼神黯然了一下……
二
岳王庙,历史的沉重现实的忧思
位于西湖西北角的岳王庙,是到杭州不能不去的一个地方,对我而言。是起初对民族英雄的敬仰抑或是后来对历史和现实的拷问,说不清楚,反正是要去的。
少年时代,评书《岳飞传》几乎成了每天“必修”的“课程”。在那里知道了岳飞、金兀术、秦桧等人物;抗金、风波亭、民族英雄等字眼不时地涌上脑际。对英雄的敬仰,对奸臣的愤恨,是少年时代最为朴素的情感表达。
在去岳王庙的路上,我继续着以往的纠结,想想,真的挺矛盾的,南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软弱的一个朝代,竟然是历史上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最为繁荣发展的一个朝代,也涌现了岳飞、文天祥这样永垂千古的民族英雄。
是以土地换和平——暂时的太平盛世、繁华一梦?还是委屈外敌的包围,求得苟安中的盛世?这就是南宋的繁荣和发展?我糊涂了,现有的答案似乎无法诠释我的纠结。
也许,岳飞的悲剧是注定的,正像南宋的最终灭亡一样。历朝历代,在不断排挤忠良、工于内讧以及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中耗去很多内力,自然就薄弱了御外的力量……
岳飞苍劲的草书“还我河山”,醒目地高悬在岳王庙大殿的中央;看到这四个大字,我不经意地就想起了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军的内耗中,元气大伤,已无力抵御沙皇俄国的入侵,致使外兴安岭、库页岛、巴尔喀什湖以东等地区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下,被强迫割让至今。千年之后,岳飞的愿望依然是“空悲切”。此时,岳飞的“还我河山”,给我徒增了些许的悲壮和苍凉。
尽管,开国元帅叶剑英的“心昭天日”、明代莆田人洪珠的“精忠报国”、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的“碧血丹心”与已故西泠印社社长沙孟海的“浩气长存”等手书匾额,显示了岳飞作为一代的民族英雄,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和被敬仰的程度,但是,相对于南宋王朝的覆灭以及曾经沦丧的国土,这些后人评价的意义,对于现代人来讲,更多的应该是起到爱国和警醒的作用;如果说,能证明这种作用的,就是始建于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年)的岳王庙,经历了元、明、清、民国几个朝代的时兴时废,却能代代相传一直保存到现在。
岳飞遇害前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的八个大字,使我自然地想起了一个地点——风波亭,千古以来,这无疑成了岳飞冤案的代名词;风波亭,很有意味儿的一个名字,一代忠良湮灭在人为制造的一场风波中,这样的“风波”,寒心的何止是当年岳飞的家人,又何止不为历代忠良和忠良之后所忌惮;“怒发冲冠”、“天日昭昭,天日昭昭”——那是岳飞的一腔热血和赤胆忠心啊,当时,却无法感动那些昏庸的心灵。
走进岳飞墓园,墓道两侧有石马石虎石羊各一对,石俑三对,正中便是岳飞墓,墓碑上刻着“宋岳鄂王墓”,左边是岳云墓,墓碑上刻着“宋继忠侯岳云墓”,两座墓,依然保持着宋代墓圆形的式样。墓前一对望柱上刻有一副对联:“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看看这幅对联,再想想历史,觉得可叹也可悲,为什么一些冤假错案,总不能及时纠正,而非要等到历史去评判。正是这样,南宋嘉泰四年(1204年), 即岳飞死后63年,朝廷才追封岳飞为鄂王,这,实际的意义又有多少呢。
岳飞没有死在外敌的手里,而是死在了自己人的阴谋之中,看着供人唾骂、遗臭万年的秦桧、王氏反剪双手、面墓而跪的铁铸人像,加上墓阙后重门旁的那一副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奸臣”,我的内心涌上的不仅仅是可惜可叹的感慨,而是陷入奸臣何以总是当道的思索中。
感觉,忠臣,被诬陷与冤枉,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里似乎成了一条不是规律的规律;历朝历代,甚至现实中,但凡忠臣,迟早都逃脱不了被诬陷与冤枉的命运,或致死或流放。有人说,这是政治,你不懂。可能,我真的不懂,我只知道,一个民族的强盛,一大批忠良贤臣、仁人志士是不可或缺的基石。没有了他们,国以何堪。
久久地注视着岳飞墓,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难道,真的必须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才有了意义吗?我们总在说要避免悲剧的发生,可是无论历史还是现实,我们人为制造的悲剧总在不断地上演。我们避免了吗?也许,我们从来也没想去避免过。毁灭了有价值的,而那些无价值的就会在制造新的悲剧中体现“价值”。
美文美按,精彩至极!


感谢一直鼎力支持丁香,谢谢成文,辛苦了!期待更多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