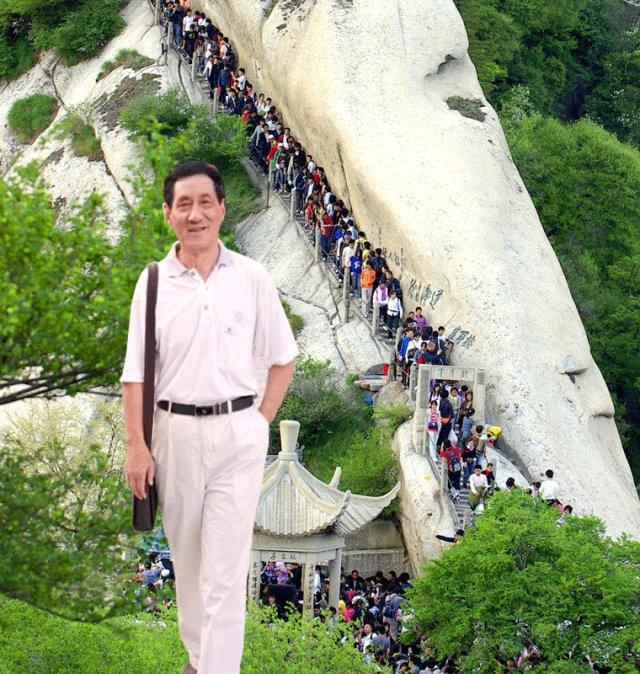琅琅读书声
琅琅读书声
![]() 恒古以来,在我的家乡第一次出现了琅琅的读书声。总之,不是讲给别人和历史,只是应该告诉自己唯一的一句话是:我和一群衣衫褴褛的放羊娃一起,给自己的生涯筑起了最重大的基础。
恒古以来,在我的家乡第一次出现了琅琅的读书声。总之,不是讲给别人和历史,只是应该告诉自己唯一的一句话是:我和一群衣衫褴褛的放羊娃一起,给自己的生涯筑起了最重大的基础。
那天的我已经十岁,在老师教鞭的指引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汉语拼音前面的十个字母读会了。那一天一直到散学好久,我都觉得胸膛震响,直到今天我写到此处,又觉得那清脆的雷声在心中升起了。二十多个放羊娃睁着清澈惊讶的眼睛,竭尽全力地齐齐喊着音节表:“啊,喔,鹅!——”
这是我第一次发出的读书声,那些齐齐喊出的音节,金钟般撞击着我的心。后来听说当年练气功的有一手叫“气灌丹田”的功夫,我想我的丹田之气是由一群童男童女相围,以春季雪水侵泡大地百草生出清香之气,再由万里扫荡的长风挟幼童初声和田野初绿,徐徐汇集,猛然击入,进入我的丹田,才造就我的今天。
然而那一天我如醉如痴,木然端坐,襟前是起伏不平的圆形山峁,脚下是高低不平的褐色田园。齐声发出的一声声喊,象似一声声春雷,在我的心中久久持续着,直到天地苍茫,大漠日沉。
记得七十年代回乡探亲时,我听到了那种绝非二十世纪的落后观点:书嘛念上些好是好哩,怕的是念得不认得主哩。念书走了的不是没见过,念得狠的坐了个帆布棚,念得日囊的骑着个叮铃铛——那一个你敢指望守着这祖辈创下的家业哩?咱不求那些个虚光,咱家养下的娃,哪怕他大字不识一个,只要能守住这份家业,就是咱的好娃哩。
庄户外面,荒山野谷依旧那样四合着,一如过去的荒凉满目。
清晨,我来到母校,又一次重逢了久别难忘的琅琅读书声。像久旱的芜草突然浇上一场淋漓的雨水,我愣愣听着,觉得心里给侵泡得精湿。那怕悲苍的景色怎么否定着,但某种城市式的苗芽还是在生长。
回味般咀嚼着四年里我听过的,这个村庄刚烈的苦难史,觉得这琅琅的读书声简直不可思议。
已是深夜,窗外那坚韧的景色终于黑暗了。只有清脆的童音,春水击冰般的琅琅读书声带着一丝血传的硬气,带着一丝令人心动的淳朴,久久地在这深山窑洞里不停地回响。
人世睡了,山野醒着,一直连着陇东陇西的滔滔山头,此刻潜伏在深沉的夜色中。高星灿烂,静静挂在山丛上空,好像也在等着一个什么。
长江和黄河本是两姊妹,黄河先是一泻千里地奔腾冲流,渐渐地变成了沉重的涌淌前移。她想乞求水量,稀释负担。而长江对她已经竭尽全力,她拖拽着更大的流域,被更庞大的如蚁人群和密集村庄拖累着,几千年来疲惫不堪,几千年来有心无力。黄土地上的人们,就如在一个家族的框架中,相依为命地挣扎前行。
一切真实就是如此,一切悲哀就是如此,一切原因就是如此。
十多岁的放羊娃不读书,你问他长大了干啥?
“娶媳妇。”
“娶媳妇干啥?”
“生娃。”
“生了娃干啥?”
“放羊。”
……
一声风号嗖的掠过山岗,把他的粗嘎尾音带走,那里有绿树,我辨不出。我只看见哀伤的风景,四下里环绕着我。仿佛山影和树影都在动,辨不清是涌动还是吼叫。
我出神地凝视着漆黑的夜空,仿佛看见了一个梦。在浪涛般涌动不息,又像高原大山般遥远的背影上,此刻印上了一个在阳光中嬉戏的,新鲜的小生命。我久久地望着,心里慢慢涨起了庄严的潮。
未来虽然很遥远,但未来的头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