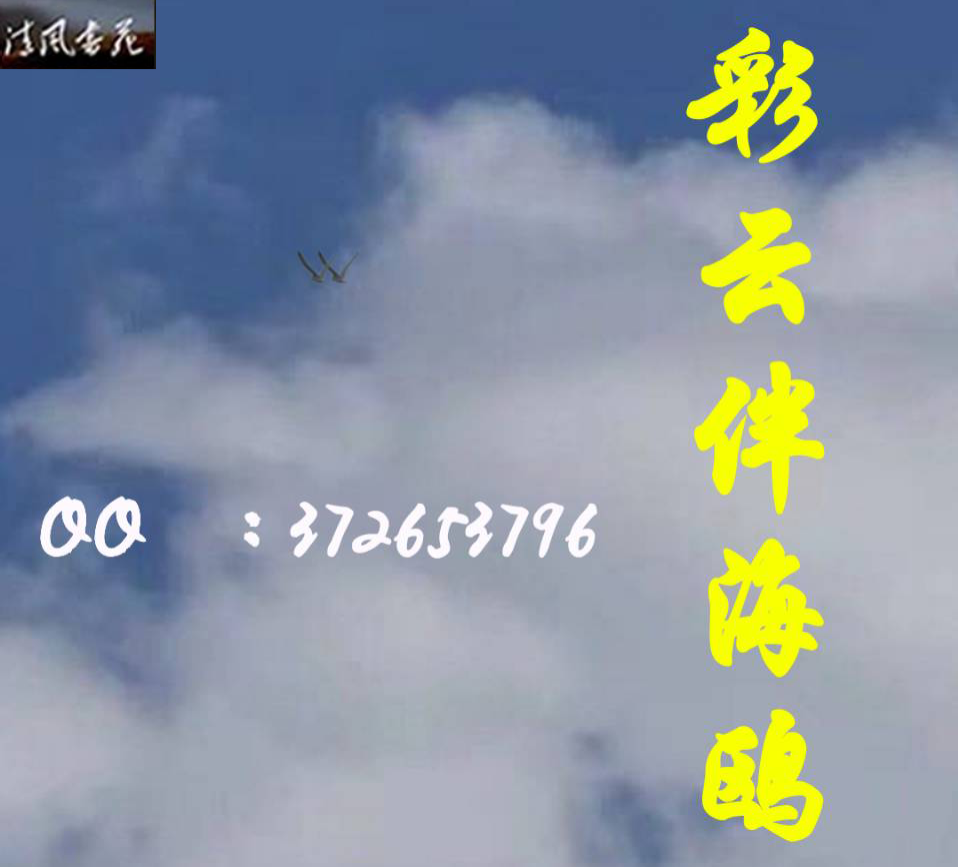【檀香】故乡的石桥(散文)
【檀香】故乡的石桥(散文)
![]()
去年秋季,我回老家住了几天。
闲来无事,我漫步来到石桥。石桥被两边的小楼遮挡,早已不见原来横跨三十多米的伟岸风姿了。想寻找田园和乡貌的影子。
桥下,小河依旧,河水缓缓流淌,两个成年人带着几个孩子正在小河里用网捕鱼,不时小有所收获,欢笑声便传上岸来。桥上车辆不多,只有三三两两的路人匆匆忙忙走过,随后又留下原来的平静。
这座石桥修建于七十年代,全长约30余米,主要连通南坝至樊哙的公路,解决土黄、樊哙片区二十余万人的生产、生活和出行问题。
修桥那年是个秋天,当时我还不满十岁,对修桥十分好奇,也感到兴奋,每天都要和小伙伴们一起在石头堆上爬来爬去,嬉戏打闹。直到爸爸或妈妈收工回家把饭煮好了,高声喊我乳名方才回家。那些时日,也少不了父母的教训,便躲在修桥叔叔的背后,求得他们的庇护。
曾记得,石桥修了近两年才竣工。以前修桥全靠人力放炮开山取石头,打石头,抬石头,没有车辆运输。因此,我见证了石桥的每块石头,也看着石桥一天一天在劳动者手里崛起,直到石桥横跨在陇溪河两岸。
竣工那天,来的人比较多,还有从县城坐吉普车来的叔叔阿姨,人们在石桥上放了比过年还要多的鞭炮,那个热闹场面是我第一次看到,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大家对石桥的期盼。
石桥竣工后不久便全线通车,就有了从县城跑上来的货车、客车从石桥上经过,车上满载着肥料、布匹、盐巴等生产生活物资。为了看稀奇,我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一起,只要听到车子从拐弯处传来的声响,便飞身跑过一段田坎,跑到石桥上,站在石栏边等待车子的到来。直到扬着尘土的汽车从跟前一晃而过,然后就追着汽车的屁股往前跑,直到累得不行才依依不舍往回走。
通车不到十年,我离开了家乡参军入伍,后来转业参加工作,便很少和石桥见面了。
后来,人们在离石桥200米处重新架设了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此后,老家旁边的石桥日渐没落了,不仅往来的车辆少了。经过的人也少了许多。但它一直是我的牵挂与念想。
小石桥是我童年时代的伊甸园。那时我胆儿大,每天放学回家,先在桥下两米深的水潭里洗澡,打水仗,玩耍累了,就在桥墩上睡上一会儿,天不黑绝不回家。
那时候,每当夏夜繁星点缀,辛劳一天的父辈们,从四方纷至踏来,有的端椅而坐,有的垫一把蒲扇,坐在石桥上的石阶上,享受着习习凉风,还有的靠在躺椅上悠然地喝着茶水。他们漫无边际的聊《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谈起了《三国演义》中的孔明诸葛亮……大妈婶婶们则是家长里短:生产队里今年哪家又要结新媳妇啦,哪家今年又要生娃添丁啦,哪家今年的收成好没有偷懒啦……我舅舅是个有雅兴的人,有时会在月色下来几段川剧,那粗旷的川腔在夏夜里的桥上,就是一阵高潮,在寂静的乡村传得很远。
天气酷热的那段时间,桥下硬是兴旺,附近的大人们各自带来一张竹席,铺在干巴巴的河床上,一边纳凉一边数着天空闪烁的星星,一边沐浴着皎洁的月光,一边听着流水淙淙的唱歌,那感觉,就像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一样舒服。
岁月悠悠,家乡的面貌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已经脱胎换骨,唯独我日益想念的石桥,依然无声无息的横卧在那里。在岁月的洗礼下,她仍然弓着那古老而沉重的躯体,虔诚地呵护着小村生命的流程。迎接着南来北往的村民。
这次回到家乡,虽然看到了熟悉的小桥流水,却难以找回往昔童年的快乐与幸福,也听不到过去那种欢呼呐喊的童声嬉闹,再也找不到那昨日的情愫。随着岁月的流逝,对一些往事的记忆已经变得模糊,但故乡这座四十来岁的石桥,却延长了我对家乡的思念和梦想,使我情不自禁的叩响回首往事的钟声。
石桥虽然老了,却也变得轻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