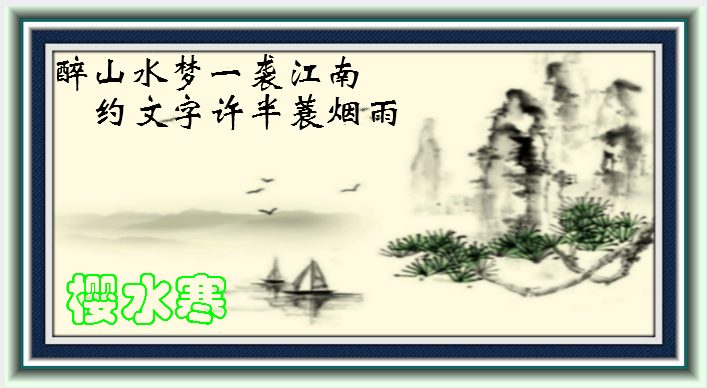【江南风景】秦腔里的“青衣”(散文)
【江南风景】秦腔里的“青衣”(散文)
![]() 在南方待的久了,对“青衣”这个戏曲中的角色会产生一种错觉。就好像,青衣只是“京剧”或者“昆曲”里面的一个角色。
在南方待的久了,对“青衣”这个戏曲中的角色会产生一种错觉。就好像,青衣只是“京剧”或者“昆曲”里面的一个角色。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人们对“青衣”的认知等同于“京剧”;昆曲细腻优美,唱腔委婉,戏词清丽,好像是专门为“青衣”(女性)量身定做的一方舞台。
正是由于地理和人文方面的原因,许多人往往忽略了一件事:其实,青衣也属于“秦腔”。
秦腔,从字面意思上理解,它是一种“秦国的说话腔调”。秦腔和昆曲一样,同为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秦腔起于西周,源于西府(陕西省岐山和凤翔),成熟于秦,主要流行于陕、甘、宁、青海、西藏等地。其中,以陕西西府秦腔最为古老,保留了较多的古老发音。
秦腔和我国许多的传统戏曲不一样,它有一个最为独特的演唱方式,那就是——吼。我来到南方后,一个人无聊时,常会听一折子秦腔消磨时光,身边的朋友听见了,便说,这是什么嘛!嗓门这么大,怪吓人的!我就给他们解释说,这是我们家乡的戏曲,秦腔。
南方人接受不了秦腔,是因为秦腔太过于粗野了,不适合南方的细腻与委婉。秦腔要“吼”,必须要“吼”,只有吼出来,戏的味道才会出来。这种吼,是属于大西北的品性:原始、古朴、粗犷、苍凉。
但是,尽管秦腔如此粗犷,它也有它细腻的一面。这种细腻,正是由“青衣”带来的。
秦腔里青衣的扮相,和京剧、昆曲、豫剧等传统戏曲相差无二。她们都是身穿颜色朴素的长袖衫、外披水衣、头戴黑色的头套和齐眉穗儿、画着淡雅妆容的女性。如蜻蜓点水一般在戏台上行走,低吟,浅唱,顾盼生姿,一步一莲花。让人崇拜,让人欣赏,也让人伤怀。
秦腔里的青衣角色,大多为正派贤良的女性,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三娘教子》中的王春娥,《宝莲灯》中的王桂英,《白蛇传》中的白素贞。而秦腔中最令人感动的青衣角色,便是《三击掌》中的王宝钏和《铡美案》中的秦香莲。
王宝钏,一个豪门的千金小姐,为了薛平贵而放弃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苦守寒窑十八年;秦香莲,一个善良朴实的农村妇女,因丈夫陈世美背信弃义入赘皇家,携二子千里迢迢去开封府的包公面前寻求王法公道。
这样的两位女性,身处于不同的社会阶级,却为了她们心中的“爱”和“仁义道德”,义无返顾的去追寻真善美,且始终保有自我的真性情。试问,我们在面对这样的角色,面对这样的女性的时候,心中是不是会有一丝的惭愧,同时,又有满腔的敬意呢!至少,我是有的,我深深地为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这样伟大的女性而自豪,而感动。
秦腔和许多传统戏曲一样,它里面有一种艺术的对比。王宝钏和秦香莲是一种对比;王宝钏出身高贵,秦香莲生于农家;王宝钏原本可以听从父命,放弃薛平贵,她仍可以过上锦衣玉食的贵族生活;秦香莲其实也可以忍气吞声,忘记陈世美,带着两个孩子去过平凡朴素的乡村生活。但是,她们都没有这样去做。她们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我们所认为的一种幸福安稳的生活,而是一种“公道”。这种公道,有“爱情”的公道,也有“王法”的公道。这种公道,或许并不为我们所理解,但她们仍是义无返顾的去做了,即使,最后的结果并非是她们想要的。但,这正是她们的伟大之处。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表示:男人都是粗陋之物,唯有女性才是世上的洁品。这样的言辞未免太过偏颇,但这是对当时礼教杀人,女性地位卑贱的封建社会的一种控告,一种人性上的反思。不光《红楼梦》如此,在《牡丹亭》和《西厢记》中,我们都会看到古代的女性为了追求内心的向往,敢于和一切封建势力作斗争等诸如此类的故事。
人们常说,艺术来源于生活。文学是艺术,传统戏曲也是艺术,秦腔,不外如是。正是由于古代封建社会的种种压迫,我们才会看到敢于反抗礼教的女性身上的光辉;正是由于如曹雪芹,汤显祖这样的作家的真实揭露与批判,我们才会了解到那个时代的繁华与悲哀;也正是因为有了一代又一代的戏曲工作者的传承与努力,我们才会看到在百年以后,一个又一个的女性在戏台上用她们的一生演绎着一个名为“青衣”的故事。
秦腔是大西北的戏剧。大西北这三个字,注定了它的广阔与厚重,同时,也注定了它的地域性和局限性。大西北之地,虽幅员辽阔,山峦起伏,但它环境干燥,缺少南方水乡的委婉与细腻,也没有沿海地区的经济发达。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青衣,却始终存在着。这种存在,就如同山之于水,天之于地。没有水的流淌,山是死寂般的厚重;没有地的守候,天是无边的空洞。
在老家,每年的清明节前后,村里最大,最为热闹的一件事便是搭台唱戏。唱戏,唱什么戏?当然是秦腔!秦腔里最好看的戏是什么?有人说《二进宫》,有人说《周仁回府》,有人说《辕门斩子》。人多了事就多,争争吵吵,各有所好。如果让我说秦腔里什么戏最好,我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对秦腔的了解和认知都是小时候听长辈们说的,走马观花,仅知皮毛。只有爱秦腔,懂秦腔的长辈们才能发表意见。而他们的意见,最后都会总结成一点:秦腔里最好的戏,就是苦情戏,就是青衣的戏。
为什么呢?因为青衣代表了最为真实的生活,代表了每一个朝代的女性,代表了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面貌。她们虽阶级不同,身份不同,思想观念不同,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义无反顾的投入生活,投入烟火的深处,并且无私的奉献着她们的一切。
戏台布置完毕,众人立于台下。此刻,板胡响起,紧接着,二胡响起,幽咽悲凉的苦音慢板(秦腔里的一种音乐前奏)从戏台上徐徐响起……戏台上,巨大的红色帷幕缓缓升起,与此同时,鼓、三弦、竹笛等各种乐器同时奏响,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依次亮相。念白过后是清唱,文场之后有武场。一个个人物,一朝一代的故事,就这样唱着,吼着,热闹着。人们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直到从藏青色的帷幕后面走出一个形神消瘦,默默低诉的女子,方才的热闹才渐渐止住了。
青衣出现了。
你仔细去看,看戏台上那一个个粉黛轻施,细步莲花的女性。你看她们的眼睛里,是不是写满了持家操劳,殷勤切切;你看她们的脚步,一步是一日,两步是春秋,三步是岁月;你看她们的背影,或丰腴或消瘦,都是平凡生活给予她们的沉淀;你看那三千青丝,你看那一指兰花,那不只是戏曲艺术的精绝表演,更是千千万万个女性用她们的一生凝结成的流年往事。
青衣在戏台上咿咿呀呀的低诉着每个朝代的生活往事,戏台下坐着的,站着的女性,又何尝不是真实生活中的“青衣”呢!
“娘为儿织布和纺线,一两线能值人几文钱。儿只顾玩耍把线揪断,短了分量少工钱……”(《三娘教子》中王春娥的戏词)
“未央宫斩的是韩信,自古道忠臣不爱身。董永典身曾葬父,大孝之人也受贫……”(《三击掌》中王宝钏的戏词)
“ 你我结下大仇怨,不报此仇心不甘。怀抱钢刀出庙院,包相爷台前去喊冤……(《铡美案•杀庙》中秦香莲的戏词)”
……
一转身,咫尺天涯。一甩袖,十里桃花。一段词,唱尽悲欢。一曲罢,曲终人散。而属于青衣的故事,却从来都没有消散。
青衣,不仅存活于秦腔戏曲当中,更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只要我们用心去找,去倾听,去感受,我们就会知道,原来,在平凡琐碎的生活背后,还有着那么多不平凡的女性!
她们,也许不及王宝钏的意志坚强,也许缺少秦香莲的一腔勇气,但她们仍是那么的朴素善良,那么的随和大气,那么的真真切切……
这些品性,是大西北的品性,是秦腔的品性,也是属于青衣的品性。因为有了这些品性,大西北不再是一个外人眼中的荒凉之地;因为有了这些品性,大西北人才能站的更直,走的更稳,更加堂堂正正,光明磊落!
秦腔里的青衣,和京剧,昆曲中相差无二。在秦腔的唱法中,最大的特点是“吼”,但这也不是说所有的角色都得“吼”。秦腔里的青衣,和京剧、昆曲、豫剧等传统戏曲中的青衣角色一样,温婉细腻,品性纯良;但当她回归到每一个地区之后,又会呈现出各自的韵味。
我国的戏曲种类繁多,但“青衣”这个角色大都相似。文中所写,并不全面,仅为我个人的见解。青瓷兄若是感兴趣,下来可听听秦腔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