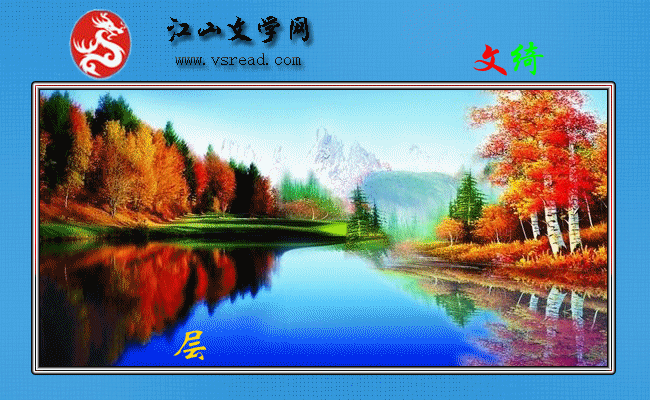【荷塘】我的幻听症(散文)
【荷塘】我的幻听症(散文)
终于看完了这本托马斯•曼的厚厚的《魔山》,卡斯托普被一战的枪炮声震醒,离开了他整整待了7年的那座隔绝了时间的狂迷颓废的魔山,那个群魔乱舞的疗养院。他在拥挤的车窗中向那个腐朽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学者挥手告别,而这个唯一康复的“问题儿童”的青年虽然从冷漠麻木、虚耗光阴的浑噩中醒来,可他又跑进了战争的恶梦,在泥泞里,在黑黝黝的森林中,在三千名冲锋的队伍里,在炮弹爆炸的火光中,哼着怀念家乡的歌词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他醒得太迟了,而我就像他一样,在厚厚的快把人裹得窒息的茧中沉睡了很久,摆在我面前的依然是迷途。
我天性耽于幻想,敏感、执着、脆弱、内向而倔强,而我的家贫穷,母亲无文化,无业,父亲早年以修车为业但生意惨淡后赋闲在家,父母勤苦而不睦,家人多灾多病,家业困蹇,我虽读书勤奋但学业坎坷,两次名落孙山。我工作后,又执迷于爱情,结果屡屡受挫,更伤于种种感情的利刃,如此种种,无不透露着一个黑暗的宿命。
2012年年初,我离开了一家大集团公司,想自己创业。可一无本钱,二无人缘,所谓创业只能从打零单开始。自己设计名片,去建材市场发资料,准备先在我那间出租小屋里做起。然而这纯粹喝西北风的方式,根本做不起来。于是,我开始找工作。一家一家的跳,一心只求高薪。年底进了一家装饰公司,干了两个月,由于自己耿介清高的性子而与任销售总监(是公司老总的儿子)龃龉,就一气之下而愤然离职。离开这家公司后,时近严冬,心情疏萧,买了电吉他、音箱,又买了踩鑔、吊鑔、哑鼓和一个纸箱组合成简陋的架子鼓,躲进摇滚乐和文学的桃源里,开始了半隐居状态的生活。我用这些简陋的乐器写歌,用一个音频编辑软件录歌,还鼓着一口气完成了一个拖了多年的长篇自传体散文的最后一章,一个有缘无果、难于割舍、分分合合疯狂挣扎了近八年的感情故事。
2012年冬的一个下午,我将失业抛上九霄云外,漫游于艺术世界,拿着《杜甫诗集》去小区后面空旷的临时小车站看书。这座车站,铁路交错,杂草丛生,鲜有火车经过,荒凉而空旷。我经常来这里徜徉,在这里,我孤独的灵魂得到了发酵……然而,渴望在艺术上有所作为的心灵又从虚热的光亮中迷失于纵横交错的一条条铁轨。那天,我看见一个落魄的诗人从已被胡兵攻陷的长安城门狼狈地逃出来,爬过长满荆棘的山包,趟过浑浊的激流,他灰暗的衣袍鼓荡荡地被风扯得像块破口袋,他依然跌跌撞撞奔向一个叫做“家”的地方……一阵风沙猛然扑来,空旷的车站翻滚着尘土,我觉得我这黑暗孤独的生活实际没有一间屋子可以庇护。
2013年7月我的幻听症爆发了。
有天我迷迷糊糊地出了门,全身如木头一样僵硬,双脚像被一根无形的绳子扯向前方。身后觉得有人跟着,似乎还听见有人向我道歉。走到那个通往圆通街的大坡前,双脚忽然变得轻盈,没几步就跑过大坡。我进了寺庙,忽然脱力,委顿地靠着柱子,想想我的人生和工作、事业,心累透了。一个师傅看了看我,问我怎么坐在地上,叫我进去跟其他居士诵经。经声中,我的迷乱暂时安宁少许,我呆呆看着墙上那幅佛陀为大众说法的图,看了很久。晚上,我听见有同事或家人或路人在外面讥笑、威胁我,在奸淫我的女朋友,我发疯似的拿着鼓棒,钻进一个个巷子到处查看,打电话回去问家人上来过没有,还逼着房东打开我楼上的单间抓坏人,围着麻园村瞎跑,在黑巷子里哭泣,仿佛身后跟着无数的跟踪者……
我在网络上看到,说发生这种病状很可能是被坏人用“电脑扫描仪”扫描到了,这是一伙非常可怕的黑道份子,他们利用这种高科技在扫描、监视、窃听、残害、诈骗一些无辜的人,我相信了,发誓要找出那些用脑电波扫描我的坏人!结果,弄得我更加歇斯底里。一入睡,在意识朦胧时,就出现各种恐吓声和谈话声,那两个月我倍受幻音的折磨,我常常感到被坏人跟踪、监视、恐吓,后来我辞去了工作,跑到成都避难,十天后回昆明决定离开这个寄托着梦想的城市这个给予我孤独困蹇的城中村,狼狈地逃回家。
回家后,我以为我有一个新的开始,然而工作也不顺利,还是经常受幻听和头晕、烦躁的折磨。2014年年底,我的幻听发作厉害,与新婚妻子吵架,她家伙同一伙暴徒冲进家中殴打我和母亲,剥夺了才两个月的婚姻,2015年初父亲病殁,接着我神智昏谵,病了数月,后被家人送去寺庙修行,现在,我在家养病。
我的幻听症和癔症编制出一个恐怖荒诞的梦。
在梦里,我丧失了自信和抗争的力量,非常懦弱,一步步被黑道用无孔不入、无坚不摧的脑电波监察仪牢牢钳制并沦为他们的奴隶,家人、朋友一个个倒下,最终我也被他们大卸八块。这个梦非常清晰可触,就像一个漆黑的能吞噬一切的魔洞在心中呼呼声响。我非常恐惧,在网上搜了许多脑电波扫描残害人脑的案例向警方报案,但警方否定这种脑电波扫描的存在,认为我有精神疾病。
向警方报案后,这些幻听开始激怒了,他们怨恨我泄露了秘密,每天都对我进行精神的威胁、思维的控制和暗示,我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白天都不敢出门,常常将自己关在幽暗里。
我去精神医院就诊后,医生认为我需要长期治疗。2015年7月,去医院打完针回来躺在沙发上,看见天花板上满是仙人怪客……有天早上我听到刀子划在墙上的哧哧声,我以为黑道的坏人来了,竟然吓得跪在门前向他们求饶。接着,我听见房屋四周响起粗暴的咒骂声和搜寻我的声音。我垮了,浑身出现痉挛现象,头也抬不起来,脑浆像被一根棍子搅得黑里泛黄。
2015年8月我在朋友的介绍下去寺院诵经修行,这个幼时就有的信仰又让我重拾希望。但我总是感觉到背后一个个人影,他们总是在我诵经时,告诉我未来,诡异和灾难的未来!破碎的婚姻之痛、家门受辱和事业的失败、身体的疾病,就像幻听症魔头派出来的三个恶魔时常攻击我的心脑。我只有一边吃药一边忏悔自己的业障,愿灵魂在经声中站起来。
2015至2016,疾病让我丢弃了专业,成为一个半脱产的赋闲养病人。特别是在2016年10月开始,母亲出去照顾老人,我一人在家,那种孤独感影响下,幻听症密集爆发,无论是在寺院,在回家的途中,在睡眠时,在一种魔力的胁迫下,与世隔绝的距离时时拉开,我对庙里的师父,对路人,对一家家商铺里的销售人员,对家人、朋友,都产生一种隔绝和怀疑,我觉得他们在隐藏一个我一直被蒙在鼓里的秘密,乃就是我的前妻是如何的背叛我,我家幼时又与这家人有如何的关联,我又是如何被几家人拿来抵罪,他们都被五个恶魔组成的和解团控制着,多少人都牵连在其中,而我的疾病和霉透顶的婚姻又是如何成为它们抵罪的纽带,家乡延续了很多年的抵罪风俗又是如何被我泄露,那些看不见的和解团又是如何要报复我,包括我吃饭,上厕所,做梦,看电视,都成为它们拿我抵罪侮辱攻击我的桥段。我的颅腔里、喉轮里、五脏里、耳膜里,随着病情的加重,渐渐听到一种由咚咚声演变出来的说话声,我体内的恶魔开始与我对话了。我被关闭在一个冷寂的家中,就像一个服刑役的罪犯。它们有时还鼓励我自尽,有时禁止我进食,不准炒菜,不准动菜刀,不准买菜,不准与人说话……有时觉得它们会控制一些陌生人在路途中和我联络,有一次我正在街上走着,一个道士领着一个女的忽然走到我身边,那个道士将我指给那个女的看,我当时迷迷糊糊没反应过来。还有一夜,午夜时分卧室里充满了嗡嗡的声音,空中布满闪烁的红亮点,我坐起来的时候,听到一个恶魔说有人进来了,房门就开了,我急忙念佛咒,接着我发狂地拿出一支来复玩具枪到处射击,才感到我即将离体的心魂又抢救回来。还有几次,我夜出漫步回来,感觉全身被什么捆住似的很沉重,头上还顶着看不见的“水桶”,全身晃晃荡荡,有时身上还有人的感觉,感觉多半是一些“小孩”,我实在无法承受时,我便跳起来落到地上才能卸掉一些无形的包袱。有一天下午,由于我的拼命抵抗,我感到它们叫一个恶魔刽子手来,用一把无形的刀,砍我的一个个无形的脑袋,这种惊悚亲历过古代刑场的罪犯才能感觉到。而另一晚上这个刽子手又来了,我从床上跳起来,拿起衣服乱甩,才制止了这个刽子手。只有特别是在半夜,种种胁迫的声音发出后,我被它们带出家,根据它们提供的路线和信息,去走一些莫名奇妙的夜路,犹如一个梦游患者。我经常被它们唤着名字,用失败的婚姻来刺激得歇斯底里,阵阵发狂,甚至不穿衣服跑去开外大门,迎接那些看不见的恶魔。还有一段时间,它们编出一些关于我的未来,三世因果,家运的信息灌输给我,让我情不自禁痴痴呆呆地编辑自己的未来的剧本,悲欢离合,种种变故,种种厄难,种种矛盾冲突,让我自我暗示催眠,自我报废,让我的大脑不得休息,经常处于异常兴奋与颓丧的状态……凡此种种,举不胜举,我是如何与它们交涉、斗争、被奴役,又是竭力守住自己的灵魂不被劫持,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写篇灵幻小说来表现。当我拿出手机来录下它们发给我的信息,和当我努力回返现实,将它们的声音转化成咚咚声,再由咚咚声销于静音时,它们开始溃败了。它们在自性真心的照妖镜前原形毕露,它们在我写出它们的丑恶伎俩时,会来干扰、阻止,最后败退。佛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无不道破了这些幻象魔音的虚妄。如何守住这颗灵妙真常的真心,不为魔扰,如如不动,还在于孜孜不倦地求索,还在于信仰的力量,还在于对这个大千世界的情怀,对生死的观照。
有一天晚上,我走下公园的商区行走,走进一个巷子的时候,我看到一个阴暗的高架桥,当我看近时,发现并不存在那个不存在的高架桥,那个十多年的孤独打工者身影渐行渐远,灵魂不禁一阵寒碜……
我走过了一条怎样的道路?我怎么变成了一个舛人、枯人、病人、痴人?我是怎么成长不起来,对于那个即将来临的中年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对于那个午夜写诗那个在重金属的暴风雨中狂打架子鼓的摇滚愤青之种种留念,面对回家乡三年来的一大叠家业颓落、失业的账单,生出种种拔腿就跑的构思,解嘲似的倒下后,我应该如何厚起一层城墙厚的皮,抗击住疾病的侵蚀和灵魂的战栗,走出那个令人心魂沦丧的“魔山”?
我知道,我的疾病来源于我所走过的黑暗孤独的生活道路,歌德说:“受苦让我获得更多。”是啊,我应该认命了,我应该承受,我应该活得勇敢一点,有滋味一点!
于是我在挣扎,多希望成长为鲁迅笔下的那棵野草!
我在修行,我在诵经,佛端坐在首页默默无言。
我站在灰色的路口,静候着那道光将我救醒……
这个冬天的雪没有降落,冰冷一次次从我背部流过,黑色的诗歌纷纷落满一地。幻听魔头与我终于又达成了一次激战后的和解,它退出说话声,退回到耳鸣,回到隐匿,我也退回到暂时的自由和清醒,退回到又是一个新春,退回到三十八岁的心智,守住灵魂的故园。
净空法师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而我最先要学习的,还是如何放下,放下疾病,放下苦痛,放下那些纵横交错的夜路,最后连放下也要放下。
赞赞赞
赞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