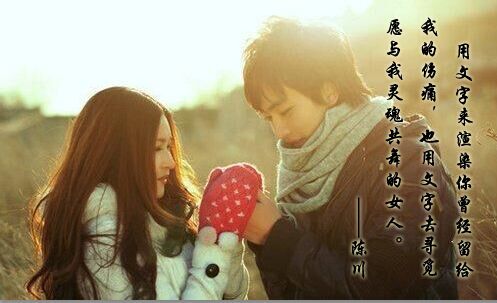【百味】关东小炕桌(散文)
【百味】关东小炕桌(散文)
![]() 我家有一个充满关东风情的小炕桌,卯榫结构,做工精巧,高度仅为27公分,是东北人放在火炕上吃饭用的,距今已有65年的历史了。小炕桌历尽风雨沧桑,伴随着父母和我两代人,走过了漫漫人生路。
我家有一个充满关东风情的小炕桌,卯榫结构,做工精巧,高度仅为27公分,是东北人放在火炕上吃饭用的,距今已有65年的历史了。小炕桌历尽风雨沧桑,伴随着父母和我两代人,走过了漫漫人生路。
我老家在吉林省蛟河市,是个老工业基地。1950年新中国刚刚建立,我父母就结婚了,住的是草房,睡的是火炕。我父亲是个木匠,就自己动手,按照东北特有的样式,做了一张骨架结实、桌邦镶边的小炕桌,并在上面凃满了松油。黄黄的,锃亮锃亮的,显得很精巧别致。平日里,小炕桌上摆满了大葱大酱、苞米馇子粥、黄面锅贴饼子。那时的东北人,全是盘腿坐在火炕上吃饭,吃完饭就在火炕上唠嗑。
1951年,鹤壁发现了大煤田,震惊了全国。为支援鹤壁的煤炭生产建设,我父亲从吉林省蛟河市来到了鹤壁一矿,当了一名技术工人。1955年,上级要求东北籍的职工全部将家眷搬迁至鹤壁落户,于是,小炕桌就随着我父母的简单行装,乘着火车,从3000多里地的吉林省辗转来到了河南鹤壁。
河南的饭桌全是高腿摆在地上的,河南人可没有在炕上吃饭的习惯。于是,我父亲就将小炕桌挪到了地上,又做了几只小板凳相匹配,一切生活习惯入乡随俗。因小炕桌造型独特,我爸又爱吃大葱、白菜叶蘸大酱,所以,引得许多河南邻居前来观看。
60年代初,国家进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人民都吃不饱饭。我家的小炕桌上,也只能摆些清汤寡水。我那时3岁,每天端着一只小木碗,趴在小炕桌上吃水煮胡萝卜。全家6口人,有5人因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唯独我没得。原因是大人们宁可自己忍饥挨饿,虚弱得拉不动腿,每天头昏眼花的,也要千方百计让我吃饱饭。
后来,国家经济形势好转了,小炕桌上的伙食也日渐好了一些。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记得爸爸最爱吃我妈手擀的捞面条,炸鸡蛋酱;我最爱吃大米饭,茄子炒土豆;妹妹最爱吃粉条;姥爷最爱吃虾酱。唯独妈妈,成天在厨房忙活,总是最后一个上饭桌。有饭她就吃些,若来了朋友、熟人将饭吃完了,她就掰几块冷馍,就着捞面条的清汤对付。星期日家里改善生活,做一条鲤鱼端上桌,妈妈从来不动筷子,尽着我们兄妹三人吃,最后盘子中剩下的鱼头,全由妈妈包圆。父母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知道粮食的金贵,所以,家中的剩饭剩菜,几乎没有扔过,即使放酸了,回锅热一下,妈妈也要吃完它。
这张小炕桌是全家聚会的中心,只要上面摆有热气腾腾的饭菜,就证明我们全家人的生活充满了生气、活气与福气;只要小炕桌的四周坐满了人,就证明全家人平安团圆、健康幸福。小炕桌上的伙食,无非是普通百姓之家的粗茶淡饭,但每每吃饭时,总是充满了全家人的欢声笑语。国家若发生了重大政治事件,全家人一边吃饭,一边展开热烈的讨论,有时候争得脸红脖子粗的。逢年过节时,妈妈忙得不亦乐乎,小炕桌上就摆满了酸菜炖粉条啦、木耳炒肉丝啦、小鸡炖蘑菇啦、汆白肉等等关东特色菜,这也是我们全家人最快乐幸福的时光。我永远也忘不了妈妈终日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忘不了小炕桌上大年三十的酒席、初一早上的饺子、正月十五的元宵、端午节的粽子、中秋节的月饼。我呀,就是围在小炕桌前长大的。
60多年过去了,父母早已过世,我也进入了老年。如今,家中买了大房子,添置了新家具。但那张历经65年风雨沧桑、充满关东风情的小炕桌,承载着我家许许多多的故事,是两代人苦辣酸甜生活的见证。今天,它已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老物件了,虽然显得老旧,甚至有些糟朽,可我依然舍不得扔掉它,用清漆又将它油了一遍。搬家时专门雇车从老区拉到了新区,放在新楼房的客厅中依然使用它,现在桌上堆满了书籍报刊。
小炕桌是我情感的寄托,上面有我父母的影子,有我儿时的温馨记忆。尤其妈妈那一声“吃饭啦!”的呼唤声和收拾碗筷的叮当声,是我童年最美好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