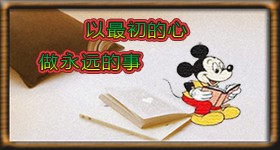【流年·那时风】我下雪,每一天,我都道别(征文·散文)
【流年·那时风】我下雪,每一天,我都道别(征文·散文)
![]() 一、暗物质
一、暗物质
一雨入冬。清晨的人行道上,步行的,骑自行车的,脑袋均缩进衣领,匆忙而过。
推着板车卖菜的妇女,一路吆喝着,慢腾腾地从对面走来。尽管她的吆喝,对于匆忙的路人来说,就是赘言。我还是觉得,吆喝顺耳还漂亮,听听:早啊,买菜吗?有新鲜的蔬菜,才从自家园子摘下来的。漂亮话吸引我的视线。
我的打量却被中断。
他迎面走来,径直向我,我不能对视。早些时候,先生就告诉我,他不大正常,喜欢蹭到年轻女人面前傻笑,然后做些不堪入目的动作。与先生散步时,我会壮着胆子打量——他的衣服肮脏,但不完全破烂,他壮实的身体有点佝偻,右眼眼角有大块暗沉的胎记,荫翳住打探来的目光,开满笑花的脸庞总是潮红,显得污秽不堪入目。他的双手乐滋滋地前后摆动,但看见人,手伸到人面前,张开嘴巴,露出一口发黄的龅牙。这样一个被暗物质覆盖面容光亮的男人,说话黏糊又可笑:给我点吃的,我想要吃啊,总不能让我饿死啊。眼角挤在一块的胎记堆积出黑铁似的阴郁,两个拖泥带水的语气词“啊”,流溢出小孩子可怜撒娇的意味。
这个可恶的人的心理不难辨析。他索要吃的,无非缺少吃的,而“总不能让……”的表达方式,又暴露他的认识:饿死,不是他自己的错误,是他人的错误,因为他人没有及时给予……这么说来,他需要的不止食物,还有宠爱,且不得,所以只能乞讨。丝丝怜悯浮现在胸口,逐渐取代了厌恶。是的,尽管是陌生人,可是,他突然跑到你面前,你不得不看见你不喜欢甚至恶心的东西,譬如他的不洁,他身体呈现的锈铁般的暗物质,他近乎下流的言行,他的纠缠……
此时,他站在我面前,扬起脑袋,豁开的嘴巴露出下腭与舌根,眼睛里满是乞求。他让人想起孩子,只不过已经长大却一路被神放弃,放弃在背对阳光的阴面。疾病的苔藓爬上生命的旅程。
他的手朝我伸来,口齿不清地讨要:呜呜,给我点吃的,我想吃啊,总不能让我饿死啊。嘟囔中,嘴角有涎水缓慢溢出。说到底,这是饥饿的召唤。他的手在我短暂的逡巡中,试探着前移,他要图谋不轨——我耸起肩胛骨,偏起右肩,打回他的手。同时,飞速递出手中的早点。拿去吃,拿去吃。
他不接。趁我疑惑时,他飞快地出手,拉住我右臂。呵呵,呵呵。他的傻笑很不流畅,短促、断续,像被什么堵塞了喉咙,给我不干净甚至难受的感觉。
喂,你干什么。
高分贝的斥责声音严厉、刺耳,果然吓住了他。他的手缩回,停留在半空,然后放下,左右手交握在一起,相互搓动。他局促地晃动身体,再次豁开满口龅牙的嘴巴,朝我露出潮红的笑容。呵呵,呵呵……
我拔脚就走。快走,接近于跑,但不能跑,担心引来他更强烈的攻击。他呵呵的笑声不断,一路跟随,里面有很不干净的杂音。
来往的人流分散了他的纠缠。我的心情暂时舒缓并平静下来,仍然不能完全排除对他的厌恶,却也无法计较,他本不是正常人,当然不能有正常举动。
第二天,再次遇见推车卖菜的妇女。她一路的吆喝,仍然毫无新意,仍然不失漂亮。提着早点的我,想买板车里的新鲜蔬菜,我朝妇女走去。
他又站在妇女面前,犹如从天而降。他靠近板车,朝妇女撒娇讨吃的,然后伸出了手。
你干什么啊,这个疯子,着实讨厌。妇女大声呵斥。我停下了脚步,站在不远处看。
滚,滚一边去。卖菜的女人一边训斥一边驱赶。
他退后一步,搓着双手,呵呵傻笑,面色潮红。他是不需要蔬菜的,也拒绝了旁人递给他的早点。但他以怪异的笑声、伸手姿势和不断重复的撒娇话语来表达他的渴望:“给我点吃的,我想吃啊,总不能让我饿死啊。”无疑,反复表达的渴望恰恰正是他原本缺少的,他以重复强调。或许,他希冀在不断地惹是生非中引起注意,仅仅乞求一点“爱”……我心中又涌出杂乱的想法,却无勇气走上前。
风猛烈地灌来,我感觉到刺骨的冷。一个奇怪的想法冒出来,我缩紧肩膀,加快脚步。我没有绕开,而是迎向他和那个推车的妇女。既然避免不了相遇,不如主动面对。
妇女正推板车离开。他依旧在旁边纠缠。
我扬起右臂招呼:我要买青菜。妇女哦哦回答我。他侧脸朝我望望,居然缩回了手,双手交握,人与板车隔出一定距离。
妇女热情地为我推荐蔬菜。也许受到她的感染,尽管他还在旁边,我丝毫没有恐惧和不安,而是顺手递出手里的早点。趁热吃了,你不是说肚子饿吗?男人就要多吃,才有好身体。
他觉得意外,怔了怔,接过早点,却又露出那潮红的笑脸。嘴巴嗫嚅下,终究没吐出什么。妇女也递给他一个青绿黄瓜,说,刚好解渴。男人咧嘴哧哧而笑。妇女又道,我们都是好人吧,欺负好人可不是男子汉作为。男人居然噢噢点头,看我买菜准备离开,他又想跟上来。妇女叮嘱我小心点。
我的心有些忐忑,但还是鼓足勇气,笑道,大哥,你还没感谢我。男人停止脚步,再次噢下,说出谢谢。我扬起右手表示再见,他提着食物转身离开。
卖菜的妇女懂得,他是个病人,而病人的行为可以不计较,她在以健康人自居。这当然没有错。我读过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关于疾病与健康,桑塔格这样说: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乐于拥有健康王国护照,但或早或迟,至少有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
对于那个被打发走的男人而言,妇女和我不过暂时幸运地站在生命的阳面。
二、身体的暴政
回先生老家路上,先生接到电话,被委托去拿药,于是,绕道到军医院精神病科,帮他同学带回五氟利多片。
车上,随着先生的介绍,我开始揣想这个年长我三岁的男人。他应该有白皙而臃肿的脸庞和身形,这是他常年吃激素药的结果,他行动迟缓甚至僵硬,眼神呆滞空洞,却整天作张望状。一起床,就搬把椅子坐在屋檐下,正对着家门前曲折小路张望,似在沉思。不明内容的沉思却使他混淆了时空,眼前变得模糊似是而非。他突然跳起来,大声叫喊:把这条该死的土路给我挖了,全挖了。然后,他扛起锄头去挖去砍。狂躁的血液使他周身沸腾,他分辨不了眼前的物和人。凡是挡住他眼睛的,他觉得是故意寻碴儿,于是抡起锄头狠狠挥舞。倒下的总是他的亲人,鲜血淋漓。
他被制服了?我问。
先生回答,强制制服。但强制制服结果就是,他发病的频率越来越高,周期越来越短。
我懂,“强制”这个充满铁锈气味的词语,无时不在传递血腥、冷酷和坚硬。它代表公认后默许的权利,对陷落阴面的个体实施集权和暴政,是对肉身的封锁禁锢。说白了,它是面对阴面行为的非常手段。于他,“强制”的结果,只能囤积他没有发泄完的病菌。大量的病菌积聚,在时间中发酵再喷射。
先生说,他常常被捆了手脚,在锁了大门的窗子边像狼一般嗷嗷嚎叫。
而开始发病时,他蹲坐在家门前的土路上,不过是水稻田中间的田埂,抚着被锄头砍伤的手臂,哀哀哭泣,然后,呼喊咒骂卷空家财跟人跑了的媳妇。这条小路是唯一连接前面公路的通道,所以,他痛恨这条小土路。
絮叨中,回到老家,我们一起去给先生的同学送药。
走在几乎不能称为道路的小土路,我很不习惯。田埂土路七弯八拐,肠子一般细弱,仅仅落下一个人的双脚而已。田埂上有坚韧的棒头草和苜蓿,这些植株拉拢了细软的泥土,使泥土异常坚实,方便落脚。田埂两边是庄稼地,棉花高大蓬勃。再走上一段,是刚刚被收割完晚稻的秧田,只留下稻谷篼子。田埂上有许多断裂的缝隙,不清楚是否他挖掘的结果。
初冬的阳光,还是爽朗的,拥挤着的红柑橘浓烈地渲染了爽朗。柑橘林后,就是他的家。先生大声喊着他的名字。
他出现在我面前。哦,哦,是你啊,他的眼光移向我——你好。他的双手在胸前重复地搓握。我回应,你好。他的脸庞确实白皙,异常的白,拥挤一块儿的肉显然浮肿,但白胖脸竟然出现了红晕。他羞涩了?
我的心抖动了下。这个高中毕业生,虽是独子却并不幸福,父母脾气异常刚烈。我几乎能想到,在他的妻子卷了钱财跟人跑后,父母指着他的鼻子,气急败坏地叫骂,灌注出“没有用,废物”等暗示。他被叫骂和暗示一点点浸染,再被俘虏。他的思想分成两半,一半提示他就是一个废物,只能连累他人,另一半思想因为所接受的教育又让他怀疑、抗拒。两个思想日夜纠缠吵闹,他开始是静静听,然后被它们左右牵制,但心灵如此脆弱,无法调和,被它们拉拽得痛苦不堪。
先生递给他一支烟,笑着说,你是否还记得,高二时,我俩在寝室偷着抽烟,被班主任老师发现,在宿舍楼下罚站好长时间。他愣了下,眉心揪在一块,留在某处的眼神浮现困惑。哦,哦,我想想,有这事情么?他凌乱的头发在金色的阳光下,泛出柔弱的黄色,有着婴孩般的无助。
先生又说,高一下学期九校联考物理,我们寝室就你一个人及格,还是72分,然后不知道是谁故意在你试卷上,把分数改成了52分,结果你聪明地把试卷贴在教室墙壁上……他嘴角咧开,眼神望向半空某处,笑容浮现于微红的脸庞,他沉浸在回忆中。
烟头即将熄灭时,先生交代他,一定要按时吃药,病好些了,最好能出去打工,换下环境,或许有好处。他点头附和先生的建议,并以语言强调,语速不断加快:就是嘛,我就是这样给他们说的,可他们硬是说我不能适应,担心我不行,担心我死在外面。先生鼓励,你是一个大男人,可以自己做主了。
他坚定而急促地点头表示肯定,他还建议,要先生给他们说说。他说的“他们”,是他的父母。好,我找机会试试。应诺的先生,在当天晚上找到了他的父亲,并把他的父亲请到先生老屋来说。
你看见了,他的病那么重,发起病来,可不是闹着玩的……老人已是满头白发,却异常执拗,无法听进任何建议。
无奈中,先生居然建议,他就是压力太大了,可不可以不把他当做病人看,换个眼光和方式……他是病了不假,可是他更需要理解,放开手脚也许更……老人站起来,打断道,你这么建议,我倒真想试下,放他出去……可是,我有个要求,你给我写下担保,担保他不会出事。
沉默中,老人弹灭右手上的烟,告辞。他不接受我们的“理解”说。对于疾病,历来只有控制,对身体实施暴政。忠直对待并理解疾病,如同真理一般匮乏。
他最终就是被送进精神病院。先生叹息。他叹息式的预见在半年后果然变成了现实,这丝毫不能证明我先生有多神。桑塔格早替我们说过:疾病是一种用来戏剧性地表达内心情状的语言。而当语言遭受轻蔑和否认时,也等于摧毁了一具灵魂,疾病已经病入膏肓。
三、罪恶论
遇到他时,我大约十岁。
他也还是少年,初中毕业在家。没有毕业吧,就是中途辍学,原因并非家里没有钱供养他读书。他的父亲是我们村有名的木匠,经常被村里村外的人请去做工,毫无疑问,他们家境比一般庄稼人要殷实。他辍学实在是他本不是读书的料。那时,他至少十六岁了。
关于辍学的原因,我隐约还知道,与他的身世脱离不了关系。他的父亲在他牙牙学语时,赶走了他的母亲,新娶了邻村的一个年轻女子。后娘不喜欢他,他磕磕绊绊地摸着桌椅和树木走会了路,哭哭泣泣地学会了穿衣洗衣服。他十岁时,后母生育了弟弟,然而……襁褓中的弟弟却在父母作乐中,被重叠的身体压死。后母无法出口的羞耻与郁积的怒火变成随时随地的叫骂——祸根,就是你带来的祸害,早晚会把你自己也害了。祸根,你这个祸根……后母的叫骂,响彻在村头村尾和田间地头,甚至追逐到学校。有一天,后母披头散发地冲进课堂,拽起他的衣领,给了他两记清脆的耳光。从此,他不再上学。
回到村里,他形单影只,他从不和男孩子玩。但在女孩子中,只有女孩子的场合中,他会脱掉裤子,捧起他腹部下逐渐昂起的阳物。胆战心惊的女孩子捂着脸蛋跑开,他哭丧着脸,声音抖颤:你们都不看啊。伙伴们屡次传播着他的流氓信息,相互提示警告。
于是,他理所当然地被我们疏远并排斥。我们女孩子躲避他犹如躲避瘟神。
然而,一个村子里,总有意想不到的时候。
我躲闪不及,遇到他了。从我家后门出来,是一片蛇床子围拢的坡地。过了这个坡地,穿过一条公路,就到了学校。
我先说说蛇床子。蛇床子也叫寸金草,那是强悍的植物,自根茎分枝,密密麻麻地蔓延出一整片,然后朝上生长,简直可以淹没我十岁的身体。“寸金草”概括了它的生命力,而“蛇床子”的称谓却告知它是毒蛇蜗居的窠臼。这样说来,作为植物的它,是相对阳光的阴面,被隔离的被遮蔽的,神秘、暴力与危险可想而知。而神秘与暴力、危险的多重浸淫,罪恶似乎不可避免……罪恶之源。蛇床子赋予的遇见也不可避免,恰如人生的隐喻。